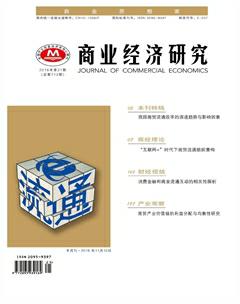“一帶一路”共建框架下產能過剩轉移與產業合作共贏的博弈
閆磊+秦浩+陳云霞
內容摘要:“一帶一路”框架已構建了一個與沿線國家經濟交流的平臺。基于此,本文通過分析我國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的資源稟賦、技術優勢等特征,闡明中亞與西部地區產業合作共贏的必要性,并就中亞與西部地區如何開展合作共贏提出相關的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 ? 中亞與西部地區 ? 產能過剩 ? 產業合作
“一帶一路”對我國產能過剩的影響
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曾一度對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過分追求,而忽視了體制調整、結構轉變、加強創新等利于中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以至于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即政府為了追求經濟快速增長,過度使用各種經濟政策杠桿,大幅降低了投資要素價)日益凸顯。
所謂產能過剩,集中表現為企業生產的產品過剩,它屬于生產能力的過剩。當產能閑置超過一定的合理水平,就會引發產能過剩問題。它是我國產業發展中的“頑疾”,其反映了當前我國產業結構處于失衡狀態,進一步會帶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等問題。雖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針對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但是,政策調整的結果并不理想,我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過度投資。
2015年期間,在投資方面,我國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較上年同期下降了5.7個百分點;在消費方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0931億元,同比增長10.7%;在進出口方面,進出口總值24.58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7.5%,較上年明顯低迷。對此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有代表性的研究,如王立國等(2012)從科技進步和技術水平的視角對我國的產業過剩問題進行研究,發現技術水平的先進與否直接關系到重復建設的發生概率,特別是在產能過剩的形成時期。高越青等(2014)認為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的根源是市場退出機制的問題,需要落后產能“淘而不汰”等途經予以解決。由此可以發現,如何治理產能過剩問題是我國產業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提出的一大難題。
就實際而言,中央政府對產能過剩的問題關注日益密切。2015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推進裝備和產能的國際合作。同年11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針對經濟發展不協調的結構性問題繼續深入挖掘,旨在掃除當前阻礙我國經濟增長的路障應作為“十三五”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產能合作的實現是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的關鍵舉措。“一帶一路”沿線包括65個國家,人口約44億,且這些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相對發達國家而言較為落后,這對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無疑是個好的機遇。
“一帶一路”的戰略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有著天壤之別。“一帶一路”的建立并不是為了控制沿線地區各國的經濟命脈,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也不只是著眼于產能過剩問題,而是旨在促進產業間的合作以實現共贏,這不僅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優質選擇。
中亞與我國西部地區產業合作共贏的可行性分析
產業發展是帶動區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而產業結構更是與當地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質量等有著直接關系。眾所周知,在不同的地緣環境、自然資源、周邊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下,會形成不同的資源稟賦,在稟賦差異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各地區各國家獨具特色的產業結構。
通過前文分析,建立在資源稟賦基礎上的我國產業,特別是以傳統產業為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就我國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而言,當前不僅制約著當地資源的合理配置,不能有效釋放經濟活力,而且對生態環境造成威脅,不利于建設“五位一體”的和諧社會發展。而中亞國家也處于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開發使得我國沿線地區與這些國家獲得了新的戰略伙伴關系。其中,塔吉克斯坦的“2030年國家發展戰略”、烏茲別克斯坦的“福利與繁榮規劃”等都與我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不謀而合,為實現產業合作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基于這些分析,本文對我國西部地區和中亞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行分析。
(一)我國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特點
我國西部地區的能源具有比較優勢,礦產資源較為豐富,依據這樣獨特的資源條件,重工業結構突出,初級產品比重大,能源工業初具規模,而且原材料工業基礎較好。在煤炭資源方面,該地區煤炭分布廣泛,我國西部地區的遠景儲量較為集中,寧夏和陜西地區儲量豐富,種類齊全。從已探明的煤種構成來看,可供煉焦用的煤比重僅占10%左右,在鐵礦石資源豐富的甘肅酒泉等地煤炭資源嚴重缺乏,需要輸入,而占有儲備優勢的動力煤則可出口。在石油資源方面,我國西部地區擁有克拉瑪依、玉門、長慶和青海四大油田,而且石油天然氣化工廠較多,標準化和科學化程度較高,石油工業從原油開采、輸送到提煉加工已經形成完整的體系。在水力發電方面,該地區建成四座大型水電站,水利發電技術領先。蘭州是西部地區的綜合性化工基地,還有寧夏的化肥廠、銀川的橡膠廠等。在紡織業方面,各省區都建立了較大規模的棉毛紡織業,西寧的毛紡織出口中亞、俄羅斯等地。
但是,我國西部地區這種過分依賴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該地區經濟發展的“資源詛咒”效應逐步凸顯(邵帥,2008)。即便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著手解決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問題,但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升級存在明顯瓶頸、各省區市的產業同構化趨勢明顯,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改善,而且我國西部地區的鋼鐵工業比較薄弱,并不能滿足地區內需求,機械工業多為重工業、國防服務業,為農業、輕工業服務少。與我國中東部地區的差距持續拉大的同時,這一區域內部的經濟差異也呈擴大趨勢。高能源消耗產業集中,對能源需求量大,使用效率低,對生態環境構成了較大程度的污染。
(二)中亞地區產業結構特點
中亞五國是重要的初級產品和原材料基地,能源資源和礦產資源存儲量大,人均能源產量是我國西部地區的6倍以上,煤炭、天然氣,特別是鋼和生鐵的生產量相比我國更是處于前列。煤炭資源和煤炭工業分布集中,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大量向國外輸出煤炭和煤電,其中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儲量高達300億桶,天然氣儲量1.9萬億立方米,煤炭儲量 336億噸。烏茲別克斯坦天然氣儲量達1.6萬億立方米,石油儲量在6億桶左右,且在生產規模和機械化生產水平上比較先進。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前景良好,分布在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也是該區的主導產業之一。在電力方面,其構成多樣,電站總裝機容量高達3877萬千瓦,而且吉爾吉斯斯坦的水能蘊藏量高,烏茲別克斯坦能源種類齊全,以天然氣和水力發電為主。黑色金屬礦產資源集中分布在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兩國,并且形成了龐大的采掘工業。在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方面,哈薩克的東部阿爾泰山有“有色金屬寶庫”之稱,此外,銅在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均有分布。得益于這一優良的自然資源稟賦,有色金屬工業成為哈薩克斯坦的經濟主導部門。
雖然能源資源是中亞地區最大的優勢,而且礦產資源也較為豐富。但是,中亞地區由于受前蘇聯重工業發展戰略根深蒂固的影響,導致如今的產業結構依然單一化、低級化,憑借礦產資源和能源資源的充足,五國以礦物開采和工業原料生產為主,而輕工業、加工工業、食品工業明顯落后,機械制造也不發達。總體經濟規模仍然偏小,多年來其豐富的資源和經濟發展極不相稱。
由于中亞五國處于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產業結構低級狀態長期得不到改變,集中表現為對資源的重度依賴,且分工較為固化,而分工的固化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的單一,特別是工業結構單一,除冶金工業、化工工業和農機制造業外,整體加工業落后,大量的工業品需要盡快進口。缺乏高新技術產業,能源需求受制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因此內需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需求依托于出口。此外,這樣的產業結構對能源的高消耗提出了要求,對環境也造成了高污染,不利于長遠發展。
(三)中亞和我國西部地區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對比
通過上文分別對我國西部地區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的分析,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西部各省產能過剩問題突出,產業的關聯程度較低、產業組織結構層次較低,突出表現為二元經濟和外部移植經濟下的低水平、不健全的產業結構,由于過分依賴要素投入和投資拉動,形成了較難改變的“資源互補”、“產品互補”的資源導向型產業結構,其導致了我國西部地區的產業附加值低、縱向分工難以適合生產需求等。我國西部地區較全國而言,其產業結構總體水平較低,從傳統產業來看,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利用率低于全部平均水平,化解產能過剩的壓力增大。從新興產業看,總體規模依然偏小,技術創新能力依然偏弱、技術創新綜合服務依然滯后。而沿線地區,例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蒙古等,其中特別是塔吉克斯坦,該國水能資源豐富,擁有中亞地區水資源的60%,但是有效利用率極低,只有5%。因此需要我國為其提供科學技術和工藝設備,以促進該國經濟增長。由于制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是產業結構的低度化,因而通過沿線地區的產業合作不僅可以將過剩的產能提供給有需求的國家市場,而且可以向該國家引進科技工藝和生產手段,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這些領域是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下的重要合作方向。我國西部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國家進行合作,是順應經濟發展潮流的必然舉措。
中亞與我國西部地區產業合作共贏的布局
伴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國家間的合作共識不斷加深,出于經濟互補的要求,跨地區、跨國家的產業合作越來越引人關注,各國之間的貿易合作與交流成為必然。學術界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如比較優勢理論、關稅同盟理論、市場內部化理論等為各國間開展貿易進行產業合作提供了強有力的依據。其中的一個主要依據在于發展差距和技術梯度的存在(盛洪,1994),而不同地區的經濟互補和產業結構互補帶來了開展區域產業合作基礎的可能性,通過不同國家和區域之間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信息、技術等交流,可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實現合作共贏。
策略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在構建我國西部地區和絲路沿線國家國際經濟合作帶的模式下,需要結合上述對我國西部地區和中亞五國的產業結構優勢和劣勢,從而具體分析我國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產業合作的策略。我國西部地區與中亞五國毗鄰,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承東啟西,大規模開發資源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要依托。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通過甘肅、青海、新疆、寧夏、陜西省區與中亞國家開展資源、能源等合作,會促使雙邊實現經濟新一輪發展。但是,新機遇也帶來了新挑戰,在我國西部省區與中亞國家合作的同時,市場必然會驅使產業合作實現多元化,這要求我國要進行相關體制機制的創新,從而使“一帶一路經濟帶”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和顯現,使得我國西部地區和中亞五國的產業合作得以優化和完善。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產業合作渠道將會逐漸融洽,合作意愿將會不斷增強,合作內容將會不斷提高。
近年來,中亞地區與我國西部地區經濟貿易不斷加強,筆者將1995年和2012年的中亞五國出口額與進口額進行對比,可以看到在中亞五國優勢產業中,出口量呈現大規模提高,特別是基礎能源和礦產資源,在加工工業方面的進口數量也呈現遞增,如石油深加工、化工及其制成品、食品加工以及高技術含量的電子機械等。
(一)傳統產業領域合作
我國西部省份的傳統產業在發展中面臨著過度倚重資源和發展方式粗放兩大瓶頸,因此要充分挖掘這些地區的優勢和潛力,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加大產業鏈的價值增值,建立一批煤炭化工、石油儲備等基地,以提高產業規模和集中度,進而變成突出的優勢,與中亞地區進行產業合作,促進產業鏈的深化。以甘肅省為例,在甘肅省的石油化工基地方面,代表性的是蘭州石化企業,通過技術改革,促進乙烯擴能改造。同時,發展蘭州石油儲備基地,建立石油化工等原料集散地。
(二)新興產業領域合作
我國西部省份在新興能源方面選擇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醫藥等關鍵領域作為新興產業基地建設的主攻方向。要延伸產業鏈條,提升產業集約化水平,實現新興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不斷壯大高精尖技術隊伍,提高技術含量,轉化為可以出口的優勢,與中亞地區進行經貿合作和產業聯動。以甘肅省為例,在甘肅省的河西新能源基地方面,在促進產業集群的基礎上,大力推進以酒嘉地區為核心的新能源基地建設,合理布局配套調峰電源建設,加快新能源裝備制造產業升級和規模擴張。同時,建立政產學研用戰略聯盟,強強聯合,促進新能源、新材料的開發與使用。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將以我國甘肅省為代表的我國西部省份與中亞五國在傳統能源和新能源方面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我國與中亞國家在能源資源和加工業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具有很大的合作潛力。
對策與建議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發現,經濟利益的訴求、政治環境的穩定、相似的民族傳統等都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地區國家和我國西部地區的產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些有利條件下,結合當前我國西部地區和中亞五國的產業結構現狀和產業合作方式,筆者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提出具體的配套政策,以實現相關的機制創新。
第一,科學優化基地布局,引導產業集群發展。針對西部地區產業基地的不足,要想積極地參與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與地區的產業合作中,以實現共贏。應主動把握產業結構的調整機會,建立以環境容量、基礎設施條件等作為約束變量、以形成地區間的合理分工、優化布局結構作為目標的產業布局,并通過明確定位、協調統一等方式優化產業基地空間布局。在推動雙方合作過程中,要注重各大基地在空間上的相互統一和協調。
第二,產業基地建設思路須堅持以下原則: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本為紐帶,以企業為主體,通過外引內聯,推進強強聯合,積極主動應對外界挑戰,化挑戰為機遇,從外部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創造發展條件。充分發揮規模效益,加快培育若干個具有一定產業規模的大型集團化企業,堅持把重點突破、整體推進作為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方法,促使上中下游產業鏈之間的企業改組聯合,使各產業間形成緊密的產品鏈和產業群,同時要加大創新力度,加大政府對公共服務設施的先導性投入,轉變投融資和管理方式,引導資源優化配置。
第三,加強不同產業的分類指導,提升基地的產業組織效率。應根據我國西部地區的實際情況,對不同產業分類指導,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產業基地高效、健康的發展。立足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按照有序開發和總量控制并舉的思路,延伸傳統產業鏈條,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應共贏。做大做強新興產業,是西部各省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構建現代產業體系、促進新型工業化向縱深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四,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生產要素,促進產業基地均衡發展。合理安排好產業基地內部大、中、小企業的合作,實現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與技術合作。要努力利用專業化分工、規模經濟、橫向一體化,實行必要集中,搞好企業協作,同時應與高等教育機構聯手,加大專業知識人才的培育力度,企業應當為經過高等教育培訓的人員提供平臺,使其在實際生產環節充分運用專業知識,實現非技術人員向技術人員的轉型,從而增強企業自身的實力。
第五,充分利用互聯網通訊技術,加強中亞五國與我國西部地區的互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方便中亞五國與西部地區的信息技術交流溝通,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并以此來帶動交通服務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