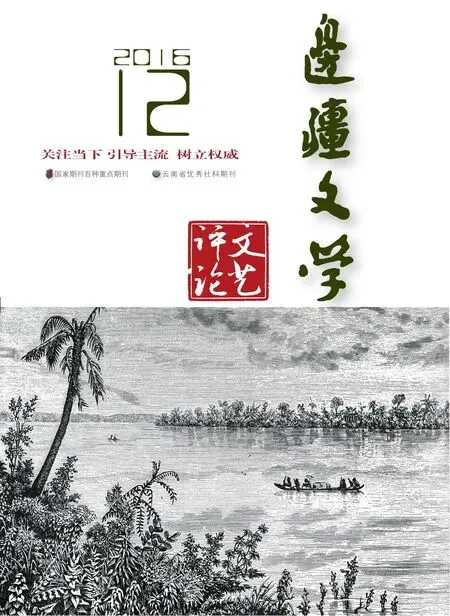錢鐘書論宋詩
◎焦印亭
錢鐘書論宋詩
◎焦印亭
錢鐘書先生深于宋詩,無論在宋詩的大判斷中,還是于小結裹里,都有精辟獨到的見解與評論,具有重要的詩學價值和理論意義,其《談藝錄》和《宋詩選注》是上世紀40到80年代大陸宋詩研究的最大收獲,為當今乃至后人的宋詩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與有益的啟示,對今天正在進行的詩學建設和詩歌創作都有深刻的意義。錢先生涉及廣博,限于篇幅,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對宋詩宏觀整體的準確把握
說到宋詩,就不能不提到唐詩,唐詩與宋詩孰優孰劣,這是每一個宋詩研究者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千百年的一樁公案。
唐、宋詩之爭起自南宋。最早見于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對蘇、黃及江西派的發難,這拉開了唐、宋詩之爭的序幕,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人對唐、宋詩之別的評價。時人評價宋詩時往往仍將其置于唐詩的參照系統之下,認為這一時代的詩歌不及唐代。而錢鐘書卻另辟蹊徑,從創作主體的“體格性分”之差異來進行劃分,他指出不能僅以唐、宋朝代的不同而區分唐、宋詩之優劣。“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1](p2)然后他又高度概括了唐、宋詩之間“體格性分”之差異:“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1](p2)這一立論站在宏觀的高度,向我們說明了詩分唐宋的關鍵不在于詩、不在于朝代、而在于創作主體,在于創作主體的“體格性分”之差異。這樣就通過表層現象把握著了問題的深層意蘊,為觀察認識一個朝代的詩歌的本質特征找到了一把鑰匙。
曰唐曰宋,特言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1](p2)
在錢鐘書眼中,唐宋詩只是稱謂之便,唐詩未必是唐人所寫,宋詩未必出自宋人之手,唐人可以寫宋詩,宋人也可以寫唐詩。杜甫、韓愈、白居易、孟郊,雖是唐人,但詩中議論化的傾向比較突出,且以散文的筆法入詩,雖是唐人,卻開啟了宋調。張耒、姜夔、九僧、四靈等,雖是宋人,但詩意境蘊藉、清空騷雅具有唐詩空靈飄逸之貌,實為唐音。既然詩的風格是由人的性情決定的,因此不同的人,不同的審美主體就會有不同的詩。“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1](p3)正
因為人的性情分為“高明”和“沉潛”,所以“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唐宋之畛域”。[1](p3)錢鐘書認為,自唐宋以后,所有的詩可分為兩類,一類偏重豐神情韻,一類偏重筋骨思理。所謂“詩分唐宋,本乎氣質之殊,非僅出于時代之判,故曠世而可同調。”[1](p313)真取心析骨之論。既然風格出于人的性情,性情會隨著時代、閱歷的不同而改變。詩人的風格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變化和表現。例如人的一生,少年時代雄心勃勃,才氣英發,就喜歡寫唐詩。到了晚年,閱歷豐富,思想深沉就趨向宋調,即錢先生所謂“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后不侔。”[1](p4)
錢鐘書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論證后,最后引出了清人蔣士詮的“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作為結論,對唐宋詩未作軒輊之分。在他看來,“詩不當論時代,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于外。”[1](p143)唐詩和宋詩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各有千秋、互有短長,“襲常蹈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是唐詩所短,“長鋪廣引,盤折生語”是宋詩所長。[1](p143)他的這一切理饜心之論和精見卓識,令人嘆服,為我們準確地把握宋詩的本質提出了全新的理論,體現了他不同流俗的理論勇氣和創新思想。世人在論及唐宋詩之別時,錢先生的話已成經典之語,被人多次征引。他對唐宋詩的認識,正如敏澤先生概括其為學特點時所說:“獨行其是,不顧人非,既不拾別人唾涎因襲陳言;更不托飛騰之勢,仰人鼻息。”[2]
對于宋詩的價值,錢鐘書在《宋詩選注·序》中做了精確的描述:“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并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3](p10)可見,宋詩為變唐詩而來,善變唐詩者只有宋,怎樣拓展、變化的特征是什么,錢鐘書亦進行了深刻的揭示:
“有唐詩做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大不幸。有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會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3](p10)
“宋人能夠把唐人的道路延長了,疏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肯去冒險開荒,沒有去發現新天地。用宋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憑借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澈,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里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么特著的轉變,風格和意境雖不寄生在杜甫、韓愈、白居易或賈島、姚合的身上,總多多少少落在他們的勢力范圍里。”[3](p11)
“若只就取材廣博而論,宋人之視唐人,每有過而無不及也”。[1](p108)
在此,錢先生既肯定了宋詩對唐詩的發展和藝術創新,也指出了其在嬗變過程中的缺憾。
對宋詩的不足,他更有清醒的認識:宋詩的缺陷是,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宋代五七言詩講“性理”或“道學”的多得惹厭,而寫愛情的少得可憐。[3](p7)其次: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歷史和社會,卻沒有全部反映出來。有許多情況宋詩里沒有描敘,而由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3](p7)
錢先生肯定了宋詩對唐詩的發展,另辟新境,在題材內容上較唐詩廣闊,在技巧上較唐詩精細。他一方面肯定了宋詩的創新,同時也批評了宋詩的模仿和復古。
在對宋詩的成敗得失了然于胸后,錢先生給宋詩做了總體的評價:“整個說來,宋詩的成就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我們可以夸獎這個成就,但是無須夸張、夸大它。”[3](p10)與唐詩和宋詞的研究相比,宋詩的研究一直較為冷落,對其總體評價也不高,錢鐘書以獨特的視角觀照宋詩,發之有為,持之有故,對宋詩的定位可為超然持平的公允之論。
二、對宋詩重大問題的深刻揭示
1、以文為詩
以文為詩,指詩的散文化,是宋詩的一大特點,也是招致詬病之處。錢鐘書卻不以為然,在《談藝錄》中,他多次論及宋詩血緣上的兩個老祖宗——杜甫和韓愈對宋人的沾丐和影響,他引用李武曾《秋錦山房
外集》卷三的一句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宋詩杰出者,其于杜韓諸家入而能出。”[1](p428—429)針對《后山詩話》批評韓愈的“以文為詩”,和蘇軾的“以詩為詞”,是失去詩、文、詞各自的“本色”、也是不可取的。錢鐘書則從文體演變和發展這一獨特視角,對其作了另一種闡釋:“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詞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1](p29-30)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中也有相同的觀點和論述,“以文為詩,乃刊落浮藻,盡歸質言之謂。”[4](p478)錢鐘書對南宋劉辰翁的評點不甚滿意,批評其“尋章摘句,小道恐泥。”但對《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所表現出的推崇文人之詩和強調文對詩的積極影響卻十分稱賞,劉辰翁論詩、詞,不同于《后山詩話》死守疆域,持比較通脫的態度,他稱贊韓愈、蘇軾的以文為詩“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因此錢鐘書說其“頗能眼光出牛背上。”[1](p34)隨后錢鐘書又援引西方文學的現象來進行比勘:“西方文學中,此例甚繁。就詩歌一體而論,如華茨華斯之力排詞藻,即欲以向不入詩之文字,運用入詩也。雨果言‘一切皆可作題目’,謂詩集諸學之大成,即欲以向不入詩之事物,采取入詩也。此皆當時浪漫主義文學之所以自異于古典文學者。后來寫實主義之立異標新,復有別于浪漫文學,亦不過本斯意而推廣加厲,實無他道。俄國形式論宗許可洛夫斯基論文謂:百凡新體,只是向來卑不足道之體忽然列品入流。……竊謂執此類推,雖百世以下,可揣而知。西方近人論以文為詩,亦有可與表圣、閑閑、須溪之說,相發明者。”[1](p35)基于此,他對王安石的這類詩是稱道的:“荊公五七古善用語助,有以文為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傳。”[1](p70)
2、以禪喻詩
“宋人多好比學詩于學禪”、[1](p257)“比詩于禪,乃宋人常談”。[1](p258)錢鐘書對嚴羽的《滄浪詩話》很是贊美:“儀卿之書,洵足以放諸四海,俟諸百世者矣。”[1](p276)并對其“通禪于詩”的貢獻作了高度評價:“滄浪別開生面,如驪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獨覺,在學詩時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詩后之境界,妙悟之外,尚有神韻。不僅以學詩之事,比諸學禪之事,并以詩成有神,言盡而味無窮之妙,比于禪理之超絕語言文字。他人不過較詩于禪宗,滄浪遂欲通禪于詩。”[1](p258)與此同時,錢鐘書又破解了嚴羽“妙悟”說的玄妙神秘:錢鐘書認為,“悟”,無時無地不在,“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他征引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三來進行說明:“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后,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后火可不滅。故悟亦必繼之以躬行力學。”[1](p99)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學道學詩,非悟不進。”[1](p98)在錢鐘書看來,“悟”者,就是今語所說的對事物內部規律的心領神會,既有先天的成分,更有后天的積累與學習,悟并不是禪家獨得之秘。“悟乃人性所本有,豈禪家所得而私。一切學問,深造有得,真積力久則入,禪家特就修行本分,拈出說明;非無禪宗,即并無悟也。”[1](p199)
詩和禪的相通就表現在“悟”,“禪與詩、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雖二,而心之作用則一。”無論是禪悟還是詩悟,“皆是思力洞澈阻障、破除艱難之謂;論其工夫既是學,言其境地即是寫悟。”[1](p101)因為禪悟與詩悟心理機制相同,所以“詩人覓句,如禪家參禪;及其有時自來,遂快而忘盡日不得之苦,知其至之忽,而不知其來之漸。”[1](p102)
錢鐘書一方面認識到了詩禪相通,同時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區別:“了悟之后,禪可不著言說,詩比托諸文字。”“禪宗于文字,以膠盆黏著為大忌。”[1](p101)而“詩自是文字之妙,非言無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鏡花,固可見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鏡而后花能映影。”“詩中神韻之異于禪機在此,去理路言詮,固無以寄神韻也。”[1](p100)“禪破除文字,更何須詞章之美;詩則非悟不能,與禪之悟,能同而所不同。”[1](p307)在《談藝錄》補遺中,錢鐘書又就詩和禪對待語言的不同做了詳細的闡發:“禪于文字語言無所執著愛惜,為接引方便而拈弄,亦當機煞活而拋棄。……祈向正在忘言。詩藉文字語言,安身立命;成文須如是,為言須如彼,方有文外傳神、言表悠韻,斯神斯韻,端賴其文其言。品詩而忘言,欲遺棄跡象以求神,遏密聲音以得韻,則猶飛翔而先剪翮、踴躍
而不踐地,視揠苗助長、鑿趾益高,更謬悠矣。”[1](p412)
因此他批評嚴羽“詩之有神韻者,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之說,“幾同無字天書”。嚴羽“以詩擬禪,意過于通,宜招鈍吟之糾謬,起漁洋之誤解,”[1](p100)也就不難理解而在情理之中了。在這里,錢鐘書既準確把握到了“學禪學詩,非悟不進”的相通之處和二者對于語言的不同態度,又揭示了“悟”在詩與禪之間的作用是不同的:禪以悟為止境,詩則不能止于悟。正如他所說的那樣:“禪家關捩子,故一悟盡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一指頭禪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詩家有篇什,故于理會法則外,觸景生情,即事漫興,有所作必隨時有所感,發大判斷外,尚需小結裹。”[1](p101)在此他指出了詩與禪在‘悟’后的重要區別:禪家一悟之后,終身受用;“詩雖悟后,仍需深造。”錢鐘書一方面注意到了詩和禪的相通,又未將二者混為一談,并對“以禪喻詩”者提出了忠告:“余竊以為潭藝者之于禪學,猶如先王之于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1](p104)否則,“禪以生縛,忘摩詰之誡,”“看朱成碧”。[1](p104)
3、活法
活法是江西詩派“脫胎換骨”、“點鐵成金”理論之外的又一談藝要旨。出自呂本中的《夏均父集序》:“學詩當識活法。活法者,規矩具備,而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于規矩。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錢鐘書對呂本中論詩講“活法”很有好感,評價它是“江西社”中人“傳授心法”。“活法”的來源與涵義,錢鐘書理解為它深受禪學的影響,是禪學與詩學相互融通的產物。佛家有“死語不離窠臼”之說,詩家有“文章切忌參死句”之說,(陸游《贈應秀才》)論詩有謝玄暉“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說,“彈丸”形圓易動,是“活”生動形象的比喻。二者都是擺脫窠臼和束縛而越出規矩之外,“活”是它們追求的最高境界。盡管“嚴滄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論‘詩法’,一則曰‘造語須圓’,再則曰‘須參活句’,與‘江西派圖’作者呂東萊之說無以異”。[1](p117)因此,錢鐘書斷言呂東萊之“活法”論是“借禪人‘死語不離窠臼’話頭,拍合謝玄暉“彈丸”名言,遂使派家有口訣、口號矣。”[1](p439)隨后,錢鐘書借用曾向呂本中請教過詩法的曾幾的詩對“活法”理論進行詮釋。《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其圓如金彈,所向如脫兔。”“勿參死句”就是參活句、“離窠臼”,曾幾所認為的“活”就是“縱橫無不可”,“活法”就是“其圓如金彈,所向如脫兔。”錢鐘書認為“其圓如金彈,所向如脫兔”兩句詩的內涵是“‘脫兔’正與‘金彈’同歸,而‘活法’復與‘圓’一致。圓言其體,譬如金彈;活言其用,譬如脫兔。”[1](p438)兔擺脫了束縛,當然就“縱橫無不可”無可了。而“金彈”的本質特性就是“圓”和“活”,就是“古人作詩有成法,句欲圓轉字欲活”。[1](p433)既然“活法”與“圓”一致,錢鐘書就參照《文心雕龍》中對“圓”的闡述來理解“活法”,“活法”應體現在五個方面:體勢要“自轉”(《定勢》);結構要“圓合”(《熔裁》);事理要“圓密”(《麗辭》);辭句要“通圓”(《論說》);聲韻要“轉圓”(《聲律》)。
針對呂本中的“活法”:“規矩具備,而出于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于規矩。”錢鐘書作了這樣的闡發:前后兩語“乍視之若有語病,既‘出規矩外’,安能‘不背規矩’。細按之則兩語非互釋重言,乃更端相輔。前語謂越規矩而有沖天破壁之奇,后句謂守規矩而無束手縛腳之窘;要之非抹殺規矩而能神明乎規矩,能適合規矩而非拘攣乎規矩。東坡《書吳道子畫后》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后語略同于東萊前語,其前語略同于東萊后語。陸士衡《文賦》:‘雖離方而遁員,期窮形而盡相’,正東萊前語之旨也。東萊后語猶《論語·為政》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恩格斯詮黑格爾所謂‘自由即規律之認識’。”[1](p439)可見,錢鐘書所理解的“活法”的核心是“變”,“活法”就是“變法”,但“變”要遵循一定的規矩而不能越出規定的范圍,猶如“明珠走盤而不出于盤”、“駿馬行蟻封而不蹉跌”。[1](p439)
在《管錐編》中,錢鐘書又對“活法”理論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引東坡《書吳道子畫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認為這是“不囿陳規,力破余地”,“才氣雄豪不局趣于律度,邁越規矩,無法有法”。“規矩拘縛,不得盡才逞意,乃縱心放筆,及其至也,縱放即成規矩”。“破壞規矩乃精益求精之一術”。[5](p1193)接著又用蘇轍《汝
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稱贊孫遇畫為“縱橫放肆,出于法度之外”,而又“有縱心不逾矩之妙”來比勘“活法”。又引黃伯思《東觀余論》卷上《論張長史書》評張旭的草書曰:“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內。”由此可見,錢鐘書所理解的“活法”不僅僅用于論詩,也運用于其他藝術,“活法”是一種廣泛的文藝觀。[5](p1193—1194)
錢鐘書還對“活法”理論作了補充與生發:詩人應該深入到生活實際當中去進行體驗,將心中的感觸和真實情感傳達出來,就是參活句,就不會落入前人的窠臼。如果“生吞活剝,句剽字竊,有如明七子所為,似者不是,豈非活句死參”?[1](p100)因此他十分贊賞楊萬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呂本中提出來的口號,意思是要詩人又不破壞規矩,又能夠變化不測,給讀者以圓轉而‘不費力’的印象。楊萬里所謂的‘活法’當然也包含有這種規律和自由的統一,但是還不僅如此。根據他的實踐以及‘萬象畢來’、‘生擒活捉’等話看來,可以說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親母子的骨肉關系,要恢復耳目觀感的天真狀態。”[3](p161)在這種理論的支配下,錢鐘書以為“蓋藝之至者,縱心所欲,而不逾矩;師天寫實,而犁然有當于新;師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1](p61)
作詩、論詩有貴活句賤死句之說,錢鐘書認為,除此之外,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別。讀詩過泥,也是死參,故讀詩也有圓熟的問題,不能過于拘泥于字面意義的闡釋。他指出古人“謂切題而無寄托者為‘死句’,僅知作詩有活句死句之別,而不知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茍能活參,斯可以作活句。譬如讀‘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而曰‘鵝豈不先知’便是死在句下。”[1](p305)可見,詩句的所謂“死活”除了作法之外,與讀者是否善于參與和鑒賞也有密切的關系。
4、脫胎換骨與點鐵成金
“奪胎”、“換骨”出自釋惠洪的《冷齋夜話》卷一,“點鐵成金”出自《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洪駒父書》。錢鐘書說這兩句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黃庭堅本人的風格和“山谷詩擅使事,以古語道今情”的特點,[1](p107)也算得上是江西派的綱領。“脫胎換骨”與“點鐵成金”之說,前人的批評是十分尖刻和嚴厲的,如金代王若虛曾云:“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6](p523)對宋詩作詩之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法,錢鐘書從用事與用辭方面進行剖析:如黃庭堅詩《演雅》:“絡緯何嘗省機織,布谷未應勤種播。”錢鐘書認為他的辭義出自《詩經·大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萁,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葛洪《抱樸子》外篇《博喻》有:“鋸齒不能咀嚼,萁舌不能辨味”一節等,這是“黃山谷承人機杼,自成組織,所謂‘奪胎換骨’者也。”[1](p6)錢鐘書又以蘇軾詩為例,說蘇詩多從唐詩那里推陳出新,如《東欄梨花》:“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錢鐘書引用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說它出自杜牧的“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憑欄干。”《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錢氏指出它化自香山之《惜牡丹》詩:“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另有李商隱“酒醒夜闌人散后,更持紅燭賞殘花。”經過對照與比勘,可見蘇軾對唐詩的生發和點化,故錢鐘書說:“唐人衰颯之語,一入東坡筆下,便爾旖旎纏綿,真所謂點鐵成金、脫胎換骨者也。”[1](p121)
對王安石詩的用辭,錢鐘書也進行了取心析骨的挖掘和解剖,通過對荊公詩大量事例的分析,在《談藝錄》中,錢鐘書向我們展示了王安石詩“偷語”、“偷意”、“偷勢”的很多例子,其中不乏“點鐵成金”者,但也不可否認,“點金成鐵,亦復有之。”[1](p445)錢氏指出,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1](p245)王安石脫胎換骨的辦法是儲存古人佳語,“占盡新詞妙句”,“代為保管”,“挪移采折”,甚至“久假不歸”。技巧是“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襲,或反案。”[1](p247)從而做到“語言有色澤、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讀者對詩的內容做更多的尋味”。[3](p43)因此,“后來宋詩的形式主義是他培養了根芽,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匯和典故的游戲、測驗學問的考題,借典故來講當前的情事”。[3](p41)
與“脫胎換骨”、“點鐵成金”密切相關和相通的是“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這兩句著名詩論見于黃庭堅的《山谷內集詩注》十二《次韻楊明叔并
引》,是黃庭堅論詩的妙旨,并為江西詩派所詠傳。經過考證,錢鐘書以為這兩句話最早出于梅堯臣之口,而非黃庭堅,蘇軾在《東坡題跋》卷二《題柳子厚詩》之二也說:“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南宋初人早徵古而忘祖”,以為其為山谷詩法。在論述這兩句著名詩論時,錢鐘書先征引《南齊書·文學傳論》:“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其認為它的精神實質是以“新變”達到“代雄”,近似于“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文章怕寫得平凡,俗指平庸陳舊,變庸俗為雅正,變陳舊為清新,即是“使熟者生”,即是變舊為新。“使文者野”即使華偽的文辭變得誠樸。將庸俗的變為雅正的,將陳舊的變為清新的,離不開選材取境,錢鐘書指出蘇軾僅在用事“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是有局限的,若在選材取境上“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則沒有局限。為更好地說明“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錢鐘書把它與陌生化的原則相對照:
近世俄國形式主義文評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為文詞最易襲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須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竊謂圣俞二語夙悟先覺。夫以故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謂之使野者文,驅使野言,俾入文語,納俗于雅爾。……抑不獨修詞為然,選材取境,亦復如是。歌德、諾瓦利斯、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雪萊、狄更斯、福樓拜、尼采、巴斯可里皆言觀事體物,當以故為新,即熟見生。[1](p320--321)
可見,“宋人詩好鉤新摘異,炫博矜奇”,[1](p207)是由于宋詩在修辭、選材、取境上做到了“新變”,而后與唐詩相頡頏并平分詩國秋色。從錢鐘書對宋詩詩學的見解中,不難發現,他對一些問題的總結和闡述,每每能一反流俗,在眾人的批判之處,拈出其長處,在眾人的尊奉之處發掘其不足。這對我們全面正確地認識宋詩的特點,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新人耳目的理論意義。
三、宋詩名家的精當評論
陸游是宋詩乃至中國詩史上作品數量最多、影響也很大的詩人,這自然引起了錢鐘書的充分關注。他在分析陸游詩時,首先抓著放翁詩藝的特點是“人所曾言,我擅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1](p118)如《游山西村》:“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來自強彥文寫紹興的風景詩:“遠山初見疑無路,取經徐行漸有村。”經過陸游的改造,詩的形象變的鮮明了,并蘊涵了豐富的人生哲理。陸游的寫景詩,錢鐘書贊揚不已:“放翁擅寫景”,“如畫圖之工筆”,[1](p118)“其模山范水,批風抹月,美備妙具,沾丐后人者不淺。每有流傳寫景妙句,實自放翁隱發之者”[1](p131)對放翁律詩工飭溫潤的特點,錢鐘書于《后村詩話》所評“古人好對仗,被放翁使盡”深以為然,并稱贊“放翁比偶組運之妙,冠冕兩宋”。[1](p118)于放翁詩所受影響的源流,錢鐘書敏銳地意識到“《劍南集》中詩,有顯仿宛陵者”。[1](p115)并進而指出,陸游《題蕭彥毓詩卷》、《夜坐示桑甥》、《讀近人詩》等所體現的詩學思想均來源于梅堯臣的《讀邵不疑詩卷》“作詩無古今,惟早平淡難。”盡管放翁口頭上批評晚唐,“違心作高論”,“鄙夷晚唐”,[1](p123)但錢鐘書發現他是“喬坐衙態,呵斥晚唐”,[1](p125)“放翁五七言律寫景敘事之工細圓勻者,與中晚唐人如香山(白居易)、浪仙(賈島)、飛卿(溫庭筠)、表圣(司空圖)、武功(姚合)、玄英(方干)格調皆極相似,又不特近丁卯(許渾)而已”。[1](p124)對放翁的愛國詩,錢鐘書也準確地揭示了他的顯著特征:“他不但寫愛國、憂國的情緒,并且聲明報國、衛國的膽量和決心。”“愛國情緒飽和在陸游的整個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3](p171--172)“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于君國之思。”[1](p123)這和楊萬里等人相比顯然是不同的。
但錢鐘書并不因為陸游是偉大詩人而采取“諱尊”的方法來曲意衛護,他客觀地指出了放翁詩的不足與弊病:在制題、取境方面“寬泛因襲,千篇一律”。[1](p128)“詩中議論,亦復同病。”[1](p128)“意境實鮮變化”,“心思句法,復出互見”。[1](p125)“吟弄酬應之什,仍復層見疊出”。[1](p126)在藝術形式上:“似先組織對仗,然后拆補完篇,遂失檢點”。“八句之中,啼笑雜遝,兩聯之內,典實叢疊,于首擊尾應、尺接寸附之旨,相去甚遠。文氣不接,字面相犯。”“雖以其才大思巧,善于泯跡藏拙,而湊填之恨,每不可掩。”[1](p127)
對陸游詩隨意粗疏的不足,錢鐘書批評道:“一時興到,越世高談,不獨說詩。自語相違,慨然不惜。”[1](p451)其談兵詩“自負甚高,視事甚易”,“氣粗言語大,偶一觸緒取快,不失為豪情壯概。顧乃丁寧反復,看鏡頻嘆勛業,撫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遠略、奇謀妙算,……不僅‘作態’,抑且‘作假’也。”[1](p457)還批評了放翁詩中“有二癡事:好譽兒,好說夢。兒實庸才,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1](p132)從對陸游的公正評判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學者的寬廣胸襟和氣度。
此外,他對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朱熹等人的詩作,均有切當獨到的闡述和解析,尤其對他們詩歌藝術的總結與批評,對我們全面地評價宋詩的特征,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
總之,錢鐘書對宋詩的研究無論是宏觀的透視,還是具體問題的個案分析,都能從別樣的視角切入,議論精彩,見解卓越,啟人甚多,在學術史上頗有益人神智的詩學價值與理論意義。
[1]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2]敏澤.論錢學的基本精神和歷史貢獻——紀念鐘書先生[J].文學評論1999.(3)
[3]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4]錢鐘書散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5]錢鐘書.管錐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王若虛.滹南詩話[A].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責任編輯:萬吉星

曹 悅 白魚口60x60cm 布面油畫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