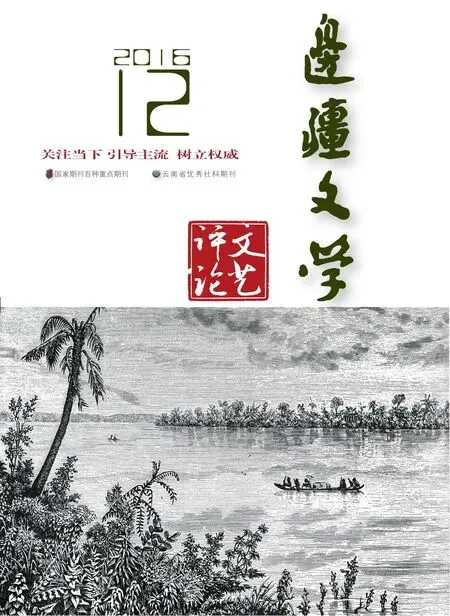這是一個真的人:方巖印象記
◎黃孝陽
這是一個真的人:方巖印象記
◎黃孝陽
青年批評家
主持人語:我和方巖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四批客座研究員,一年多的客座,我們常到各地參加各類會議,說實話,每次開會誰發言講了什么,似乎都忘記了。但每次朋友們聚在一起喝酒,酒桌上漫天飛舞的段子,卻總是歷歷在目。方巖喝起酒來從不偷奸耍滑,并且極為豪爽,最為重要的是,他有著童真之趣,似乎有顆孩童般的善良的心。他的文章寫得很嚴謹,立意也頗高,視野也很寬。他在和我的對話中說,希望自己四十歲寫的文章在他六十歲后還有人讀,其實,這是一個對自己很高的要求,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文章肯定會有人一直讀,一直讀的。(周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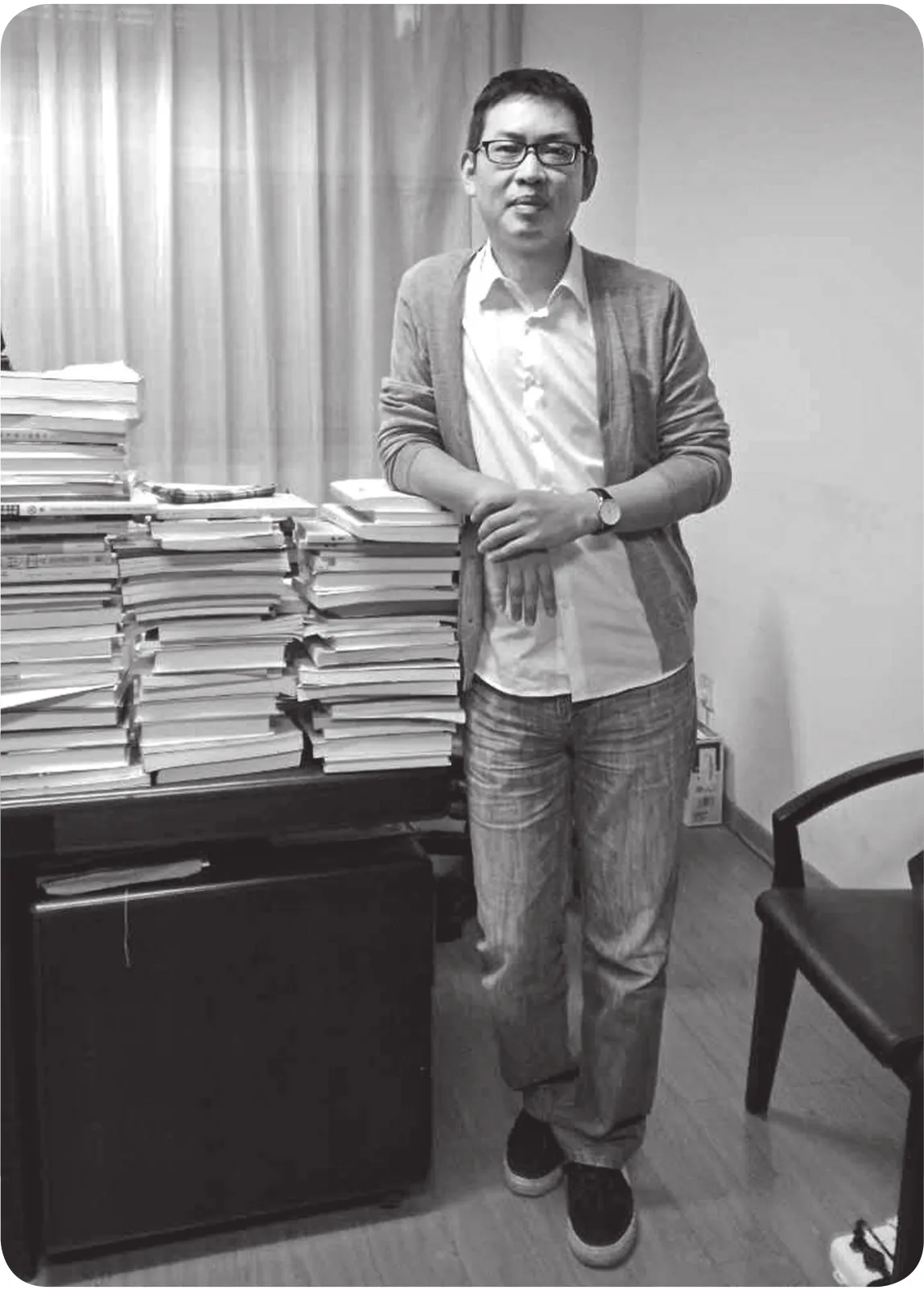
方巖 男,1981年12月出生,安徽六安霍邱人。青年批評家,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1997年至2013年間輾轉于四所大學,或為學生或為老師,現就職于江蘇省作家協會《揚子江評論》。主業編輯,副業文學批評。曾獲安徽省首屆優秀碩士論文獎(2008年)、《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2014年)、江蘇省紫金文藝評論獎(2016年)。
我對方巖的熟悉是在一次游戲中。是殺人游戲。
十幾個年輕人在一個賓館房間里,基本坐著,就他躺著,還脫了鞋,居然沒異味。眼神還那樣天真無辜——哪怕最后被揭穿兇手的身份,眼神還是這樣,就好像在“天黑請閉眼”時他沒殺過人。他的口才與邏輯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心理素質與表演能力是超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顏值與他所從事的這個文學批評行當有點不搭,完全就是現在公眾語境里的“小鮮肉”,完全迥異于我們對文學批評家形象的那種苦大仇深的傳統想象。
這樣一個年輕人的舞臺應該是在屏幕那兒,那里的掌聲會對得起他顏值與智商。他跑到文學批評這個行當里來想干什么?難道是想體驗人生有多么寂寞嗎?
就有了與他相對深入聊天的機會。
在會后的餐敘中,我隨口問他對剛出版的幾本名家新作的看法。結果他的直言不諱還真是把我給驚著了。我小心翼翼地問,“你在文章里也這么寫?”
他睜大了眼睛,似乎不大能理解我的問題。他在尋找著合適的措詞。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愚蠢。我的問題,對他來說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
他掏出手機,把他的幾篇文章通過微信發給了我。
“當然這么寫啊。”他終于快活地笑起來,拿起筷子敲打白色的餐盤,又補充道,“我希望自己的批評能成為一種寫作,而寫作本身可以介入更多的領域。我現在其實就是通過寫作來摸索文體和表達的問題。比文學更值得關心的事情多了——我不是想說文學不重要,而是因為我們當下討論文學的方式降低了文學的重要性,傷害了文學。”
午后的陽光照進餐廳,照耀著這個如夢似幻的現實。他的樣子異常干凈,音樂的聲音在他手下叮當流出。
我想到了“赤子之心”這個詞語。
我沉默下來。我心澎湃如昨。
這些年我見過許多文學批評家,私下聊天臧否人物是一回事,寫評論激揚文字又是另一回事。臺下“垃圾”之聲不絕于耳,臺上“鮮花”之頌浩浩蕩蕩。在我們看來,這是正常的,是一個成人社會不言而喻的游戲規則,甚至不妨說是一個情商高的表現。
“在這樣一個體制下,誰不是犬儒者加機會主義者呢?我們都要活著,活好一點。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吧。”一個大V曾與我推心置腹。我懂得他的語重心長,但,真的很煩啊。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活著,不是只有犬儒這一種活法;“一簞食,一瓢飲”也能活好。人類史更沒有在余華那本《活著》處終結。把什么問題都推給體制,不僅是道德上的混亂與匱乏,也還是一種知識上的偷懶與無能。我不喜歡這一小勺廉價的內心實質不知所措的雞湯。
在這樣一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人子當有他的光芒。
而這首先要去求真。
我把方巖發來的文章仔細讀了,又去網上搜索了關于他的更多文章。我不能說他的目光有多么敏銳深刻,視野有多么開闊非凡,觀點有多么復雜深邃,結構有多么雄渾深厚,以及他對每部作品特點、意義、場景的解讀有多么準確精致,啟人深思……我當然可以把這些詞語毫無吝惜地贈送給他,反正不是我發明
的它們,反正它們早多半淪為逢場作戲的陳詞濫調。但我做不出來。因為他的文章在這里,有著刺疼雙目的真,真正的真。
我是多么迷戀“真”這個字啊。
沒有真誠之心,真摯之意,真切之法,哪來的真相、真實、真理,哪來腹內的那輪驕陽?
方巖的文字讓我重新感受到真的力量及其衍生的美感。
他嘗試著去理解人子中間那些隱秘而偉大的情感、經驗,結合歷史深處的秘密和囈語,當代各門學科所貢獻的理性與知識,構成我們日常的眾多細節、繁華表象,以及此時代諸多秘而不宣的肌質、紋理,來辨析一個文本的真偽好壞,并借助于它們來論述 “中產階級的文化幼稚病” ,“改革開放后出生、市場經濟體制下成長的一代人的某些精神狀態”,等等命題。
我也不能說方巖的論述有多么振聾發饋。我已經過了一個被某個觀點“振聾發饋”的年齡。在人文學科領域,我是不大相信有一個要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猶如深藏于金伯利巖層的鉆石,等著人類去挖掘發現。而更讓我著迷的,或心生敬意的,是我們尋找真理的旅程,是關于這趟旅程的地圖與手札、祝祭與汗水等,所謂“路漫漫兮我上下求索”。
方巖表現出了這種潛質。在字里行間我讀到了他的情感與夢想,讀到了他的固執與專注,讀到了他的不討好自己與不逢迎別人。這些文字乃他的血肉分娩之物,雖然目前還不能稱為一座完美無缺的琉璃塔(這是一個令人恍惚、心生疑慮的意象),許多字詞段落還只處于一種構件狀態,但毫無疑問:
這是一個真的人。
這還是一個能抵抗世俗層面諸多誘惑、內心有著磐石的人。
也許哪天,這石里便躍出一個猴王。
我很喜歡方巖那篇《“卑賤意識”與作為歷史證言的文學批評》。文章不長,但是對文學批評價值、地位與意義的總體沉思。方巖借助黑格爾關于“個體意識與外部社會權力進入一種對抗、質疑的關系所產生的卑賤意識”,論證了文學批評擺脫對作品的依附性與從屬性(把作品當作中介)的可能性——在一個“歷史證言”的高度,獲得主體性;在一個“自由的言說和創造性的精神活動”的起點,獲得有效性;在一個觀念與思想層面的討論,獲得公共性;在一個以文學為土壤的言說空間,獲得共振性。
主體性,有效性,公共性與共振性,構成一個自洽的國度。
這是方巖對文學批評的渴望。為此他不惜清算了當下兩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批評模式,又繼而清算了自我,還提出了一個面目依稀可見的方法論。邏輯大致如下:
1. 今天我們談論的“文學”“哲學”“歷史”,是一個現代性話語建構的結果。在文學內部談論文學,基本上不大可能擺脫已有某種理論和某個概念的策縛(這已經提前預設了批評論述過程和價值判斷),以及面向文學史的價值招魂。
2.能否來到“文學”外面,在一個“哲學”“歷史”的角度,或者說回到一個“文史哲不分家”的角度,又或者說在一個人文學科外面審視文學(這個“又或者說”是我的添加)?
也說一點意見,并不一定對。
這些年,有兩句話很流行,一句話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于《詩經》;另外一句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出自于《華嚴經》。
什么是初心?在我的理解里,無外乎,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發現這個世界的更多奇妙,以及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等等。
方巖希望自己的寫作,能通過文學批評這種文體,介入更多的領域。所以他辯護與自我辯護,所以他找來黑格爾、阿蘭·巴迪鷗、薩義德、以賽亞·柏林等大師,為這些辯護詞背書。這固然是學院知識生產體系嚴謹與規范性的要求,但我還是希望有一天,他把大師們都忘掉,把一篇文章的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等都忘掉,就站在一個人的立場,基于一個國族的經驗與傳承,用一個世界文學的視野與高度,以一個獨與天地往來的格局,踏足自由之境,書寫文字與夢想。
我知禮法,但禮法豈為我輩所設。
我輩當以植物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我輩當以動物的精神,披毛帶甲,橫沖直撞。
那時,如果說文學作品是一種價值,那么我相信,文學批評就是“創造價值的價值”。
(作者系江蘇文藝出版社圖書編輯室主任)
責任編輯: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