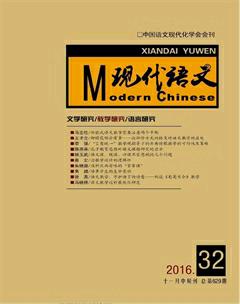《望江南》“想象”教學分析
鐘菊蓮+姚莉
小令是元代散曲的一種,雖然篇幅極為短小,表達的意蘊卻十分豐富。同時,因其寫作內(nèi)容及語言風格與學生現(xiàn)有的閱歷及語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給小令的教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溫庭筠的小令《望江南》,就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個字,卻寫出了一位飽受相思之苦的思婦形象,這一點對于學生來說是很容易就能感受到的。但如何深入人物內(nèi)心,感受人物情感的變化,卻是這首小令教學中的難點。
孫紹振在《名作細讀》中說:“詩人調(diào)動讀者的想像來參與,卻并不提供信息的全部,他只提供了最有特點的細部,把其他部分留給讀者去想象,讓讀者用自己的經(jīng)驗去補充。”《望江南》這首小令恰好是一首簡短又值得挖掘的小令,它的語言就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它抓住了最有特點的部分,在特點以外留下空白供人想像。學習這首小令,關(guān)鍵是要有效地調(diào)動學生的想像。在教學過程中,我選取了兩個頗有特點的細節(jié),根據(jù)詞中的內(nèi)容,引導學生在閱讀中通過想像來走近人物,深入思考,品出滋味,體會到了作品中人物細微的情感變化。
一、對人物行為進行想像
起句“梳洗罷”,意思是“梳洗打扮好了之后”,很簡單平常的一個生活細節(jié),看似平平。
可若將“梳洗”二字細加品味,會引出頗多遐思:這是一位怎樣的女子?她會怎樣梳洗打扮?梳洗打扮好了之后準備做什么?當把這些思考向?qū)W生提出來時,學生的思維頓時活躍了起來:有的說,這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會像《木蘭辭》中寫的一樣“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打扮好了之后準備去望江樓等她的丈夫;有的說:這應該是一個長得很消瘦的女子,她的梳洗打扮應該不是濃妝艷抹,而只是打扮的干凈得體就好了,她等的也不一定是丈夫,可能是分別已久的心上人;有的說,這是一個雖用心打扮,但仍然遮不住滿臉憔悴之色的女子,她去等待久盼不歸的心上人……學生的想像不僅貼合文本,而且將思婦的形象具體化,可感化。這時,再讓學生去深入想像并感受思婦等待時的復雜心情,就簡單的多。這里引用其中一位學生對思婦心情變化的描述:又是一個清晨,思婦早早起床梳妝,一切收拾整齊之后,便滿懷希望,甚至有點興奮地登上了高高的望江樓,倚欄凝眸,憑欄遠眺,滿目是期待的柔情。希望隨著漸近的船兒越來越強烈,但屢次的失望,讓她開始顯得焦躁不安。時間在不停的推移,這一天猶如無數(shù)個前一天,是周而復始的由希望到失望。她斜倚欄桿的身影開始顯得疲憊,內(nèi)心的痛苦煎熬讓她臉上浮現(xiàn)出孤寂落寞的神情。
《戰(zhàn)國策》中道“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蘇軾在《江城子》中,也是以“小軒窗,正梳妝”寫出了懷念妻子王弗時的繾綣深情。但《望江南》中的思婦雖著意修飾,卻是顧影自憐。從“梳洗罷”的情節(jié)想像中,不難體會到她內(nèi)心的期盼,滿懷熱烈的希望,希望中的美好日子好像即將到來,孤寂獨居的生活好像就要結(jié)束。可當熱烈的希望不止一次地破滅,冰冷的現(xiàn)實只會讓她的孤寂變得更加刻骨。正是學生對特定人物——思婦的行為進行了想像,才深切體會到人物內(nèi)心由希望到失望的,極其微妙的心理變化。
感悟這首小令,不在字面意思,而在詞句背后的情味和意蘊。引領(lǐng)學生讀出詞句背后的那份情、那段愛、那顆心、那種味,讓學生以自己獨有的想像去品味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就是還學生以真正意義上的“讀者”地位。
二、對特有情境進行想像
小令中的“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一句,是最能令人生發(fā)想像出一幅鮮活畫面,一幕立體場景的句子,也是感悟人物獨特心靈的關(guān)鍵句子。
“過盡千帆皆不是”,表面上是寫景:來來往往的帆船有很多,卻沒有一葉是思婦所要等待的。這樣的解讀未免有些輕描淡寫。稍加推敲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句其實寫的是思婦內(nèi)心希望與失望交替的過程,是與“梳洗罷”恰好相反的心境。在教學中,我問學生:“你們能不能發(fā)揮想象,用自己優(yōu)美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來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境?其中要加入適當?shù)摹⒑侠淼摹⒂嘘P(guān)人物的描述。”學生的想像描述是令人驚喜的:有的說,這是一個緊蹙眉頭,倚欄遠眺的女子,遠遠看見帆影,她便引頸長望,心兒隨著船的漸行漸近而漸漸緊張,希望也漸漸高漲,可是船到樓頭卻無情地繼續(xù)前行,當她意識到這并不是她等待的船兒時,她變得非常失望;有的說,可是這時的她還沒有完全失望,幻想促使她把目光再次投向遠方,眼里重新充滿期待,只是臉上的神情顯得更焦急了;有的說,她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倚欄張望,等待,發(fā)髻都被將風吹亂了,她也毫無察覺,就這樣,直到夕陽斜掛天際,微弱的斜暉就像含情的雙眸,一天又過去了,悠悠的流水就像是思婦的青春年華,毫不留情地逝去,更像是思婦心中久盼不歸的憂愁,綿綿不絕……就這樣,學生在情境的想像中,仿佛看到了思婦的神情由原來的滿懷期待,而變得蒼白凝重,讀出了人物內(nèi)心無數(shù)希望與失望的交替,感受到了她內(nèi)心的摧傷越來越慘重,體會到了她內(nèi)心的無比落寞。這樣的想像描述,體現(xiàn)出了學生與文本人物之間心靈的碰撞。學生有了這樣的想像,才能真正體會思婦盼望的時間之久,她的癡情和執(zhí)著,以及內(nèi)心的痛苦煎熬。
“千帆”是“千船”的代指,但這又不僅僅是修辭方法的差別。船在水上,越向遠處,越是只能看到帆而不是船。李白的“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寫的是去船,把它倒過來,不就是這位思婦盼望來船的過程么?所以,一個“帆”字把讀者的目光引領(lǐng)到了遠處,使讀者也像詞中的思婦一樣極目遠望,企盼人歸。而“水悠悠”三個字,更是讓我們聯(lián)想到古詩詞中眾多以水寫愁的名句,如李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寫出了愁的情狀,將無窮的憂愁和不盡的流水相聯(lián)系;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寫出了愁的長度,將水的綿長悠遠和人情緒上的愁苦統(tǒng)一了起來;李清照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寫出了愁的重量,通過水中之舟,間接道出了愁的沉重壓抑……水的悠悠不絕和愁的千絲萬縷的特點是相吻合的。正是對“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這一情境的想像再現(xiàn),才使學生切實體會到了人物內(nèi)心由原本“梳洗罷”時的歡快,滿懷希望,變得空寂焦急,最終失望,內(nèi)心滿是綿綿的憂愁。獨特的情緒體驗形成對照,鮮明而強烈。
通過這次想像教學在《望江南》教學中的運用,學生賞析詩詞的能力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他們對于這首小令中的留白,能夠?qū)W會去捕捉,并用貼合文本的想像去填空,最終真正體會到了人物內(nèi)心的獨特情感。小令是能激發(fā)學生想像力的,有感染力的作品,很多詩詞同樣也有這些特點。沒有想像,就沒有詩歌。所以進入想像,通過想像來走進詩詞,把自己的感情和經(jīng)驗投入到文本的理解中去,一起參與創(chuàng)造,應該是閱讀詩詞作品具體的、可行的、有效的方法之一。
(鐘菊蓮 姚莉 浙江衢州華茂外國語學校 3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