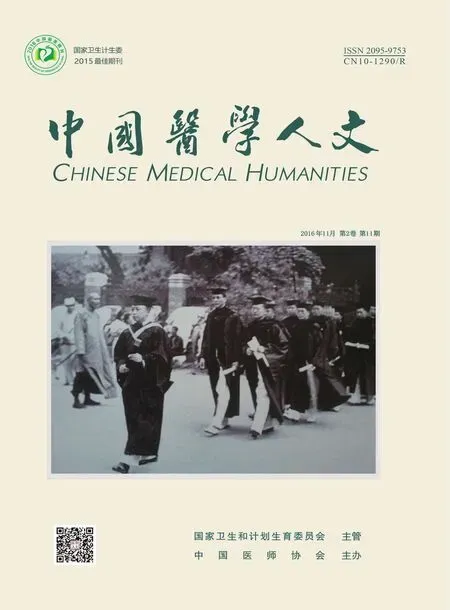返璞歸真
文/羅思敏
返璞歸真
現代醫學一日千里,世界各地近乎每天都會有科研論文發布,接著就是新藥物及新技術的誕生,因此前線醫生必須持續進修,才能緊貼如雨后春筍般的臨床實證醫學。就好像我現在每天處方給糖尿病患者的藥物,跟我當年在醫學院所學習的已經大有不同。不過,并不是所有的醫學范疇都需要天天創新的,有一種現象,其珍貴在于回歸自然,這就是“醫學人文精神”。
前陣子應中國醫師協會的邀請,前往哈爾濱出席人文醫學年會作一個專題報告。這次最難能可貴的,就是有幸聆聽到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秦伯益發人心省的講學,題目為:呼喚醫學人文精神的回歸,其內容涉及醫學社會學的歷史、現狀及前瞻,遠超越臨床診癥的微觀層面知識,因此愿與諸位讀者分享。
還看中西歷史
回顧歷史,不少社會運動也是呼喚人們,要回歸到從前被視為珍貴的精神,從而達到社會持續健康的進步,好像十四至十七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提倡恢復古希臘、古羅馬文化,提出人本主義思想體系,使人性回歸及個性解放;而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則批判中世紀蒙昧主義,使理性回歸,從而煥發創造性,促進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及社會革命的互動,除了為法國大革命奠下充分的思想準備,其影響遠至中國近代的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
至于古代的醫藥先賢,如扁鵲、華佗、張仲景、孫思邈及李時珍等,他們從醫的目的皆是懸壺濟世、治病救人,實現醫患和睦,把醫(醫治)、教(教學)、研(研究)三者結合。我再翻查資料,在眾位醫藥先賢之中,相信東漢張仲景的故事,最能夠令日常身兼繁重行政工作的醫生們反思:據說張仲景從小厭惡官場、輕視仕途,無奈要在世襲制度下被封為長沙太守。他為了留守前線,以醫術為百姓解除病痛,擇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大開衙門,不問政事,坐在衙門大堂為百姓治病,得到百姓的愛戴,然而也令張仲景成為了當時主流社會的異類,從他的著作中仿佛就感受到其憤世嫉俗的悲嘆。由于當時政局不穩,張仲景最后辭官隱居,終于寫成臨床醫學的驚世巨著,為后世中醫學作出重大貢獻。至于唐代的孫思邈,同樣重視醫德修養,在他的著作里早已系統性地論述了醫德規范,強調醫生必須擁有精湛的醫術及高尚的品德,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醫生,見到任何層次失調,就理應去嘗試治療,這里的“失調”指人體失調,以至整個社會失調。反觀當代醫學,硬件建設和物質條件當然有著明顯的進步,我們現在隨手可得的抗生素、預防疫苗,以及如磁力共振檢查及器官移植手術等高超的技術,都是古代先賢完全沒有的。可是秦伯益院士認為,當代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內涵卻明顯在退步,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
秦伯益院士認為當代中國醫學人文精神倒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是醫學科學本身的變化。究竟醫生行醫的目的,仍然是如上文提及的懸壺濟世,還是把治病視為謀生手段呢?我接著反思,究竟最能夠令一位醫生欣慰的,是每位病人步出診癥室時抒懷的笑容,或者是以自己能夠登上月球人或星球人之列為榮呢?又還是在成為月球人或星球人之后, 同時一樣會為病人的笑容而欣喜呢? (注:月球人和星球人泛指一個月或一星期賺到一球即一百萬的人士)
在醫學的領域上,學科的分工也越來越細致,一方面專業化有助提升各種技術,這當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一個整體的病人卻越來越被碎片化了。我作為家庭醫生,有時候會遇到一些病人,一進診癥室便拿出一張寫滿五至六種不同身體部位不適的字條逐一求診,包括頭痛、失眠、流鼻水、胃氣脹、偶爾腳痹及跟老公吵架很傷心等等。如果診所工作量繁忙到一種程度,連醫生喝水及上廁所的時間也欠奉的時候,遇見這種病人容易令醫生心里一沉也是不難理解,因為盡管醫生有著菩薩心腸及神仙妙手,也很難在五分鐘之內為病人解決六種身體病征。然而,當客觀的環境因素令醫生可以擁有合理的行醫環境時,例如北歐國家擁有較為健全的基層醫療體系,令當地醫生的工作與生活得到平衡。作為家庭醫生,當看見眼前的病人,把身、心、社、靈所有的失調全部告知自己,熱切寄望能得到治愈之時,如果我們有能力把六塊碎片重新整合為一個人,不枉眼前病人對我們的信任,這不正就是我們應該引以為榮的事情嗎?
在這次東北之行的最后一天,我獨自騎著單車,在松花江北欣賞太陽島的風景,不禁想起一個月前在丹麥的綠色國土之上,見到當地居民多以單車代步的實況及反璞歸真的民風。其實,需要呼喚回歸的,又豈止于醫學人文精神呢?

專 注 攝影/馬小平
(本文曾刊于2016年8月11日香港《信報》)
/香港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