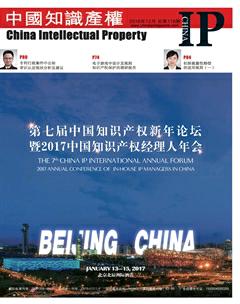掀起“專利操控實(shí)體”(PAE)的蓋頭來,看到了什么?
孫遠(yuǎn)釗
鑒于PAE本身的復(fù)雜性與不同的商業(yè)運(yùn)營模式,即使目前已經(jīng)有了比較清晰的畫面得以向世人呈現(xiàn),但也產(chǎn)生了更多待決的問題,從而需要更進(jìn)一步的調(diào)研。
背景:各方紛陳、實(shí)證不足
如果要舉行一個選拔,讓各界挑出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最受關(guān)注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問題,那么“專利非實(shí)施實(shí)體”(patent non-practicing entities,NPEs,也就是過去俗稱的“專利流氓”,patent trolls)的現(xiàn)象定然會榜上有名,而且還可能名列前茅。到目前為止,雖然這還是一個主要發(fā)生在美國的現(xiàn)象,其境內(nèi)已有十幾萬家企業(yè)成為專利侵權(quán)訴訟的被威脅對象,許多中國企業(yè)也受到波及,并因此付出了相當(dāng)高昂的和解金或損害賠償與訴訟費(fèi)用。
由于“專利非實(shí)施實(shí)體”并非十惡不赦,在過去還曾一度活絡(luò)了國際技術(shù)市場的交易,而且在另一方面又極難對其定義,甚至可能包括大學(xué)與研究機(jī)構(gòu)在內(nèi)(因?yàn)樗鼈兓旧弦膊粡氖庐a(chǎn)品的制造,而且有著非常活躍的交易活動,如專利許可等),奧巴馬政府為了聚焦專門以少數(shù)專利從事侵權(quán)訴訟威脅的活動,另外創(chuàng)設(shè)了一個名詞,把“有問題”的稱為“專利操控實(shí)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 PAEs,言外之意就是想以此來區(qū)別“好的”與“壞的”NPEs),并以白宮的名義在2013年出臺了一份報告書,準(zhǔn)備采取一系列的舉措來遏止這個現(xiàn)象的繼續(xù)蔓延。
美國國會也不遑多讓。雖然兩院的多數(shù)成員都是共和黨籍,與奧巴馬總統(tǒng)一向多有歧見,但在這個問題上卻頗有共識,其也是從同年(第113屆會期)開始強(qiáng)力推動立法,試圖對這個現(xiàn)象予以規(guī)制。而且連許多州也開始有所行動。雖然在憲法的結(jié)構(gòu)上專利問題是完全屬于聯(lián)邦的管轄范圍的,然而如弗蒙特州(Vermont)等還是通過了立法,甚至毫不避諱地直接稱為《專利流氓防止法》(Patent Troll Prevention Act)。1至于國會的相關(guān)立法工作雖然在開始時勢不可擋,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已是胎死腹中,主要原因是許多代表性的企業(yè)紛紛舉旗反對。它們認(rèn)為,專利維權(quán)本來就是天經(jīng)地義;如果對于PAEs做出各種限制或要求,事實(shí)上也就是對訴訟維權(quán)本身做出了各種額外的限制或要求,并牽動了整個體制中的微妙平衡,影響到未來的市場關(guān)系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
最新實(shí)證:PAEs鮮為人知的那些事兒
一項(xiàng)為各方所關(guān)注和期待的實(shí)證調(diào)研工作,是聯(lián)邦貿(mào)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從2014年9月15日開始依據(jù)《聯(lián)邦貿(mào)易委員會法》第6條所賦予的權(quán)力正式對28個業(yè)內(nèi)知名的PAEs展開的資料搜集與分析。鑒于絕大部分涉及到PAEs的專利爭議最后都是以和解收場,而雙方當(dāng)事人在和解時通常又會附簽一份保密協(xié)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因此外界根本無從知悉其中的具體內(nèi)容。但是FTC的調(diào)研卻完全不受此限制,這就讓FTC得以揭開PAE的面紗,搜集到大量的具體數(shù)據(jù)和資料來從事實(shí)證分析。
在歷經(jīng)了近兩年的調(diào)研后,F(xiàn)TC于2016年10月出臺了一份名為《專利操控實(shí)體活動:聯(lián)邦貿(mào)易委員會的一份調(diào)研》(Patent Assertion Entity Activity: An FTC Study)的報告。其中將PAEs依不同的商業(yè)運(yùn)營模式區(qū)分為“組合式PAE”(Portfolio PAE)與“訴訟式PAE”(Litigation PAE)兩類。前者是由投資人提供資金來累積成千上萬的專利組合、寄出威脅、警告或要求信函并協(xié)商許可協(xié)議。這一類占了調(diào)研對象的80%并獲得了約32億美元的許可收益。而后者則是依賴不超過由10個專利組成的組合來從事訴訟以獲取對其專利的許可和收益。這一類占了整個調(diào)研許可量的91%,一般而言能夠從每個被許可方獲取不到30萬美元的許可費(fèi)收益,并且還要與專利的讓與人(賣方)分紅。總體而言,它們占了調(diào)研對象的20%并獲得約8億美元的許可收益。此外,這類PAEs通常沒有正式的雇員,而且通過不同的層級安排設(shè)置了數(shù)百個關(guān)聯(lián)性的操作實(shí)體(外圍組織或機(jī)構(gòu))。就其所持有的專利期限而言,平均較“組合型PAE”所持有的要年長三歲。
一個有趣的發(fā)現(xiàn)是,雖然報告中想刻意對PAE和NPE做出區(qū)別,因?yàn)楹笳呖赡馨酥T如大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以及計算機(jī)芯片設(shè)計者等同樣從事各種技術(shù)轉(zhuǎn)讓活動的單位和個人,但報告中對于無線網(wǎng)絡(luò)的調(diào)研部分卻發(fā)現(xiàn),NPEs表現(xiàn)得時而像是“組合式PAE”,時而又像是“訴訟式PAE”。調(diào)研顯示,NPEs平均寄發(fā)了遠(yuǎn)比PAEs還多的警告信函,而多數(shù)的NPE許可費(fèi)收益是在30萬美元以下。
問題:PAEs是否違反競爭法規(guī)?
一個有趣的問題和現(xiàn)象是,作為聯(lián)邦反壟斷法的主要執(zhí)行機(jī)構(gòu)之一,聯(lián)邦貿(mào)易委員會在這份報告中卻通篇對于究竟PAE的行為是否抵觸了現(xiàn)行的反壟斷法規(guī)沒有采取明確的立場。這是因?yàn)樵诒徽{(diào)研的“組合式PAE”案例中,只有1%屬于標(biāo)準(zhǔn)必要專利(standard and essential patents, SEPs),從而應(yīng)符合標(biāo)準(zhǔn)設(shè)定組織以“公平/合理與非歧視性”(fair/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的待遇從事許可的要求和承諾。這個調(diào)研結(jié)果等于否定了過去外界認(rèn)為許多企業(yè)將其專利轉(zhuǎn)讓給PAEs是為了逃避F/RAND許可條件的猜測。
不過聯(lián)邦貿(mào)易委員會的主席伊迪絲?芮米瑞茲(Edith Ramirez)女士已經(jīng)表明,特定的PAE在建構(gòu)規(guī)模性專利組合的過程中如果涉及到許多替代性專利(substitute patents)的累積,那么就可能會觸發(fā)競爭法上的顧慮,因?yàn)檫@顯然很容易讓專利的持有者能對市場競爭造成“攔截”(hold-up)。不過在實(shí)踐中,至少從消費(fèi)者或使用者的視角來審查,要決定這種特定專利組合中的所有專利彼此間是否能從事合理的交換運(yùn)用往往是極度困難的。因此,該委員會的另一位委員莫琳?歐豪森(Maureen Ohlhausen)女士則表示,像這一類的專利組合事實(shí)上也有可能成為發(fā)明人與制造商之間的一個效能平臺,反而有助于推動更多的創(chuàng)新。她進(jìn)一步將專利組合中的內(nèi)容細(xì)化區(qū)別為“相當(dāng)可能為無效或不構(gòu)成侵權(quán)的專利”(從而會引發(fā)“攔截”效果并產(chǎn)生抵觸反壟斷法的顧慮)以及堅持忽略“適當(dāng)而且有益的專利”的企業(yè)但最終還是與PAE協(xié)商后達(dá)成許可協(xié)議等兩種情形。2
由此可見,鑒于PAE本身的復(fù)雜性與不同的商業(yè)運(yùn)營模式,即使目前已經(jīng)有了比較清晰的畫面得以向世人呈現(xiàn),但也產(chǎn)生了更多待決的問題,從而需要更進(jìn)一步的調(diào)研。尤其是無法徑行論斷是否任何的PAE,尤其是“組合式PAE”,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有違反反壟斷法的可能。縱使如此,這樣的不確定性無疑形同烏云罩頂,加上違反反壟斷法規(guī)的調(diào)查一向耗時耗資源,萬一成立,處罰也是極度嚴(yán)厲,顯然不是一向希望尋求速戰(zhàn)速決的PAE所想看到的。
除此之外,美國國會在2011年通過的《美國發(fā)明法》(America Invents Act,AIA)中的一些條款(例如只要案情內(nèi)涵稍有不同就必須分別起訴)和聯(lián)邦最高法院近年來的一系列判決(例如對于商業(yè)方法專利的大幅限縮、改變律師費(fèi)用的承擔(dān)規(guī)則等)都對PAE(尤其是“訴訟型PAE”)形成了相當(dāng)巨大的壓力。從相關(guān)案件的起訴數(shù)量已經(jīng)大幅下滑也可見一斑。即使如高智(Intellectual Venture)等具有代表性的“組合式PAE”也已經(jīng)做了大規(guī)模的轉(zhuǎn)型。PAE在美國的“榮景”顯然已大不如前。因此,為了本身的生存,一部分難以轉(zhuǎn)型的PAEs開始向美國境外發(fā)展,已是勢屬必然。
隱憂:中國版的PAE已然浮現(xiàn)
在中國境內(nèi)也早已有一些“個體戶”采取了類似“訴訟型PAE”的維權(quán)手法向不同的法院起訴,請求訴前禁令,并以此作為“要挾”被告和解賠償?shù)氖址ā>驮谧罱呀?jīng)看到國外一家知名的PAE選定到南京法院向索尼起訴專利侵權(quán),極有可能是想以此作為測試中國法院以及中國市場是否適合成為下一個PAE主要活動場所。
由于過去十幾年來施行的專利申請補(bǔ)貼政策,目前的市場上已充斥了無數(shù)的“垃圾專利”。隨著損害賠償金額持續(xù)向上調(diào)整、提高的趨勢日盛,訴訟費(fèi)用仍然相對低廉的現(xiàn)狀(因此即便在立案上必須一侵權(quán)設(shè)立一案),一旦相關(guān)的大氣候與小氣候分別形成,這些原本表面無用、在“鼓勵創(chuàng)新”的口號下所炮制出的各種專利相當(dāng)可能“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搖身一變成為“完美風(fēng)暴”,成為事實(shí)上阻礙創(chuàng)新的“地雷”。據(jù)媒體報道,目前,發(fā)改委已經(jīng)著手研擬規(guī)定,試圖未雨綢繆。然而可以預(yù)見的是,任何與此相關(guān)的規(guī)制草擬工作恐怕都會遭遇與美國之前面臨的相似問題與難點(diǎn)(差異處在于,美國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商業(yè)方法專利這一個環(huán)節(jié),而中國的潛在問題則是更為廣泛地分散在各個不同的技術(shù)領(lǐng)域),只要稍一不慎便會破壞整個體系的各種微妙平衡關(guān)系,給市場發(fā)展以及科技創(chuàng)新都帶來相當(dāng)不利的影響。
這絕非杞人憂天,更非危言聳聽。目前已到了需要進(jìn)一步全面整改現(xiàn)行的專利申請補(bǔ)貼政策并集思廣益以綢繆未來的關(guān)鍵時刻。機(jī)會稍縱即逝,思考與探索如何避免一場“完美風(fēng)暴”的形成,此其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