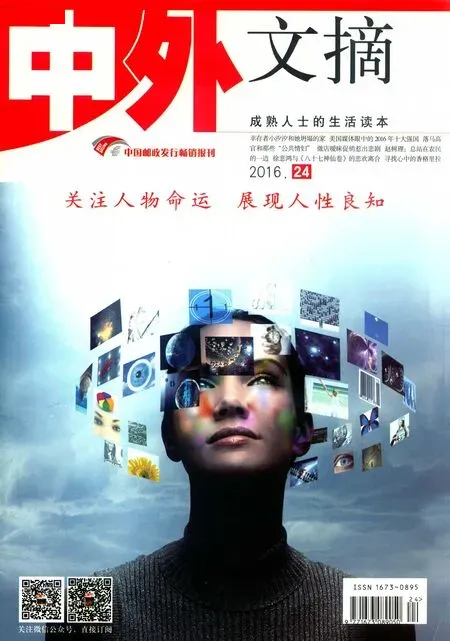風俗漸成“桎梏”
□ 閻連科
風俗漸成“桎梏”
□ 閻連科

其實,你真正到農村走走,到八億農民中了解了解,你會發現農村并沒有我們說的那種宏大的文化,而只有久遠的風俗。文化在風俗之中,風俗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組成,而文化是風俗的一個部分,是風俗表現出來的那些被人們捕捉到的晶體。電影是一種文化,這樣說不會產生異議,但把《紅高粱》中的顛轎一場戲也說成文化,未免把事情弄得過分的高深和復雜,說顛轎是風俗人人都懂了。
最能體現風俗的是鄉村節令。
立春為二十四節氣之首,有地方稱為“鞭春”,有地方亦稱“打春”。這一天,為了提醒百姓不誤農作耕耘和警旱防澇,從周代以后,就有了人扮春官、鞭打春牛的鄉俗儀式。
農歷二月,為驚蟄。驚蟄之后,昆蟲復蘇,龍為四靈之首,自然以為它是時令的先覺了。于是有了“二月二,龍抬頭”之說。于是,二月二這天晨時,農民要取灶中草木之灰,撒成一條灰線,“領龍”出來,保佑豐收平安,甚至還要唱些民謠。
清明節為掃墓添土之時,男須戴條帽,女插嫩柳枝,為的是“清明不戴柳,死了變成狗”——得有一個好的“托生”。
五月初五端午節,門楣插艾,以避瘟疫;喝雄黃酒,以避五毒;佩香袋,以避蛇蝎。還有五月十三的雨節,七月初七的七夕,八月十五的中秋,十月初一的寒衣節,十一月的冬至,以至臘月的臘八。這么多的節日,都是風俗在一個時期的一次集中體現。可以說,農民生活在風俗之中。只有不在風俗中的城市,沒有不在風俗中的農村。
然而,倘若你真的進入風俗之中,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幾乎所有這些風俗,都是對農民的一種桎梏,或是一種桎梏中的嘆息和無奈的微笑。白色孝布的飄揚,提醒晚輩的是“子從父命”之類的品德操行;而婚嫁所圍繞的多是“成妻從夫”“多子早子”。節日中的立春和驚蟄,是要把農民更緊地拴在土地上面;清明、端午、七夕、臘八等,節日中雖有歡樂,但都不難體察風俗對人們的警告。最好的節日要算八月十五和正月初一了。然而中秋節往往又讓人感受到一種不能團圓的分離之苦。春節是農村風俗的最集中的喜悅體現:插柏枝、貼門聯、拜大年、走親戚。可是,插柏枝是為了避邪,貼門聯是為求吉,拜大年是為了把吉祥送給別人,走親戚是為了鄉村的“裙帶”之網更加親密牢固。從所有的節日中,從所有普遍流傳下來的風俗中,我們能感受到的是農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絲毫感受不到教育農民對命運和大地的抗爭。所以,農民就特別能“忍”,特別之“愚”,特別“庸俗”。
中國農民,至今仍生存在風俗之中,而不是文化之中。風俗中的文化,除了小說家能感到一種美外,農民是很難感受到的。我們到湘西走一趟,站在沈從文的故居前,從農民身上感受到的是他們對沈從文這個作家的驕傲,而不是對沈從文筆下的風俗驕傲。賈平凹的商州亦如此。
風俗都是文化,文化大都不是風俗。農村母親要求子女走有走姿,坐有坐相。按照母親的要求走路或坐下的女子,我們仔細讀她的走姿坐姿,更多地看到了風俗,而不是文化。文化的優劣,會隨著時代發展很快地增刪;而風俗,則遠遠地隨在時代之后,拖不垮,甩不去。發展了的都市,更集中、更高速地靠近著現代的文化,脫落著從農村帶來的習俗。今天去都市細心探尋,除了六十歲甚或八十歲的老人和剛剛從土地上出來的農村的人們,你幾乎已經找不到農村的風俗了。可今天的農村,盡管許多地方都已富如巨賈,生活也有了幾分都市化,但他們仍然浸泡在鄉俗、習俗、風俗之中。農村,將在很長很長且永遠一樣的歷史長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風俗的染缸里發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種不知不覺的桎梏所捆束。
(摘自《經典雜文》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