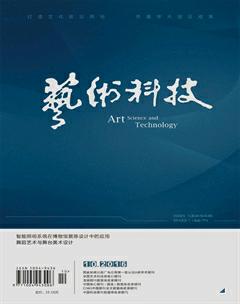大匠師的至善經驗與技術
范佳敏
摘 要:當代科學技術長足發展,互聯網使得全球經濟關聯、文化趨同,相對時間內空間距離得到縮短,發展的速度變得驚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文化的交流比任何一個時代都頻繁,中國文化已經被融入世界進程中,本土文化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遷,審美化泛化成為當下最為關注的焦點。對于當代藝術設計來說,回過頭來再認識工匠精神中至善至美的造物觀,從匠人精神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當下的設計與文化、藝術與生活,反思物與人、技與藝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工匠精神;真善美;日常生活審美化
1 工匠精神的本意
民藝學家柳宗悅曾說過,匠人在以往的任何時代都會被視為地位低下工種,或因為他們欠缺教育,或因為他們經濟狀況不良。會產生這樣的誤會或偏見,其主要是因為一般的匠人出身都較為卑微,所受教育都以技術為主,文化程度較低,大部分人又主要以手工技術謀生,被迫于社會的世俗與眼光,造物附庸風雅、風格華麗虛浮的世俗化傾向。再加上自古文人與匠人都是相對立發展,文人提倡“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的觀念,常以“新意”來解除“匠氣”,用“生”“拙”等藝術觀念反對“工”“麗”的匠氣甜熟等流弊。李漁有作《閑情偶寄》、計成則著《園冶》,都是闡明“匠文”之分的好例子。
無論文人還是匠人,對于社會的發展來說都是缺一不可的,尤其是在文化與藝術方面。社會文化在其演進的過程中,生活與藝術時常呈現出一種分離、對立的狀態,但時常又相互結合、統一。在當代后現代語境下,我們更加推崇的是文匠結合的治藝造物理念,也是當代真正的“哲匠精神”之所在。
“尚巧求精”是工匠的創作態度,“道技合一”是工匠的理想,匠人雖墨守成規,但這份堅守傳統手藝的精神確實感動人心,他們在不自覺的過程中精進技藝、演變風格,在口傳身授的過程中,傳遞了智慧與文化,撰寫著“傳、幫、帶”的匠人奇跡。
雷氏通過口傳身授的匠人之法傳建有故宮、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等,環境宜人、空間布局合理的工程,實現了“天人合一”的匠人精神。手工時代的匠人憑借生活的經驗,帶著對大自然的敬仰之情感去生活、創作,雷氏這般的匠人堪稱“大匠師”,他們是匠人也是設計師,器物在他們的手中得到升華,手是他們最有力的工具,雙手反復磨練出“技”,與“藝”,到達天人合一之“道”。
2 工匠精神的回歸
今日的中國異于過去任何時代,當代社會經歷了從新媒體到了跨媒體時代,目前迎來了“全媒體”構建。互聯網技術的長足發展使得世界文化交流變得暢通無阻,形形色色的新技術、新手段接踵而來,真是有點讓人應接不暇。社會的巨大變革使得我們的藝術觀念和藝術行為都在轉變,我們正處在藝術與生活緊密結合的時期,社會文化表征無處不顯出日常生活審美化,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物質上的改善,藝術正在揭開她神秘的面紗,慢慢從神壇上走下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成一般的消費品,融入我們生活的開銷。
藝術正向大眾化、日常化路線前進,并迅速與生活實用器物相結合,或許是當代商品社會發展的必然,當代審美泛化成為常態,“設計造物”“器物審美”“圖像與觀看”都成了問題的焦點。重溫過去幾十年,我們會深刻地體會到,世界是如何被把握為圖像的,圖像已經將我們包裹。圖像的生產、流通、消費急速膨脹的現象,印證了海德格爾所提出的“世界圖像時代”。[1]今天我們的眼球從來沒有像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那樣的忙碌、疲勞,“視覺文化”的崛起成為后現代的日常特征,人類進入了從未有過的圖像“過剩”的時期,這種視覺化現象使得現今時代迥異于以往的任何時代,各種視覺裝置紛至沓來,尤其隨著科技的進步發展,各種新型的視覺技術手段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們以往的視覺交往、視覺呈現和視覺記憶。日常生活中的我們迷失在這視覺化世界中,全然不知地追逐、游戲。在商品經濟的浪潮中,我們在意的不是商品本身的價值和功能,我們更多關注品牌、形象,社會商品價值從“占有價值”轉向“展示價值”。當下的中國文化正在驗證一個文化的新游戲規則,那就是可視性的強勢支配。[2]社會已由役物變成物役,生活在“工具理性”下的我們,被各種裝置范式所包裹,我們需要被“藝術救贖”。
大匠師們世代傳承的智慧經驗與先進技術,凝結出了優秀的文化思想,這是從真實的生活體會中走來的藝術,不夸大其詞,不好高騖遠,是踏實的源自生活的藝術、日常的藝術。大匠師們通過真誠的雕琢,創造有血有肉的“藝術生命”,值得我們代代相傳。在當代“裝置范式”的包裹下,“堅守匠心”其實是選擇了一種淡然的生活方式,是“匠人精神”的當代回歸的意義。
3 工匠精神的“真善美”
美與善本是同意,但在多數的情況下,美是從屬于善,是善的美感形式,或者就是善。[3]雖然與西方古典美學“真善美”統一的理念有所不同,其實都是將審美化作為人生境界的追求,我們理解為“盡善盡美”。中國儒道等學派產生之前的春秋初期,美與善是同意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藝術——審美活動逐漸脫離功利實踐而走向獨立,儒家是將“美善”兩者相聯系在一起,提出了“禮樂相濟”、“美善相樂”等思想,美是一種外在的感性形式(可理解為今天的形式美),而善則是內容,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道家思想是在善的基礎上追求真美,道家追求自然無為,與儒家所不同之處,道家把“美真”聯系在一起,在美育和教育等問題是采取放任態度,片面的最求個體自由,但在審美問題上兩家殊途同歸,儒家“以和為貴、以和為美”;道家“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中國傳統審美的核心思想,儒道互濟,和而不同,求天地之“大美”,人生之“至樂”。這正是傳統工匠的精神追求所在,也是大匠師的創物觀、審美觀,也是中國審美文化的根本與主流。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六材既具,巧者和之”。這是《考工記》中關于匠人的一段描述,其中的“巧者”指的就是匠人。在中國古代時期技與藝是不分的,匠人既是設計者又是生產者,有時候還是使用者,匠人在造物中不斷地摸索“創物”經驗與技術,在千萬次地反復過程中,實踐,言傳,堅守。匠人們在勞作中的方式、方法以及原則有別于現代化的機器生產,它承載著濃烈的情感,作品傳達出手工的溫度,這是匠人在藝術創作中最樸素的“真善美”的體現。
“和”是真善美的完美統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范疇,和即是美學層面的“善”,是“匠人精神”的核心追求,也是中國工匠藝術追求的至高境界。在中國和之真善美的思想不同于西方“神本主義”,其中的“和”體現出的是一種道德“人本主義”,匠人一方面以人事去順應天命,另一方面又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為理性的、道德的化身。通過日常的修煉,普通的人格精神逐步上升,到達“圣賢”的境界。匠人的實踐活動最根本的是道德實踐,最高的藝術作品也必須以“至善”為前提,到達“盡善盡美”。[4]
4 工匠精神的當代意義
當代,“審美泛化”已成為了“后現代”的美學特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一股熱潮,如今已經席卷全球,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是近幾年歐美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審美泛化成為文化界最為普遍的話題。“日常生活審美化”成為一個舊詞,一個“舶來品”來到當代的中國。邁克·費德斯通的演講,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正在消弭藝術和生活之(下轉第頁)(上接第頁)間的距離,在把“生活轉換成藝術”的同時也把“藝術轉換成生活”。①這個社會學研究范疇的話題已成為關注焦點,而且被視為“后現代文化”中特定的內容,在中國當下之流行耐人尋味,雖然反映出某種適切性,同時也是發人深思的敏感問題。
審美泛化是現代社會的總體表征,作為文化本體呈現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含義有兩層,一是指日常生活中充滿審美化的產品、物品、環境。另一層意思是指藝術和審美進入日常生活。無論那一層的含義,當代審美泛化的特征即公式:商品+形象=美。[2]似乎有些讓人不敢接受,但這正是當代“后現代主義社會”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真諦。其現象凸顯為從商品的“價值占有”向商品的“價值展示”的轉變。例如香奈兒、愛馬仕、江詩丹頓,這些知名的世界級品牌的形象價值已經遠勝于其使用價值,日常生活展現出一幅不易察覺的物役審美的窘境。隨著工具理性的自大和膨脹,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過程中,設計的本質也在逐漸滋長強勢的武斷和自以為是的粗暴,“燒包”美學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5]
大眾更多的在意“體驗”“品味”,時常是為體驗而體驗,為品味而品味。有幾個錢就開始“燒包”,一支寫字筆也可以“有品”,有錢的用萬寶龍,差點的用拉美,再不行買支無印良品。在商家極端追求剩余價值的陰謀里,設計師的良知和理性,尊嚴和使命,開始被扭轉。生活中充斥著類似的案例,例如明式家具中的官帽椅或圈椅,本是中國經典的坐具,集宋明理學和至善技藝之大成。可是當代的各種演繹讓人啼笑皆非,全然不顧器具的功能、文化、工藝、審美,各種粗制濫造的“山寨”擺放在各種所謂高級場合。大眾的審美完全傾向視覺圖像,一廂情愿的設計,奢靡繁復過度的包裝,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完全有悖工匠精神的初衷。一些藝術家、設計師們選擇了自己的那份“堅守”,紛紛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國,用心去守護那片凈土,用手去磨刻至善的精神。
國內藝術發展經歷了工藝美術發展到藝術設計的轉變,工業發展經歷了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的轉型,不久前提出“中國制造2025”的規劃。社會物質長足發展,而日常審美、日常文化在消費層面卻是倒退的,老百姓寧愿去日本海陶、代購“馬桶蓋”,據說這還是中國浙江杭州的產品;愿意在10平方米的客廳放一個72寸的高清電視機,完全看不到整體畫面;雙十一、雙十二熬到午夜不顧一切地瘋狂網絡搶購打折品。
當我們的日常生活步入審美泛化的時代,無論是生活的審美化還是審美化的生活趨勢,是否就意味著我們的現代生活已經由審美完成了改造嗎?日常不再具有壓力和局限了?現代性背景中日常生活充滿了工具理性的壓抑,日常生活變得越來越無聊,就像一個“鐵牢”(韋伯)。雖然不能像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那樣去尋找烏托邦式的理想國,也該是通過對現實日常生活的“美”的塑造來改變它。商品+形象≠美,天人合一、平衡、和諧才是我們民族日常生活實踐的藝術價值取向,無論是東方“盡善盡美”的理想,還是西方“真善美”的統一,工匠精神至善盡美的經驗與技術正好與之吻合。
注釋:①1988年4月在新奧爾良“大眾文化協會大會”上作了題為《日常生活審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演講。
參考文獻:
[1] 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三聯書店,1996:899.
[2] 周憲.文化表征與文化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317.
[3] 聶振斌.文化本體與美學理論構建[M].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6.
[4] 湯一介.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1984(4):73-83.
[5] 杭間.設計的善意[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3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