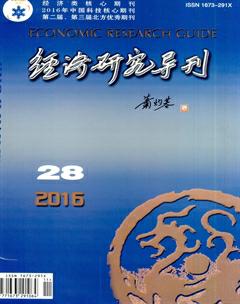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
許瑞軒
摘 要: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對于厘清刑事審判工作的內(nèi)容,有效提升刑事司法效率,及時(shí)矯正犯罪行為尤為重要。在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之下,要堅(jiān)持四項(xiàng)分離:其一,要做好控訴與審判職能的適當(dāng)分離,充分實(shí)現(xiàn)其程序意義和結(jié)構(gòu)意義上的效能;其二,要做好事實(shí)與法律適度分離,讓事實(shí)歸于真相,讓法律歸于價(jià)值;其三,要做好定罪與量刑適當(dāng)分離,構(gòu)建定罪與量刑相互分離又彼此并重的刑事庭審模式;其四,要做好審判與執(zhí)行恰當(dāng)分離,讓法官專司審判工作,提升刑事審判效率,形成有效的制衡體系。
關(guān)鍵詞:刑事庭審中心主義;分離;效率;司法
中圖分類號:DF71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8-0195-02
一、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以來,我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司法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進(jìn)行中。刑事庭審中心主義學(xué)說也空前繁榮,逐漸應(yīng)用于現(xiàn)代刑事司法實(shí)踐。其主張刑事司法活動(dòng)回歸審判,將事實(shí)判斷、定罪認(rèn)知、量刑處斷與裁判結(jié)果全部置于法庭審理之中。因而,法庭成為了刑事司法活動(dòng)的主戰(zhàn)場。刑事庭審中心主義,就其內(nèi)涵而言,指的是在整個(gè)刑事司法活動(dòng)之中,務(wù)必要堅(jiān)持:于法庭之上進(jìn)行事實(shí)證據(jù)調(diào)查,在法庭之中展開定罪量刑辯論,于法庭庭審期間形成裁判結(jié)果并予以直接公布,將直接言詞原則貫穿于整個(gè)庭審之中,對于非法證據(jù)做到嚴(yán)格排除[1]。
目前,我國的刑事司法改革工作已經(jīng)進(jìn)入深水區(qū),改革的難度不可謂不大,司法高層的著手力度也可謂之不小。雖然,刑事庭審中心主義司法內(nèi)在制度其內(nèi)部有機(jī)統(tǒng)一。但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對立統(tǒng)一的視角來看,有效地厘清刑事庭審職能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適度地做好各項(xiàng)職能的分離,減弱彼此之間的混同與干擾,促進(jìn)其獨(dú)立效能更好地發(fā)揮,亦為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
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旨在從控訴與審判分離、事實(shí)與法律分離、定罪與量刑分離、審判與執(zhí)行分離此四組職能的分離切入,進(jìn)而優(yōu)化司法資源配置,促進(jìn)刑事司法各項(xiàng)職能的應(yīng)有功能充分發(fā)揮,切實(shí)推進(jìn)刑事庭審中心主義,最終實(shí)現(xiàn)刑事庭審的實(shí)質(zhì)化。
二、四組刑事庭審職能的分離
(一)控訴與審判分離
一般而言,控訴是引起審判的先決條件,審判則是檢驗(yàn)控訴成立與否的實(shí)質(zhì)活動(dòng)。為了促進(jìn)司法公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在刑事司法程序建構(gòu)當(dāng)中,都普遍采取控訴與審判職能的分離原則。實(shí)行控訴與審判職能的分離,于程序、于結(jié)構(gòu),均有其積極意義:于程序之中,能夠促使程序啟動(dòng)意義上的不告不理和程序運(yùn)作中的訴審?fù)唬捶ㄔ旱男淌峦徎顒?dòng)必須緊緊圍繞檢察院的指控進(jìn)行,不可超越指控的范圍而恣意變更罪名或者追加被告;于結(jié)構(gòu)之上,可以實(shí)現(xiàn)結(jié)構(gòu)意義上的機(jī)構(gòu)設(shè)置和人員組織上的審、檢分離,即法院與檢察院分屬不同機(jī)構(gòu),配置不同人員。此二者互為表里,一起構(gòu)成控訴與審判分離原則密切聯(lián)系的兩個(gè)方面[2]。
然而,我國在司法權(quán)長期集中的影響之下,對于控審分離原則的貫徹,依然存在兩點(diǎn)不足:其一,《刑事訴訟法》第243條規(guī)定的再審程序的啟動(dòng)主體包括了人民法院自身,這一點(diǎn)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不符合控審分離的要求;其二,《刑訴法解釋》第241條第1款第2項(xiàng)的規(guī)定賦予法院變更起訴罪名的特權(quán),背離了訴審?fù)辉瓌t。此兩項(xiàng)不足,則有待于立法改進(jìn),亦非單純理論闡釋之所能作為。
(二)事實(shí)與法律分離
至于事實(shí)與法律的分離,則主要是針對人民陪審員制度而言。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與兩大法系的陪審團(tuán)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其背后的法理幾近相同。二者都普遍主張將事實(shí)判斷與法律認(rèn)知進(jìn)行二分,把事實(shí)部分交予陪審員處理,把法律部分留給法官判斷。正是由于人民陪審員來源于人民群眾之中,熟悉案件的事實(shí)背景和被害人與被告人的處境經(jīng)歷,所以才能夠充分地使偵查所得的事實(shí)部分無限趨近于案件事實(shí)本真的面目,進(jìn)而給刑事庭審中心主義留下充足的發(fā)揮余地。繼而,將專業(yè)的法律認(rèn)知問題拋給專門的職業(yè)法律人才,即人民法官。法官在陪審員的事實(shí)判斷既成的基礎(chǔ)之上進(jìn)行法律的價(jià)值評價(jià),一則,減輕了法官的工作壓力,提升審判效率;二則,避免了法官事先接觸事實(shí)部分,從而以先入為主的有罪推定綁架后續(xù)的法律評價(jià),做出法律誤判[3]。
如此而為,將事實(shí)與法律分離,陪審員與法官各司其職,能夠在事實(shí)部分與法律評價(jià)部分,進(jìn)行兩次的冤假錯(cuò)案的有效過濾,最終讓事實(shí)歸于真相,讓法律歸于價(jià)值,維護(hù)好司法公正。此外,筆者認(rèn)為,事實(shí)與法律二分的人民陪審制度應(yīng)該更多地運(yùn)用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審理之中,而并非只適用在重大疑難案件或者法律規(guī)定的案件之中。因?yàn)椋朔N二分優(yōu)勢之于司法公正的意義甚是重大。
(三)定罪與量刑分離
定罪與量刑作為刑事責(zé)任認(rèn)定的一體兩面,在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之下的刑事庭審當(dāng)中更加要求二者的實(shí)質(zhì)化。談及二者的實(shí)質(zhì)化,則必須厘清定罪與量刑的關(guān)系,進(jìn)而適當(dāng)?shù)貙烧叻蛛x。
量刑,即刑罰裁量,是指在對犯罪之人定罪的基礎(chǔ)之上,以量定刑罰為具體內(nèi)容的刑事司法活動(dòng),量刑是定罪的承繼,定罪是量刑的先決條件。一場科學(xué)、合法的刑事庭審活動(dòng),必然包含著定罪審判與量刑審判,在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之下,更加要求定罪審判與量刑審判的實(shí)質(zhì)化,并且其內(nèi)部順序不可逾越,任何其一也不得省略和混淆。
然而普遍來看,目前我國刑事庭審的工作重心是量刑問題,這與傳統(tǒng)的定罪中心主義發(fā)生著激烈沖突[4]。不管何者為重,這都是一種病態(tài)的現(xiàn)象,因?yàn)槎ㄗ锱c量刑無所謂孰輕孰重,拋開其刑事庭審一體兩面的特性,而主觀地去有所側(cè)重的都是偽命題。倘若,單純地以量刑為核心,就會(huì)使得定罪流于形式而虛化刑事庭審。同時(shí),量刑證據(jù)的先入為主,加大了法官的有罪推定。如果,一味地以定罪為中心,就會(huì)使量刑程序成為附屬,讓量刑審判淪為定罪的工具,一個(gè)人一旦入罪,就很難在量刑部分得到科學(xué)合理合法的處罰歸屬,必然出現(xiàn)大量的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甚至無罪而判。這些,自然背離了刑事庭審中心主義,更是踐踏著現(xiàn)代司法文明。因此,構(gòu)建定罪與量刑相互分離又彼此并重的刑事庭審模式,乃為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緊要任務(wù)[5]。
(四)審判與執(zhí)行分離
論及審判與執(zhí)行職能的分離,必須探究二者的本質(zhì)特性。刑事審判權(quán)具有較強(qiáng)的司法中立特性,而執(zhí)行權(quán)具有較強(qiáng)的行政強(qiáng)制屬性。根據(jù)孟德斯鳩行政、立法、司法三項(xiàng)權(quán)能相互分離與制衡的理論支撐,刑事審判職能適宜與刑事執(zhí)行職能相互分離。
目前,我國的刑事審判職能與刑事執(zhí)行職能均交由人民法院行使。正如有學(xué)者比喻: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dòng),人民法院身兼二職,既要做好裁判員,又要當(dāng)好運(yùn)動(dòng)員。殊不知,一項(xiàng)體育賽事如果運(yùn)動(dòng)員和裁判員不加區(qū)分,會(huì)出現(xiàn)怎樣的效果呢?然則,司法高層決策者在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之中,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體制設(shè)計(jì)的缺陷,深諳審判與執(zhí)行合一對于人民法院司法審判工作的累贅,以及對于司法公正帶來的負(fù)面效應(yīng)[6]。
在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之下,將審判與執(zhí)行進(jìn)行二分處理,法官專司審判之職,法院專管司法之事。至于,刑事執(zhí)行包括強(qiáng)制措施和刑罰執(zhí)行則交由獨(dú)立的執(zhí)行局專門行使。該執(zhí)行局應(yīng)該獨(dú)立于法院、檢察院之外,由中央垂直管轄,設(shè)好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關(guān)卡,讓刑事執(zhí)行檢查、監(jiān)督司法審判的公正性、合法性,矯正司法審判的缺陷,進(jìn)而破除以往刑事執(zhí)行單一化的執(zhí)行刑事審判的命令。簡而言之,將審判與執(zhí)行分離,構(gòu)造審判與執(zhí)行彼此之間的牽制與制衡機(jī)制,這對于刑事司法公正而言,自然裨益良多。
三、結(jié)語
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做好控訴與審判職能的適當(dāng)分離,充分實(shí)現(xiàn)其程序意義和結(jié)構(gòu)意義上的效能;做好事實(shí)與法律適度分離,讓事實(shí)歸于真相,讓法律歸于價(jià)值,維護(hù)好司法公正;做好定罪與量刑適當(dāng)分離,構(gòu)建定罪與量刑相互分離又彼此并重的刑事庭審模式;做好審判與執(zhí)行恰當(dāng)分離,讓法官專司審判工作,提升刑事審判效率,及時(shí)矯正違法犯罪,并且努力構(gòu)造審判與執(zhí)行彼此之間的牽制與制衡機(jī)制,形成有效的互促體系。
綜上,通過此四組職能的分離,可以優(yōu)化司法資源配置,促進(jìn)刑事司法各項(xiàng)職能的應(yīng)有功能充分發(fā)揮,讓整個(gè)刑事庭審工作緊緊圍繞審判進(jìn)行,讓法庭成為發(fā)現(xiàn)真實(shí)、定罪量刑的主陣地。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對于厘清刑事審判工作的內(nèi)容,有效提升刑事司法效率,及時(shí)矯正犯罪行為,尤為重要。在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之下,從控訴與審判分離、事實(shí)與法律分離、定罪與量刑分離、審判與執(zhí)行分離此四組職能的分離切入,深化“分離”意識(shí),不僅僅只局限于此處四種職能之分離,而且要不斷厘清其他相關(guān)職能的界限,進(jìn)而做到適度的分離,使得整個(gè)刑事審判工作精細(xì)化、專門化,讓司法的公平正義在高精度的審判操作之中,可以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讓人民法官專心審判工作,明確職能范圍,在對立統(tǒng)一的唯物史觀的指導(dǎo)之下,做出最貼近正義的裁判,讓每一個(gè)人民群眾在每一個(gè)案件之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樹立刑事庭審中心主義視域下的“分離觀”,能夠有效提升刑事庭審效率,切實(shí)推進(jìn)刑事庭審中心主義,最終實(shí)現(xiàn)刑事庭審的實(shí)質(zhì)化。
參考文獻(xiàn):
[1] 趙隴波.刑事庭審中心主義司法內(nèi)在制度系統(tǒng)性研究[J].經(jīng)濟(jì)研究導(dǎo)刊,2016,(19):190-191.
[2] 謝佑平,萬毅.刑事控審分離原則的法理探析[J].西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2,(5):90-94.
[3] 朱燕萍,羅世翊.人民陪審員制度中法律審與事實(shí)審分離機(jī)制研究[J].福建法學(xué),2016,(1):84-89.
[4]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328.
[5] 汪海燕.論刑事庭審實(shí)質(zhì)化[J].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2015,(2):118-121.
[6] 岳彩領(lǐng).論強(qiáng)制執(zhí)行審執(zhí)分離模式之新構(gòu)建[J].當(dāng)代法學(xué),2016,(3):121-129.
[責(zé)任編輯 陳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