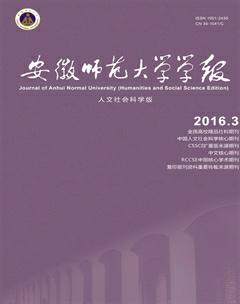李白與東晉名士風流及其詩性接受方式
仲瑤
關鍵詞:東晉;名士風流;李白;人格;詩性;俊逸
摘要:作為魏晉風度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東晉名士風流呈現出高度的詩性與藝術美。以《世說新語》為媒介,以風流蘊藉的人格趣尚為契合點,李白對東晉名士風流采取了一種詩性的接受方式。其飄逸不群的人格氣質、入仕方式的設定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謁心態都與東晉名士風流有著密切關系。同時,將東晉名士的逸興勃發和任樂精神納入到詩歌創作中,形成了飄逸俊發的詩歌風貌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lOOl 2435(2016)03 0285 06
李白歷來被視為唐代詩壇最璀璨奪目的存在,其謫仙式的人格氣質、任真率性的行為方式以及風神俊逸的詩歌風貌一直是李白乃至唐詩研究中歷久彌新的一個話題。除了縱橫家與豪俠,關于李白與魏晉風度之關系也多為論者所注意。但迄今為止,這種探討仍停留在整體以及泛論層面上,對于東晉名士群體在李白思想譜系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出現的原因及其對李白人格趣尚、行為方式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謁心理等諸多層面的深刻影響尚有待細致探討。本文擬以李白的干謁、交游類詩文中頻繁出現的眾多東晉名士群像及其詩性化的接受方式為切入點,以期對上述問題有進一步究明。
東晉是魏晉名士風度的一個重要發展與定型階段,以門閥政治的鼎盛為依托,百余年間名士輩出。通覽《世說新語》一書所錄名士風流事跡,無論就數量、出現頻率還是影響而言都以東晉一朝為最。而且,在不同的階段,這一龐大的名士群體的構成及其容止作派、人格與精神旨趣也不盡相同。渡江之初,以胡毋輔之、阮放、畢卓、桓彝等為代表的新“八達”延續了元康放達派名士散發裸體、對弄婢妾的放誕縱欲之風,同時又有王導、溫嶠、庾亮等戮力王室而又不廢清談名理的重臣型名士。隨著偏安政權的趨于穩定以及門閥政治形態的高度發展,在中后期尤其是政局較為清寧的永和年間,則涌現出諸如王濛、劉恢、殷浩、孫綽、許詢、支遁、慧遠、謝安、王羲之等以清談、容止、雅量見賞的一眾名士,極一時之風流。相比之竹林先賢的悲劇與啟蒙色彩以及元康放達派名士的荒放縱欲,東晉名士群體尤其是永和名土大抵能調和名教與自然二旨,其人格精神、容止風姿以及私人生活情調等方面都表現得更加平和高逸、矜尚脫俗。袁恪之目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并以此定殷(浩)、韓之高下。其時第一流的名士往往是第一流的清談家,以經綸才具見長的王導、溫嶠、庾亮等重臣雖預清談也只被視為第二流人物,英邁俊爽、權重一時如桓溫者乃至因不善名理而又強欲談玄為風流之士所譏。風氣所積,此期名士對容止風姿和言語之美的熱情也達于頂峰。清談容止之外,東晉名士之于琴、棋、書法、繪畫、音樂諸般伎藝也多有妙詣。《世說新語·雅量》:“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書琴。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以門第閥閱為立身依托,以哲學、藝術為精神滋養,東晉名士獲得了智性和情感雙重層面上的詩意自由。馮友蘭曾以“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八字總論魏晉風流,毋寧說是為東晉尤其是永和名士群體而發。正是這種在清談、容止以及社交與私人生活場域所呈現出的詩性美和藝術境界使得東晉名士群體超越了自身所處的時代,甚至也超越了其本身的種種缺陷和流弊而為后世所賞慕、效仿。
李白平生傲岸不羈,除了縱橫家與豪俠,唯獨對東晉名士青眼有加,在他的筆下集中出現了謝安、王羲之、王子猷、庾亮、桓溫、王恭、謝尚、支遁、袁宏等一大批東晉名士。在這之中,尤稱謝安,并屢以自比。他對謝安的傾慕若此,與其自身“功成拂衣去”式的“出”“處”思想有著直接關系。與正始名士在名教、自然之間的對立、激蕩不同,當王室多艱之際,東晉一朝的砥柱之士能較為從容地游走于出處二端,如庾亮“雅好所托,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孫綽《庾亮碑》)。最能體現這種調和和風流境界的是被稱為風流宰相的謝安。謝安一生之出處與謝氏家族的門第危機息息相關,其名士風流中不乏政事才干和隱忍周旋之術。高華平曾指出,“謝安的風流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瀟灑,也不全在其事功的顯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處;既非全屬于儒,也非全屬于道,而是在于其對出處、儒道、內圣與外王的統一與超越。”李白之傾慕謝安正在于后者在仕隱、出處之間的這種自由轉換:“謝公終一起,相與濟蒼生”(《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其二),“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贈常侍御》)。然而,李白不僅無謝安的門第之資,也無其政治才具,他對謝安式人生跡遇的熱切憧憬與自我期許只純然是一種詩意的浪漫:“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暫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書情題蔡舍人雄》),“談笑”二字,瀟灑、飄逸之極。
可以說,李白一生所賞正在此種人物風流,這種趣尚也貫穿于他對整個東晉名士群體的接受之中,如《王右軍》: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作為王謝子弟之佳者,王羲之在永和名士中最具風流蘊藉之姿,時論以為“清貴有風鑒”,李白以“清真”論之,蓋亦賞其真素之美。在李白的詩文中,“清真”一語曾屢屢出現,如“圣代復元古,拂衣貴清真”(《古風》其一),“裴子含清真”(《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等,最能體現李白之人格趣尚。至于“瀟灑”也是東晉人物品藻之習語,如王子敬語謝安云:“公故瀟灑”。可以說,“清真”“瀟灑”二語不僅精準地提煉、概括出了王羲之的風神,更道出了李白乃至有唐一代文士對東晉人物的賞契之所在。他對謝安的深相推崇也不乏此種旨趣,如“安石泛溟渤,獨嘯長風還。逸韻動海上,高情出人間”(《與南陵常贊府游五松山》)。《世說新語·雅量》載謝安與孫綽等人泛海觸風,“風起浪泳,孫、王諸人色并遽,便唱使還”,安“神情方王,吟嘯不言。”李白引此事以贊其處變不驚的高情雅量。
除了以王、謝為代表的高門名士,李白對東晉人物清真瀟灑人格趣尚的接受還集中體現在對陶淵明的接受中,如《戲贈鄭溧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六句之中巧妙地融括了《晉書》所載的諸多充滿名士風流色彩的逸事,儼然為陶公作一幅人物素描,寥寥數筆,形神俱出。又《贈臨沼縣令皓弟》“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弦琴”,也以同樣的手法極寫陶之高逸、淳古。相比杜甫對陶淵明的深刻同情之了解以及調侃式接受,李白對陶淵明高逸脫俗形象的塑造和名士趣味更能代表唐人尤其絕大多數盛唐文士的審美趣味。他之推崇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贈孟浩然》)正在于孟浩然身上所遺存的這種魏晉人物風流,尤其是那種傲視王侯的氣骨和風韻。
與這種內在人格趣味和生命情調的賞契相應的,李白在干謁、交游、贈答詩文中酷愛以東晉名士自比或比贊他人,如“謔浪肯居支遁下,風流還與遠公齊”(《別山僧》)、“吾非謝尚邀彥伯,異代風流各一時”(《對雪醉后贈王歷陽》)“賀循喜逢于張翰,且樂船中”(《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然而,任何一種模仿最終都仍然是一種變異,模仿者自身的生命意志和個性色彩越強這種變異就越大。受開元后期至天寶年間浮華冶游風氣的裹挾與激蕩,李白對東晉名士風流的效仿中也雜入了縱欲放蕩的成分,甚或不免走人唐才子式的縱浪狂悖一途。
綜上所述,李白于魏晉名士之中最為賞契的并非以嵇、阮為代表的竹林名士,而是以謝安、王羲之等為代表的東晉名士風流。以《世說新語》和《晉書》為最重要的接受中介,李白對于東晉名士風流蘊藉的人格趣尚采取了一種詩性化的接受方式,具有鮮明的審美傾向,有時甚至不免平面化、重復之嫌,但東晉名士風流的種種審美意蘊卻在李白的手中得以高度詩性化的呈現。這種獨特的接受方式對于其人格氣質、行為方式乃至人生跡遇都有深刻影響。
二
李白一生之出處、婚宦無不充滿戲劇性。作為一種生存、干謁方式乃至生命姿態,其飄然不群的人格特質和行為方式也與對東晉名士作派的效仿有著直接關系。除了隱逸求仙、縱酒沉酣、長嘯攜妓等普泛性接受,李白對東晉名士風流的傾慕和效仿一個最集中而又獨特的體現是清談。《早夏于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自稱“清酌連曉,玄談入微”,與其為詩酒放浪之友的崔宗之亦有“清談既抵掌,玄談又絕倒”(《贈李十二白》)之贊語。《開元天寶遺事》稱“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固非虛言。觀其于東晉名士之清談逸事,熟稔之至,信手拈來,如《贈僧崖公》“手秉玉塵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信可聽”,前半用孫綽、許詢于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之典,后半則用王漾稱謝安語。乃至直接引東晉人物清談之語入詩文,如《上安州李長史書》中的“白,嵌崎歷落可笑人也”,即用《世說新語》中周頻贊桓彝語。在干謁、品論當世人物時,亦好用東晉清談、品藻語,如稱裴長史:“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上安州裴長史書》)《世說新語·容止篇》載:“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于此用之,可謂雅切裴長史之姓氏。至如“沖恬淵靜,翰才峻發”(《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風生玉林,清明瀟灑”(《冬日于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覲省序》),“蘊冰清之姿”(《早夏于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等皆東晉人物品藻之雋語。對于東晉名士清談品藻話語體系的這種移植使得原本世俗化的干謁、陪宴行為和對象呈現出濃厚的名士風流色彩。然世易時移,李白甚為自詡的清談之能早已失去了它之于東晉名士的獨特身份意義,徒留浮華之譏。
當人才選拔已逐漸被納入常規渠道,科舉已成為新興的文士階層入仕之最主要途徑時,李白亦頗寄希望于以文章自達。其干謁詩文中,每以文章藻麗,下筆千言自許。司馬相如之外,李白的這種天才式的自詡也烙下了東晉名士的痕跡。《世說新語·文學》載:“桓玄常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同篇又載:“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李白所推崇的正是這種文思爽利,并希企能在一種充滿傳奇色彩的場合、情境下得以展現,從而達到一鳴驚人的效果,如《與韓荊州書》:“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正是用袁虎之典。此外,其引蘇顳稱己之言“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若廣之以學,刻意相如比肩也”,也不禁令人想起謝靈運謂殷仲文語:“若讀書半袁豹,則文史不減班固。”當其人為翰林學士,酣醉之中于御筵捉筆上作《清平調》諸篇,一揮而就而眾人咸嘆文采驚絕之時,表演色彩和榮耀達到了一生的頂峰。然而,這種俳優色彩濃厚的文學侍從角色與李白原本的政治期許實在相差太遠,唯有作傲岸任誕之態以獲得某種心理平衡。
以先天稟賦為內在根基,對東晉名士風流舉止和素養的傾慕和模仿其結果是在盛唐的時代舞臺上造就了一個以“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暮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為擅場的風流名士。而這一自我形象反過來也深刻地影響了李白對于入仕方式的設定和期許。《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云:“若大賢處之,若游青山、臥白云,逍遙偃傲,有何不可。小才拘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風朗月、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名教樂地,無非得俊之場也。”這種期許與設定充滿了東晉高門名士色彩,所謂“名教樂地”之內涵由此可窺。然而,失去了東晉門閥世族所依憑的政治、經濟特權,仍期翼以此種種名士放浪之舉人世,顯然是極不合時宜的。其結果便是“一生傲岸苦不諧”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是“世人皆欲殺”(杜甫《不見》)。《東山吟》所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正是李白對于自身時代處境的某種反思。
不僅如此,李白以布衣自許,平交王侯的干謁心理也與東晉名士風流有關。遍覽《晉書》,兩晉名士雖門第顯貴亦不妨以布衣自許,如司馬越“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東晉名士以布衣之交相稱者尤多,如王導稱與庾亮“本懷布衣之好”,王濛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為布衣之交者,往往不拘于分屬,而以意趣相賞愛,帶上了濃厚的名士風流色彩。《世說新語·任誕》載:“桓宣武引謝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曰。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又“衛永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溫謝、溫衛之間這種分屬主從,而又不拘于世俗名教尊卑秩序的名士風流舉動為李白所深羨,并將其投射到現實的干謁對象身上。在《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中,他將宣州司馬武幼成比作大司馬桓溫,并將其塑造成了一個“因據胡床,岸幘嘯詠”名士形象。也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對于“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的蘇颋頗為稱許。除了孟子所謂“說大人則渺之,勿視魏巍然也”的游說策略之外,李白的“目送飛鴻對豪貴”“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任華《寄李白》),與他對上述以神契相交的名士型賓主關系的賞慕、內化和期許也是分不開的。與前者相比,后者無疑更具名士風流色彩,也更契合李白的個性趣尚。“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對于李白傲岸不馴形象的塑造無疑也出于同樣的人格審美趣尚。
由上所述,李白種種傲岸不羈的行為作派,他的政治期許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謁心理都與東晉名士風流關系頗深。如同東晉名士每以“神仙”稱賞人物,對東晉名士風流舉止的慕習使得李白的行為方式也帶上了謫仙式的風流浪漫色彩,并因此深得同調中人如賀知章、杜甫、崔宗之等人的賞譽。但與此同時,與東晉名士所遭受的浮誕和不經世務之譏相似,李白所擅場并自詡的種種名士風流和素養被正統之士目為“浮誕”也是不可避免的。透過與東晉名士風流之間的淵源,我們會發現李白這位被認為是盛唐最富于天才與個性的詩人身上充滿了對以東晉名士為主體的古往賢達、高士的刻意模仿,他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名士化的、詩化的自我。或許還可以說,李白的一生從未有過真正的自我,其思想的駁雜和浮浪無歸都與內在本真自我的缺失有關。但不可否認的,他也是唐人之中最得東晉名士清真之趣的,最具詩性之美的。
三
東晉名士風流的深刻影響不僅在于對詩性、審美化人格精神的養成,同時也造就了一種新的美學風格——逸韻與風神。關于“逸”“韻”“風神”等與名士風流之關系,牟宗三曾有一段精妙之解:“名士者,清逸之氣也……逸者離也,離成規通套而不為其所淹沒則逸。逸則特顯‘風神,故俊。逸則特顯‘神韻,故清。故日清逸,亦日俊逸。逸則不固結于成規成矩,故有風;逸則灑脫活潑,故曰流。故總曰風流。”李白對于東晉名士風流所深賞者也正在于此種灑脫活潑的“逸”格,如《陪宋中丞武昌夜飲懷古》:“清景南樓夜,風流在武昌。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龍笛吟寒水,天河落曉霜。我興還不淺,懷古醉余觴”,即糅用庾亮南樓理詠之逸事。《世說新語·容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往,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競坐甚得任樂。
庾亮所說的“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和“甚得任樂”是東晉名士“風流”精髓之一,也是成就其“逸”格的內在要素。李白繼承、內化并將東晉名士的這種“逸”興和“任樂”精神發揮到了新的極致:“至于酒情中酣,天機俊發,則談笑滿席,風云動天”“談玄賦詩,連興數月”“樂雖寰中,趣逸天半”(《秋夜于安府送孟贊府兄還都序》),“乘興忽復起,棹歌溪中船”(《留別廣陵諸公》),“時時或乘興”(《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相比東晉名士的雅量深致,李白的“興”顯得更充沛、激蕩,甚至頗有躁狂之感:“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遂,狂殺王子猷”(《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乘興嫌太遲,焚卻子猷船”(《玩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玩月金陵城西往石頭訪崔四侍御》)。但這種勃發的狂興和逸致卻也正是李白生命激情和人格氣質之內核。
與東晉名士在行為、人格審美層面的實踐不同,置身于詩歌盛唐的李白更進一步將這種逸興湍飛從審美人格層面引入到詩歌創作動機層面。其為詩,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如《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忽憶范野人,閑園養幽姿。茫然起逸興,但恐行來遲。城壕失往路,馬首迷荒陂。不惜翠云裘,遂為蒼耳欺。入門且一笑,把臂君為誰……酣來上馬去,卻笑高陽池。”從“忽”,而“茫然”,而“但恐”,全憑一股逸氣激蕩心間、詩間,所謂“振擺超騰,既俊且逸”(任華《寄李白》)。與此同時,以行為層面的模仿以及人格精神層面的塑造為內在支撐,李白最終將東晉名士的逸韻與風神從人格審美范疇變為一種帶有天才色彩的詩學風格——即飄逸、俊逸之美。這種轉變是李白對于唐詩最為深刻的貢獻之一。
在飄逸、俊發的詩格之造就外,李白的詩歌語言也深受東晉名士清談品藻之風的影響。與前輩玄談之士相比,東晉名士的清談造詣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語言的凝煉和風神之美。如郗鑒傾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而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其次,則為意象之美,如“濯濯如春月柳”,“飄如游云,矯若驚龍”一類的人物品目中所透出的意象美與詩歌語言的意象化深相契合。再次,則是自然真率的趣味。《世說新語·排調》:“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恢笑其語拙,問日:‘君欲云那放?殷日:‘榻臘亦放,何必其槍鈴邪?”余嘉錫注云:“謂己詩雖不工,亦足以達意,何必雕章繪句,然后為詩?猶之鼓雖無當于五聲,亦足以應節,何必金石鏗鏘,然后為樂也。”這種拙率趣味并非單純的不工于詩,而以遺落形骸作為內在哲學支撐。以上種種又集中體現在《世說》一書,劉應登《世說新語序》云:“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李白對《世說新語》極為熟稔,其詩文中有大量篇句都是直接融取《世說新語》中的人物言語、事例、文辭與意境而成,如《送賀賓客歸越》:“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以右軍作比,虛實之際,人物風神盡出。在盛唐詩人中,李白最善于用簡約、真率而富于韻致的詩歌語言為魏晉人物作肖像,如“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雕,倒著還騎馬。”(《襄陽曲》其二)全從《世說新語》山簡習池醉飲之事中衍出。又《九日龍山飲》:“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詠名士孟嘉并以之自比,讀之令人但覺形超神越。其他,如《王右軍》《贈崔秋浦三首》諸篇與杜甫《飲中八仙歌》等都堪稱學習晉人清凝簡約語言風格的典范之作。就體裁而言,則又以五、七言絕二體最能得之,如《山中問答》《獨坐敬亭山》《別東林寺僧》以及眾多樂府之篇在自然真率之中所透出的風神逸韻實亦多得于東晉人物及其言語風流之美,胡應麟曾贊其“字字神境,篇篇神物。”
尤其是東晉名士的那些高度審美化、藝術化的山水品藻之語對李白山水詩歌創作和審美趣味的影響最為直接而深刻,如《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有時白云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帶上了玄覽山水的特點。其對江南尤其是會稽、剡中山水之美的賞會和描摹也往往化用晉人事跡和品藻之語,如《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遙聞會稽美,一弄耶溪水。萬壑與千巖,崢嶸鏡湖里……人游月邊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佇,入剡尋王許”即用顧愷之語。《世說新語·言語》:“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蒸霞蔚。”又《早夏于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江嶂若畫,賞盈前途,自然屏間坐游,鏡里行到,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則雜用王羲之“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以及王獻之“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語。山水的意境之美雖然在晉人手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學高度,然而由于對智悟和玄思本身的熱衷,晉人尚未能在文學尤其是詩歌中將山水之美充分表達出來。直到李白,才繼謝靈運之后,再次將東晉玄學名士對于外在山水和內在情感的雙重美學發現再次納入到詩歌中,營造出一種純然詩性和審美的理想境界,如《山中問答》:“問余何時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至如“朗笑明月,時眠落花”,“晝鳴閑琴,夕酌清月”(《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式的空靈輕清,也深得晉人山水品藻之語的凝練與神韻。不僅如此,東晉名士玄對山水,對晶瑩澄澈境界的審美追求也影響了李白詩歌的意象和詩境,如“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尋陽送弟昌峒鄱陽司馬作》)“人疑天上坐樓船,水凈霞明兩重綺”(《江上贈竇長史》)“明湖映天光,徹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秋登巴陵望洞庭》)等,于俊逸、飄逸之外別成一種明凈秀逸之美。
綜上所述,東晉名士風流之于李白的影響是全方位且深刻的。以風流蘊藉的人格趣尚為契合點,李白對東晉名士風流采取了一種詩性化的接受方式。其飄逸不群的人格氣質,獨特人仕方式的設定和自我期許以及以布衣平交王侯的干謁心態的形成乃至一生的浮沉榮辱都與這種接受方式有著密切關系。在繼承并內化了東晉名士的逸興和“任樂”精神的同時,又充之以盛唐才子式的放蕩不羈,形成了飄逸俊發的詩歌風貌。以《世說新語》為最重要的取法對象,李白將東晉名士清談所追求的凝簡而富于神韻的語言之美以及高度審美化、意境化的山水意象納入到詩歌創作中,營造出一種純然詩性的審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