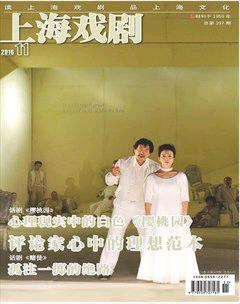當(dāng)斯多克芒不再為真理而戰(zhàn)
穆楊

《人民公敵》是被譽(yù)為“現(xiàn)代戲劇之父”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名作,也是中國(guó)觀眾最為熟悉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戲劇之一。創(chuàng)作于1882年的《人民公敵》,已經(jīng)被世界各地的杰出戲劇家搬演了一百多年,歷史見證了它無(wú)數(shù)的經(jīng)典版本。因此對(duì)任何劇團(tuán)而言,想要重新觸碰它,都注定會(huì)是一次充滿挑戰(zhàn)的探險(xiǎn)。如何才能在前人巨大的成就面前另辟蹊徑?這需要主創(chuàng)們巨大的勇氣、智慧和才情。來(lái)自波蘭的克拉科夫老劇院決心開啟這項(xiàng)挑戰(zhàn),雖然他們顛覆了觀眾對(duì)這部經(jīng)典劇作的常規(guī)理解,刻意避開了對(duì)舞臺(tái)真實(shí)幻覺(jué)的追求,令演出頗具看點(diǎn),但他們也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了易卜生筆下的斯多克芒,新意有余而深刻不足。
克拉科夫老劇院的《人民公敵》在情節(jié)鋪展上基本遵循原著。劇中斯多克芒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被當(dāng)?shù)匾暈榻?jīng)濟(jì)命脈的溫泉,水質(zhì)已經(jīng)受到了細(xì)菌的感染,于是準(zhǔn)備發(fā)表文章公開事實(shí)。可是,當(dāng)?shù)貜恼稳宋铩⑾蠕h媒體到所有居民都因?yàn)樽陨淼睦妫磳?duì)他的做法。當(dāng)?shù)厝瞬坏谌嗣翊髸?huì)上宣判他為人民公敵,而且對(duì)他和他的家人發(fā)動(dòng)了侮辱和攻擊。四面楚歌中的斯多克芒說(shuō)道:“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是最孤立的人……少數(shù)人可能正確,多數(shù)人永遠(yuǎn)錯(cuò)誤。”雖然我們不能簡(jiǎn)單地把斯多克芒理解成完美人格的化身,但通過(guò)這個(gè)為真理而戰(zhàn)的醫(yī)生,易卜生對(duì)社會(huì)弊病進(jìn)行了深刻地批判,他指出:真理完全屬于多數(shù)派極有可能是一句謊言。
易卜生本人要求當(dāng)年首演的挪威導(dǎo)演制造出真實(shí)的幻覺(jué),使觀眾覺(jué)得“每樣?xùn)|西都是真的”。因此,一直以來(lái),追求演劇的真實(shí)性被視為最穩(wěn)妥、最符合易卜生初衷的演劇方法。分明是一部現(xiàn)實(shí)主義劇作,克拉科夫老劇院是如何做到在舞臺(tái)觀念上“背叛”了易卜生呢?如果說(shuō)寫實(shí)舞臺(tái)的感染力主要來(lái)自演員們?cè)鷮?shí)、精湛的臺(tái)詞能力,那波蘭版《人民公敵》對(duì)各種藝術(shù)語(yǔ)匯的運(yùn)用則是極盡所能。他們果斷放棄了話劇舞臺(tái)一貫只重視用臺(tái)詞表現(xiàn)人物和劇情的做法,自由而盡情地調(diào)用音樂(lè)、舞蹈、歌唱、演講等各種手段。他們將原著中僅僅建立在文學(xué)語(yǔ)言之上的戲劇性,外化成極具爆發(fā)力的夸張表演。多種藝術(shù)手段地雜糅,催生了一場(chǎng)多聲部、交響式的派對(duì)狂歡。原著中的人物意志和情節(jié)沖突,也由此肆無(wú)忌憚地噴涌而出。
比如,當(dāng)斯多克芒收到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室寄來(lái)的化驗(yàn)單后,他確證浴場(chǎng)的水質(zhì)已被嚴(yán)重污染。此時(shí),如何能讓觀眾對(duì)污染的嚴(yán)重性有切身體會(huì),是導(dǎo)演構(gòu)思要著力謀劃的。幻覺(jué)式舞臺(tái)能做到的,莫過(guò)于用臺(tái)詞和有限度的肢體表演,來(lái)演繹易卜生臺(tái)詞中所蘊(yùn)藏的情緒。而易卜生的言語(yǔ)在這方面,幾乎做到了極致。醫(yī)生說(shuō):“可是你們知不知道,這座規(guī)模宏大、富麗堂皇、費(fèi)用浩大、人人稱贊的浴場(chǎng)究竟是什么東西?是個(gè)傳染病的窩兒……老實(shí)告訴你們,這個(gè)浴場(chǎng)像一座外頭刷得雪白、里頭埋著死人的墳?zāi)埂a臟到了極點(diǎn)的害人的地方!從磨坊溝流出來(lái)的那些臭氣熏天的東西把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臟了,并且這種害人的毒水還在海灘上滲出來(lái)……”
但波蘭版《人民公敵》卻在語(yǔ)言尚未停止的地方,奏起了讓人產(chǎn)生撕裂感的音樂(lè)。臺(tái)上的演員用塑料杯連續(xù)敲擊油桶、將鐵鎖鏈不斷砸向地面,吹氣手風(fēng)琴高音頻的伴奏,以及電子樂(lè)、鼓風(fēng)機(jī)、警報(bào)器魔幻般的混響,故意不和諧地?cái)嚢柙谝黄穑蓭в兄亟饘儋|(zhì)感的聲音籠罩整個(gè)劇場(chǎng)。這種設(shè)計(jì),將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生活中對(duì)污染的感受,轉(zhuǎn)化成鮮明的音樂(lè)語(yǔ)匯。它帶著強(qiáng)烈的痛感,讓觀眾的心理長(zhǎng)時(shí)間地處于一種焦慮的狀態(tài)之中。除此之外,原著中臺(tái)詞也不再是被死板地念誦,而是配合著這些讓人惴惴不安的音效,以半吼半唱的形式像污水一樣發(fā)泄出來(lái)。導(dǎo)演故意放慢了這部分的舞臺(tái)節(jié)奏,采用漸弱回環(huán)的方法拉長(zhǎng)每句臺(tái)詞的最后一個(gè)的尾音,一種似斷不斷的回響沖擊著劇場(chǎng)中觀眾的大腦。原本只能建立在語(yǔ)言上的情緒感染,就這樣被拓展成了一場(chǎng)末日狂歡式的恐懼。
這樣的導(dǎo)演構(gòu)思,一以貫之地出現(xiàn)在整場(chǎng)演出中。雖然這版《人民公敵》并未作分幕處理,但原著每幕戲的情節(jié)小高潮,導(dǎo)演都極盡所能地調(diào)用各種藝術(shù)手段來(lái)加強(qiáng)劇場(chǎng)演出效果。比如第二幕中斯多克芒和市長(zhǎng)關(guān)于浴場(chǎng)污染問(wèn)題的激烈辯論,第三幕中斯多克芒那句著名的臺(tái)詞——“要是他們不肯借會(huì)場(chǎng),我就借一面鼓,一邊敲一邊走,到街頭巷尾念我的文章”,以及第五幕中斯多克芒對(duì)岳父試圖用金錢來(lái)收買他時(shí)的斷然拒絕……可以說(shuō)導(dǎo)演不但在具體細(xì)節(jié)上做到了奇思妙想,同時(shí)也在整體效果上做到了前后統(tǒng)一。然而,這樣夸張化的處理也有美中不足。由于導(dǎo)演的意圖明確,且從戲的開場(chǎng)就極盡所能地調(diào)動(dòng)起了觀眾的情緒,故而觀眾的期待一下子被抬到了較高的位置。觀眾情緒的高位運(yùn)轉(zhuǎn)自然也就相應(yīng)產(chǎn)生了更加苛刻的觀劇要求。然而,導(dǎo)演卻未能做到全然的夸張化,在劇情中非高潮的過(guò)渡部分,演出仍然保留了一些寫實(shí)手法的影子,故而這部分不僅在整體效果上因?yàn)閺?qiáng)烈的節(jié)奏落差而顯得拖沓,而且語(yǔ)言原本的精神力量也不免在整體嘈雜的劇場(chǎng)氛圍中有所減損。這不得不說(shuō)是該劇的一個(gè)遺憾。
然而,更大的遺憾來(lái)自于該劇的斯多克芒不再為真理而戰(zhàn)。波蘭版《人民公敵》對(duì)斯多克芒的重新詮釋引發(fā)廣泛的討論。熟悉《人民公敵》的觀眾都知道,第四幕“人民大會(huì)”不但是整個(gè)戲劇的最高潮,也最能反映導(dǎo)演對(duì)原著精神的理解。值得肯定的是,波蘭藝術(shù)家在這一幕的處理上,是有新意的。當(dāng)斯多克芒即將發(fā)言時(shí),字幕提示器關(guān)閉,場(chǎng)燈全部打開,演員和觀眾共同暴露在燈光之下,導(dǎo)演將劇場(chǎng)變成會(huì)場(chǎng),把觀眾當(dāng)作民眾。雖然西方演劇觀念在打破第四堵墻后,演員與觀眾互動(dòng)已屬常態(tài),但這種做法是波蘭藝術(shù)家創(chuàng)意的起點(diǎn)而不是終點(diǎn)。這版《人民公敵》的獨(dú)特之處在于:斯多克芒的扮演者完全放棄了劇中人的角色,觀眾也不再是劇中那個(gè)海濱小鎮(zhèn)上的民眾,演員以真實(shí)的身份與中國(guó)觀眾交流起了中國(guó)當(dāng)下的社會(huì)問(wèn)題。但這位演員并沒(méi)有像劇中的斯多克芒那樣,以“獨(dú)戰(zhàn)多數(shù)人”的氣勢(shì)批判多數(shù)人的錯(cuò)誤,僅僅是適可而止地以關(guān)鍵詞的方式提及了“污染”“腐敗”“紅包”等中國(guó)社會(huì)問(wèn)題。隨后,場(chǎng)燈再次熄滅,舞臺(tái)回歸劇情,終幕開始。
對(duì)于這樣的設(shè)計(jì),導(dǎo)演在演后談中解釋說(shuō),他所理解的斯多克芒和市長(zhǎng)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涇渭分明的好人和壞人,斯多克芒無(wú)疑是一個(gè)堅(jiān)定的理想主義者,但理想主義者并不是完美的人格。這樣的人,會(huì)為了理想不顧一切,也會(huì)適得其反地忽視他人的利益,故而他的行動(dòng)會(huì)遭到社會(huì)的反對(duì)。導(dǎo)演無(wú)意貶低斯多克芒的精神或背叛易卜生的原著,只是認(rèn)為個(gè)人自由思考是更高的價(jià)值。正是基于導(dǎo)演對(duì)斯多克芒性格困境和缺陷的認(rèn)知,他想在舞臺(tái)上呈現(xiàn)一個(gè)不愿過(guò)多發(fā)表意見的斯多克芒。
那么對(duì)于這個(gè)不再為真理而戰(zhàn)的斯多克芒,我們應(yīng)該如何評(píng)價(jià)呢?
首先,舞臺(tái)上的斯多克芒和導(dǎo)演詮釋的斯多克芒相去甚遠(yuǎn)。雖然導(dǎo)演避開了易卜生的社會(huì)批判,著力從性格上理解斯多克芒的命運(yùn),有其合理性,但舞臺(tái)呈現(xiàn)沒(méi)能實(shí)現(xiàn)導(dǎo)演意圖。按照導(dǎo)演的理解,他故意不讓演員對(duì)敏感的社會(huì)問(wèn)題發(fā)表具體的意見,是因?yàn)樗幌胱尅八苟嗫嗣⑹健钡娜宋镞^(guò)于強(qiáng)調(diào)自己真理在握,以免這無(wú)形中會(huì)綁架他人的頭腦,剝奪他人自由思考的權(quán)力。從尊重自由的意義上說(shuō),他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斯多克芒性格中的缺陷和他堅(jiān)持真理的決絕斷不可分。因?yàn)椋瑳](méi)有對(duì)真理的義無(wú)反顧,就沒(méi)有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顧一切。它們就像一個(gè)硬幣的正反兩面,統(tǒng)一在斯多克芒執(zhí)拗、較真的性格之中。導(dǎo)演在放棄斯多克芒對(duì)真理的堅(jiān)持時(shí),其性格的復(fù)雜性也就被取消了。所以舞臺(tái)上呈現(xiàn)的斯多克芒只是一個(gè)大概知道中國(guó)有污染和腐敗的外國(guó)人。對(duì)這個(gè)外國(guó)人在中國(guó)舞臺(tái)上提及這些問(wèn)題是何目的,觀眾們看得一頭霧水,甚至有人覺(jué)得其有嘩眾取寵之嫌。因此,以導(dǎo)演自己的構(gòu)思為標(biāo)準(zhǔn),他的詮釋固然合理,但舞臺(tái)呈現(xiàn)卻力所不逮。
其次,舞臺(tái)呈現(xiàn)的斯多克芒和易卜生筆下的斯多克芒相去甚遠(yuǎn)。易卜生筆下的斯多克芒之所以在一百多年的世界演劇史上魅力不減反增,不在于他討論的污染問(wèn)題恰好是當(dāng)下的全球熱點(diǎn),也不在于他單純地想要堅(jiān)持他是正確的,而在于他的戰(zhàn)斗指向了全體人類共同的精神生活。人類社會(huì)需要規(guī)范,更需要對(duì)規(guī)范的反思,而有能力、有膽量對(duì)陳腐社會(huì)進(jìn)行批判的人,往往是少數(shù)。這些少數(shù)派,必然會(huì)經(jīng)受社會(huì)上大多數(shù)人的侮辱和攻擊,但斯多克芒的精神力量恰恰在于:人數(shù)眾多的反對(duì)派,非但不能將他擊垮,反而會(huì)增加他改造現(xiàn)實(shí)的決心和勇氣。斯多克芒不愿意失去了思想的頭而茍活,他想要借一面鼓,一邊敲一邊走,到街頭巷尾念誦的那片文章,大概也只有八個(gè)字“拒絕虛假、追求真理”。導(dǎo)演將易卜生的“少數(shù)”簡(jiǎn)單地理解成數(shù)量上的多少,殊不知易卜生的少,所指的不只是數(shù)量上的稀有罕見,更是質(zhì)量上的鳳毛麟角。這里“少”的意義在于:敢于和虛假較真的人因稀有而高貴!如果我們明白了易卜生在求真意義上,對(duì)社會(huì)震聾發(fā)聵的批判,自然就不難理解,他筆下的斯多克芒是難以超越的。從為真理而戰(zhàn)到有所保留,兩個(gè)斯多克芒的距離,正好是我們對(duì)崇高的理解。
敢于批判是思想自由的前提,當(dāng)斯多克芒不再為真理而戰(zhàn),所謂的自由只能是一種空洞的安撫,它脈脈溫情的面紗背后,不過(guò)是另一種形式的茍活。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真實(shí),如果一個(gè)社會(huì)仍在用謊言呈現(xiàn)真相,那這個(gè)社會(huì),無(wú)論是波蘭還是中國(guó),就還需要易卜生筆下那個(gè)為真理而戰(zhàn)的斯多克芒醫(yī)生。
(作者為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戲劇學(xué)博士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