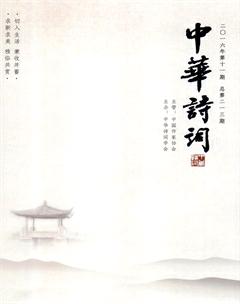賦比興之當代運用
袁忠岳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不僅以詩的形式給我們保留了2600多年前各地域各階層先民豐富多彩的生活狀態,而且其中的“詩大序”對于詩這一文體的心理發生過程、諷喻教化功能以及它的獨特創作方法都有著直切詩的本質的深刻認識和高度的理論概括。中國詩歌千百年來各種風格流派異彩紛呈,汪洋恣肆,蔚為大觀。但萬變不離其宗。時至今日,其創作方法仍不出“賦”、“比”、“興”三字。
何為“賦”、“比”、“興”?自古以來解釋紛紜,各種說法林林總總,不過從中還是可以理出一個大致能夠得到普遍認同的線索來。首先是把“賦”和“比興”相較,漢·鄭玄在《周禮注疏》中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認為“比”刺“興”美、“賦”則兼之的觀點似乎太機械死板了,但道出了“賦”與“比”、“興”不同,在于“賦”是直陳,“比”、“興”則用借托。這一點后人大多沒有異議。如宋·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詩集傳》)梁·鐘嶸也說:“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詩品序)這直接性就是“賦”的一個特點。與此相連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敘事性,那就是“直陳”、“敷陳”中的“陳”了。不用任何比喻、意象來直接寫物敘事,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含他意,這就是“賦”的方法。我忽然聯想到詩歌界一度流行的反抒情、反意象的敘事熱,這不就是我國古代就有的“賦”的寫法嗎?怎么又成了新潮流、先鋒派了呢?雖然說,人要直,詩要曲,詩忌直露,但不等于說用直接敘事法就寫不出好詩。杜甫的《北征》、《三吏》、《三別》等就是。《漢樂府》和白居易的《新樂府》中也是不乏佳篇。我在《中華詩詞》2003年5期評論沂蒙老農的詩集時,曾提出應有“現代樂府詩”,說明“賦”的寫法仍有其現實作用。詩人高昌對于“時人久疏白樂府”就很有感慨,決心用自己的詩筆來填補此空白,寫了《哀礦難》等“現代樂府”;這都離不開“賦”。獲獎的劉征《紅豆曲并序》,也是用“賦”的敘事手法來寫的,不過關于昭明太子蕭統和農女紅豆的故事則是虛構的。正如作者自述“賦詩任臆所之”,“真實不虛者只一情字”。事可虛構,情不可虛構。即使有些現代詩人標榜的冷抒情、零感情,也是有情在的,只是不露聲色而已。
“賦”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鋪”、“敷”(鄭玄“賦之言鋪”,晉·摯虞“賦者,敷陳之稱也”)。這是一種向外鋪展擴張型的寫法,用對仗、排比等句式把一件事多方面地展開來敘述,如《詩經》中《木瓜》一詩即是如此: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已故詩人郭小川就喜歡用這種反復回旋的句式,排浪式地向前推進詩意,被人們稱為“新辭賦體”。
鋪張的另一層意思是講究辭藻繽紛華麗。劉勰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到漢代這種寫法蔚然成風,并游離于詩,似成另一文體,被人稱為有韻之散文。這一古老文體后來漸漸衰落,但在現代生活中它并未完全消失。我們在各地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景點常能讀到現代人寫的賦,有名的就是巴蜀鬼才魏明倫寫的《中華世紀壇賦》和《大會堂賦》。不過,這不是大眾化的文體,沒有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和嫻熟駕馭辭藻、典故的腕力,是寫不出來的。雖然,正如前述,直陳其事的“賦”法在當今詩詞創作中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尤其對于“救濟人病,補弊時闕”的現實題材。至于其直、露、實的弊病,也不是不可加以補救和轉化。清·劉熙載《藝概·賦概》就說:“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聶紺弩的詩大多為生活實錄,用“賦”直陳,但讀起來卻很有味道,意蘊很深,即是最好的例子。
較之“賦”的直陳,“比”、“興”的婉曲借托應該更加適合詩質的表達。故“詩要比興”,是歷代詩人的共識。劉勰《文心雕龍》就單列一章談《比興》。清·吳喬《圍爐詩話》云:“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辭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唯賦而少比興,其辭徑以直,如人而赤體。”他從藝術性上比量,認為“比”、“興”要高明于“賦”。“賦”是本事直觀,為單層結構。唐·孔穎達就說:“不譬喻者,皆賦辭也”(《毛詩正義》);“比”、“興”是用相似或相關的意象透視本事,故為雙層結構,孔穎達說它們“同是付托外物”(同上),這“外物”也就是吳喬說的“衣冠”。要把“賦”與“比”“興”區別開,還是比較容易的。至于同為“付托外物”,“比”與“興”二者有什么不同?這卻是古代詩學上議論紛紛不斷加以探究的課題。宋·朱熹的《詩集傳》中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這只是從語句修辭的角度去解釋二者之異,辨認不難。如高昌在《玩轉律詩》一書中談及律詩的謀篇,就以此為依據,分作“以賦開頭”、“以比開頭”、“以興開頭”幾種,他舉古詩例子來說明。在當代詩詞中也是不乏這三類例子的,如:李增山《偕妻游張家界》:“張家界上李家游,萬座青山兩白頭。我看夕陽紅一點,宛如老伴少時羞。”(《中華詩詞》2013.4)開頭就是用“賦”直述,“白頭”是借代,與“青山”相映,來襯托“紅一點”。張君戀《題山瀑圖》:“滾滾銀河下九垓,負圖鱗介似平臺。伊誰撒下天羅網,欲把青山拽上來。”(同上2013.2)開頭就是用“比”,以“銀河”喻“山瀑”,于是“青山”就是河中魚,憑君打撈了。秦兆陽《霧景》:“霧里嫦娥云里山,奇峰隱約九重天。始信文章有妙訣,但在虛實有無間。”(同上2013.3)開頭就是用“興”,由縹緲的云霧起興產生聯想,點出寫詩的訣竅就在這亦虛亦實、似有似無之間。這個“興”還是有“比”的意思在內的。像“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引起物和所詠對象無直接關聯的純“興”例子,只有在信天游等民歌中才用得比較普遍。
由于不滿足這種句式修辭上的簡單化解釋,更多詩人學者就從詩的藝術表現和欣賞角度去體悟“比”、“興”二者之不同,由此開拓了詩歌創作和詩學研究的廣闊途徑,從而使之達到一個更高境界。略舉以下三說證之:一,“比顯興隱”說。最早見于《毛詩·關雎傳·正義》,毛亨說:“比之于興,雖同是付托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后隱,故比居興先也。”劉勰也很贊同這一觀點,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并批評當時詩風是“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在劉勰的心目中“興”是優于“比”的,其重輕判然分明。二,“興在象外”說。梁·鐘嶸《詩品》序說:“文有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比”、“賦”無新意,“興”卻是全新解釋,對后世影響深遠。如唐·司空圖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宋·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等經典名言,以及言外、味外、韻外、弦外、景外等種種提法,在詩藝上都是一脈相承的。到清·馮班就認為嚴羽說唐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鈍吟雜錄》卷五),這就更加扼要概括了。盡管劉夢得說的是“境生象外”,與“興在象外”的意思還是相去不遠的。三,“興無寄托”說。清代常州詞派把“比”、“興”引入詞的賞析評論,提高了詞的品位,尤其以有無“寄托”來區別“比”、“興”,很有創意。周濟說:“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介存齋論詞雜著》)這兒的“有寄托”指“比”,“無寄托”就是“興”了。不過“興”的“無寄托”不同于“賦”的“無寄托”。“賦”是實打實的“無寄托”,一眼看到底,無法見仁見智。“興”則是“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宋四家詞選》),也就是要“有寄托人,無寄托出”。詞人是帶著情思進入創作狀態的,心中自有寄托,但寫作時不能“喻可專指,義可強附”,而要“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這樣寫出來的詞似“無寄托”,才能讓讀者見仁見智。對于“興”的理解不止以上三種,但不論解釋如何不同,都跳不出一個“隱”字,“象外”也好,“無寄托”也好,不都是求“隱”嗎?就是現代人提出的“興”是象征、“興”是隱喻等觀點和說法,也是圍繞著“隱”展開的,并由此和現代派的朦朧、晦澀接上軌。可見,“賦”、“比”、“興”雖僅三字,其包容大得很。
當代詩詞要出精品,除了“賦”法,還是要在“比”、“興”上多下工夫,不斷創新。“比”的方法好掌握,只要抓住二者的相似點就可以了,在創作上運用也比較普遍,尤其是詠物詩,似乎還非用“比”不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劉禮鵬的《煙花》:“拔地沖天氣勢雄,千姿萬態獻姣容。可憐魂斷煙飛處,幾許繁華一瞬中。”(《中華詩詞》2012.7)把某些人鉆營、上爬、榮貴、幻滅的一生,壓縮到煙花施放的短暫瞬間,其諷刺味、荒誕感極強。杜守江的《鏡子》則向我們展示了另外一種人生選擇:“歷經磨練鑄精魂,何必方圓大小分。心里從來無自己,空明一片盡他人。”(同上2013.3)詩也如鏡子一般光亮干凈。它們都是詠物詩。
“興”對藝術的要求更高一些,但也不是不可企及。首先,不要把“興”僅僅看成是個技術活,它是歷代詩人對詩的極致境界的追求。宋·姜夔說:“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白石道人詩說》)“興”就是這樣一條通向極頂的山徑。試看被常州詞派視作“無寄托興”的樣板之一的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那只在黑暗凄冷的環境中惶恐不安的孤雁究竟是誰的影子?眾說紛紜。有說是作者自況,有說為賢人擔憂,還有指名道姓的說是為惠州溫氏女超超夭亡而作。這些都是無法落實的,也無關乎該詞藝質,可以任人猜想。大家推崇這首詞并為之傾倒的原因,在于它構筑了一幅獨特的凄冷意境,刻畫了一個孤獨不安而又不甘無為的藝術形象,為我們奏出了一首哀婉動聽的雁鳴曲。正如鄭文焯在《手批東坡樂府》中說的:“不必附會溫都監女的故事,自成馨逸。”不從意境形象的創造人手,一味地追求“隱”,那無異于緣木求魚,和“興”的本意是背道而馳的。“隱”是增加詩詞的藝術魅力,不是故意設置閱讀障礙。《中華詩詞》載彭明華的《山行有遇》,就讓我們領略到了“興”的一個現代版。其詩為:
無心驚草木,何處振清響。一影動空枝,已在青云上。
題目是《山行有遇》,遇見什么呢?詩中并無交代。但我們從“驚”、“振”、“動”三個動詞可以猜想這大概是個禽鳥,而且此鳥非常敏捷,你只能聽到“清響”,見到“空枝”,卻難覓其全貌。直到末句“已在青云上”,讀者才匆忙抬頭一睹此鳥之真像,原來是一只矯健之鷹,那已到了詩外了。熊東遨先生點評:“何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讀此可悟一二。詩不在長,得勢則雄;詩不在多,得一即可。”詩妙,評亦妙。
方法本身沒有高下之分。“賦”、“比”、“興”都能寫出好詩,因為它們追求的藝術目標是一致的。而且,相互之間并非勢不兩立,往往可以兼容,在進行創作時沒有必要分得很清,只要根據所詠內容和自己興趣,選擇最恰當的方式即可。了解了“賦”、“比”、“興”的同和異、所長和所短,我們在創作時就有了選擇,有了依傍,對于自己的發展可以有更切合個性的設計,設立更為明確的目標。如此,我們就對得起古人在漫長的歲月里,在詩歌創作方法的研究上。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的心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