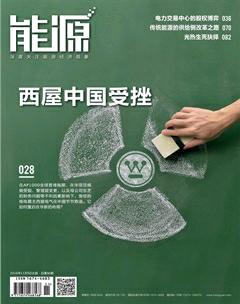爭議光伏標桿上網電價
李帥
最新的光伏標桿電價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這背后是一場政府、企業、產業的激烈博弈。
國慶節前夕,似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節前的興奮之中。但是,發改委的一篇征求意見稿同時也在節前流出,卻讓整個新能源領域的人高興不起來,尤其是在光伏領域。文件中光伏標桿上網電價的大幅度下調,讓人很不理解,一時間爭議四起。
9月2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調整新能源標桿上網電價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在意見稿中,光伏電站的標桿上網電價降幅均超過了20%,一類資源區降幅超過30%,分布式光伏按三類資源區進行定價,降幅也都超過了25%。
經過近20天的發酵,劇烈的反響似乎收到了效果。消息稱,10月17日,國家發改委召集多個部門和大型發電企業、電網企業人士召開座談會,聽取各方對調整新能源標桿電價的意見建議。而作為聲音最多的行業,光伏勢必成為討論的重點。
光伏領跑者計劃實施之后,不斷爆出低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給人的感受都是光伏的成本已經下降了很多。光伏標桿上網電價的下調在意料之中,但是為何國家此次欲調整如此大的幅度?如此劇烈的下調又會對光伏行業和企業產生什么影響呢?
低價的緣由
6.30之后,光伏組件價格大幅跳水,度電成本的下降已經成為一種既定事實。許多業內人士也都認為,光伏標桿上網電價確實有下調的條件,而且相比其他的可再生能源,光伏的可下降空間是比較大的。
一次較大幅度的下調也就并不完全是一種突然,無論是在政府還是產業,都對此有一定的心里準備或是暗示。
在國家層面,國家能源局副局長李仰哲在講話中曾表示,新能源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和矛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棄風棄光的問題比較突出,二是財政補貼資金缺口較大。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累計達到550億元,原有的補貼模式難以為繼。決策部門面臨著極大的壓力,關于產業發展未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選擇也遇到了現實的挑戰。
十月下旬,在2016年北京國際風能大會的開幕式上,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的李鵬處長表示,除了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外,新能源領域本身也有很強的替代效應,風電、光伏甚至光熱等誰的成本下降的快,誰就會在能源轉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無疑,不管是出于可再生能源基金缺口的原因,還是促進成本進一步下降的考慮,成本下降和補貼退坡已經成為“十三五”光伏發展的主旋律。
為什么國家會提出大幅下調電價?這背后或許還有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考核和綠色證書交易制度的原因,通過這種方式,既可以通過市場化方式確定補貼的額度,也可以減少對財政直接補貼資金的需求。
隨著巴黎協定的簽署以及能源轉型低碳化的趨勢,為了實現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標,發電企業可以通過綠色證書交易來實現。
根據相關報道,按照全國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到15%的要求,2020年,除專門的非化石能源生產企業外,各發電企業非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應達到全部發電量的9%以上。
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分析師劉建東告訴《能源》雜志記者:“化石能源污染的外部性成本還沒有表現出來,通過配額交易把化石能源的錢拿出一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在研究上這是一個思路,政府操作還需要一個流程,過程可能比較漫長。”
意見稿中除了價格下降的幅度大,日期也很緊迫。文件規定2017年1月1日以前備案并納入財政補貼年度規模管理的光伏發電項目,執行2016年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2017年以前備案并納入財政補貼年度規模管理的光伏發電項目但于2017年6月30日以前仍未投運的,執行2016年上網標桿電價。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對《能源》說:“調整真正起作用是在明年的六月底,價格下調還有一個預期,半年多的時間價格的預期還是比較難做的。如果是在半年多之后的話,有的機構可能比較樂觀,認為價格下降會比較快,測算出的價格就比較低。”
不難看出,進入2016年,光伏的平價上網似乎已經提上了日程,在領跑者計劃的競價機制下,光伏的“真實價格”越來越多被發現。但是,領跑者計劃的參與者多是大型企業,而且報的價格也有各種各樣的考慮,幾輪下來,我們在對一個個的低價感到驚嘆的同時,難免也會產生各種議論和質疑。
而在此時,國家下發的意見稿中又明文提出了很低的光伏標桿上網電價,一時間,不管是地面電站還是分布式電站,都引來鋪天蓋地的紛爭。
爭議不斷
“按照現在的投資水平來看,在不考慮棄光限電的情況下,下降一毛錢還是可能的。”不止一位專家對《能源》雜志記者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但是現在的調整幅度遠遠超過行業的預期,除了一些綜合能力比較強的大企業,對大部分企業來說是吃不消的。
領跑者項目的價格一個比一個低,但是領跑者項目確實有著許多特殊的緣由。對于領跑者價格的參考意義,彭博新能源財經的分析師劉雨菁認為:“征求意見稿中的價格基本是按照領跑者的平均中標價格來定的,但領跑者的價格并不一定有廣泛的行業代表性。首先,領跑者中標企業基本都是大開發商,在資源整合以及貸款成本上有明顯優勢。第二,領跑者項目由當地政府統一推進項目開發,項目落地比較容易,過程比較透明,也會增加這類項目的吸引力。如果將領跑者項目的平均中標價格推廣,會進一步提升行業集中度,也有可能加重已經存在的項目質量問題。”
對比中國招標價格和國際招標價格,劉雨菁介紹道,國內外招標價格并不一定有直接可比性。國際上許多超低價的中標項目其實都可以在2-4年之后才并網交付。但國內的周期一般在6-12個月,組件價格的不確定性少很多。具體來說,今年從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組件的價格下降許多,但是從現在開始到明年上半年,組件價格不具備繼續大幅下降的條件。
另外,據記者了解,目前國家正鼓勵土地的高效利用。按照現在的價格,農光、漁光互補項目建造成本等的具體情況可能差別非常大,成本會比較高,特別是在三類資源區。如果國家想力推水面、農業的光伏項目,價格定的過低將不利于南方省份做農光、漁光互補。
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由于目前許多互補項目其實都沒有真正關注互補產業,低電價也能促使這部分開發商認真考慮互補產業的經營問題,從而擴大收入來源。
針對意見稿的內容,有業內人士也提出了幾條建議:一個是電價調整不能太猛,擬0.65、0.75、0.85元為宜;二是時間不能過快,擬2017年8月30日后實施;三是對于光伏扶貧特事特辦,另行定價。
除了地面電站外,分布式光伏對價格的反響則更大。
“退坡制度最終實現真正平價上網是確定目標,可本次征求意見稿的光伏上網電價下調幅度大大超出預期,業內聲音已經哀鴻遍野,若真的執行下來,會讓剛起步的分布式市場大受打擊,對行業發展極為不利。”九州方圓(北京)副總經理梁燦告訴《能源》記者。
的確,分布式光伏并不具備降價的條件,具體到某些市場可能有降價的空間,比如一般工商業和有條件地區的大工業用戶。但是下一輪適合做分布式的屋頂和用戶情況可能沒有之前那么好,雖然光伏的成本下降了,但是也不具備降價的條件。
事實上,由于分布式光伏的補貼是基于煤炭的標桿電價和消費電價,2014年到2015年煤炭的標桿電價和消費電價都下降了許多,相當于分布式的收益已經下降了,所以分布式光伏可降的空間本就有限。
劉建東也表示,分布式光伏主要是應用在工業園區,電力過剩的情況下,隨著直購電和電力交易的開展,大工業用電價格比較便宜。在用電比較便宜的情況下,會有許多的觀望者,有可能不會輕易選擇建設分布式光伏發電。
無論如何,意見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月11日,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再次下發《關于調整新能源標桿電價的征求意見函》,分布式光伏補貼標準由之前的“一類資源區0.2元/千瓦時、二類資源區0.25元/千瓦時、三類資源區0.3元/千瓦時”調整為“一類、二類資源區0.35元/千瓦時,三類資源區0.40元/千瓦時”,而地面電站維持不變。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處長支玉強在公開場合指出,當前電價模式越來越難以維系。由于可再生能源規模快速擴大,技術進步明顯,相關部門制定標桿電價的難度不斷增加。由于政府部門與企業是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存在一定信息不對稱,固定電價政策可以說越來越難。
標桿電價水平應兼顧上下游發展情況,避免光伏電價補貼的調整對上游的制造業帶來較大的沖擊,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怎樣找到平衡是標桿電價確立的關鍵。
毫無疑問,為了實現最終的平價上網,光伏行業必須承受補貼不斷下降帶來的痛苦。在一定時期內,通過相應的價格促進和倒逼行業的發展本無可厚非,但是要對市場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進行合理的測算和預測,我們似乎還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