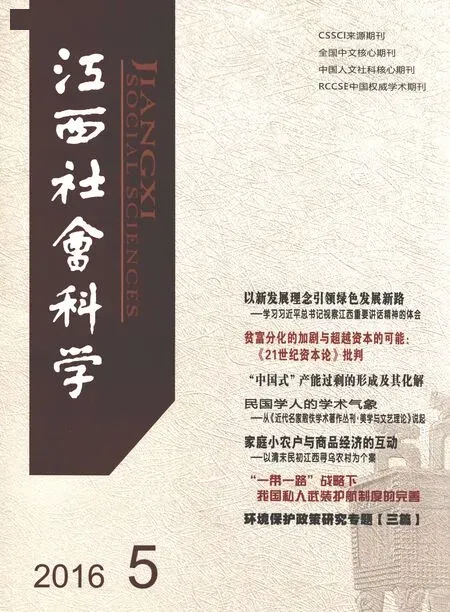家庭小農戶與商品經濟的互動
——以清末民初江西尋烏農村為個案
■溫 銳 鄒雄飛 陳 濤
家庭小農戶與商品經濟的互動
——以清末民初江西尋烏農村為個案
■溫 銳 鄒雄飛 陳 濤
長期以來,傳統中國農村的家庭小農戶經濟“被靜止”為阻礙商品(市場)經濟發展的“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然而,解讀毛澤東的《尋烏調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尋烏農村的家庭小農戶,借助遍布于城鄉的墟鎮與商道,將自己的農業生產,多元兼業與打工經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場與商品交換平臺,農民的身影在市場網絡中則是隨處可見。因此可以說,家庭小農戶經濟與當時水平的商品市場實已融為一體,可謂是“須臾難離”。
傳統中國農村;家庭小農戶;商品經濟;清末民初尋烏
溫 銳,江西財經大學生態文明與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
鄒雄飛,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
陳 濤,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江西南昌 330013)
隨著中國農村改革實踐和學界對于家庭小農戶經濟認識的不斷深入,將“家庭小農戶經濟”稱為是阻礙商品(市場)經濟發展的“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的傳統觀點,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學者們進一步闡述了舒爾茨“理性小農”的觀點:中國傳統的家庭小農戶經濟具有“類似資本主義”的特點[1](P1),也可以成為新生產方式的“孕育母體”,兼具自發的“競爭、適應、轉化功能”和“動態開放本質”[2](P3);家庭農場式的經營具有“效率最高、單產最多、技術吸收最快”等優點[3];在商品經濟的持續發展進程中,家庭小農戶經濟實是市場經濟網絡中的一個個“網眼”,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也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內驅力”與“活水源頭”。[4](P368-369)
本文基于毛澤東1930年所作的著名《尋烏調查》及其他史料,以位處中國東南腹地贛閩粵三省交界的清末民初江西尋烏農村為研究個案,立足于遍布于城鄉的墟鎮與商道這組商品交換平臺,從家庭小農戶的農業生產、兼業打工經商、日常生活和市場網絡中的農民身影等視角,全方位展示清末民初尋烏家庭小農戶與市場經濟的多向互動,并以此為典型個案,進一步佐證將家庭小農戶經濟“靜止”為“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深陷的學術誤區。
一、農業生產與市場的密切聯系
盡管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特別強調,清末民初尋烏的農業生產總體處于傳統農業社會階段,但作為受到近代商品經濟不斷沖擊的地區,與傳統商品經濟共生共存的尋烏農村家庭小農戶經濟從農業生產基本要素的配置,到土地租佃地租率的競爭博弈,再到農產品的流通,都無一不與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系。
(一)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
土地、資金、勞動力、勞動工具等生產要素是農業生產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源。在農業生產實踐當中,家庭小農戶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配置自己的生產要素。從史料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尋烏家庭小農戶對于上述生產要素的配置即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處理的,其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土地要素流轉通過市場實現優化配置。在清末民初的尋烏農村,作為農業生產基礎性要素的土地之佃、典、賣,都體現了市場化配置的特點。例如,在尋烏全部農村土地中,公共土地占40%,占全部農村人口總數不足8%的地富階層占有土地的30%,占人口總數90%以上的農民僅有30%左右的土地。[5](P105)這也使得當年尋烏地權占有嚴重不均,許多農民都缺乏賴以維生的土地所有權。然而,在地富階層受近代商品經濟刺激而普遍逐利工商經濟大潮的情形之下,全部公共土地、絕大多數的地富占有土地,以及部分中農自耕農因距離家中較遠或耕作不便而出租或佃入的土地,都是通過當時邊區較為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及其市場化運作進行的,也促使土地與家庭小農戶的勞動力資源實現了優化組合,從而既為缺地少地的農民維生提供了重要條件,也實現了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農地生產效率的提升。[6]再如,在尋烏農村,以土地典當(包括“過手典”和“不過手典”)和“賣絕”為主要形式的地權流轉,也是在市場規范下并借助于市場交換來完成的。而隨著市場供求、土地肥沃程度上下浮動的田地典賣價格,則進一步凸顯了土地資源市場化流轉配置的特點:典當坑田每石租為15元,塅田20元到25元;售價坑田每石租17元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元到40元。[5](P143-144)
農業生產的人工投入依靠市場調劑。眾所周知,在不增加土地面積和提升農業科技投入的情況之下,投入更多的人工和“精耕細作”,就是傳統家庭小農戶普遍用來提升農業單產的主要方法。同時,農業生產的周期長、季節性強和勞動強度大等特點,也決定了農業生產需要通過市場機制調劑其人工投入。具體看清末民初的尋烏農村:家中或多或少帶耕了“十幾二十石谷(田)”的大中地主,農忙時節通常需要雇請一個長工幫忙,具備“萬戶”身家且人丁單薄者則要雇請兩個長工才足以應對基本的農業生產所需[5](P124);除了大中地主要雇請長工、短工幫忙之外,“新發戶子”(小地主中的一種)在農忙時期,也多需要雇請零工或雇工幫忙;即便終日勞作于農田的一般農民,出于“追趕農時”等需要,也可能有著雇請人工(部分是相互“換工”勞作[7](P412))幫忙的需要。上述農業生產中相應人工的投入,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助的性質,但其既是在市場交換原則規范和影響下進行相應人工補充或置換的,也與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緊密相連,特別是地富階層雇請長工、短工、零工等幫忙,都是要“出工錢的”[5](P143),更是集中體現了其與市場的緊密聯系。
牛力、種子和勞動工具等生產資料需借助于市場調配。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對于當時占全部農村人口70%之多的貧苦農民生產資料狀況的掃描,實際上就揭示出了短缺時代尋烏農民各類農業生產資料普遍缺乏的現實:貧民中的境況最好者(半自耕農),土地也“不夠使用”;貧農中人口的最多者(占貧民總數60%的佃農),雖無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數有自己的牛,部分家庭甚至有兩到三頭牛;佃農中的窮困者,同樣無土地,但犁耙等生產工具“多窳敗”,本錢很少,牛則是幾家共養一頭或是替地主飼養,自己僅能“定得一爪子”;至于貧民中的最窮困潦倒者,則是無地、無本錢、無牛力、有犁無耙,甚至借米借鹽都是常有之事。[5](P132-133)在如是情形下,為了保障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開展,牛力、種子及其他農業生產必備工具,就需要借助于市場的借貸來調配。例如,在當時的尋烏農村,貧民“為了蒔田”,到了農歷三月要借稻谷做種子。再如,農忙時節,缺乏牛力者要向親友或地富租借牛力來耕田;缺乏或生產工具“窳敗”的農民,則還需要租借或購買相應生產工具從事農耕生產。[5](P133、P147)
(二)市場機制中的地租博弈
土地租佃的市場化運作及租佃雙方在市場機制影響下的多元競爭博弈,使得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土地租佃的地租種類變化、地租比率的確定以及高低波動,都深深刻上了市場的烙印,也凸顯了地租博弈與市場交換的密切聯系。
1.地租的種類
與學者們對于整個贛南閩西農村地租調研的普遍結果相一致,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土地租佃的地租也基本是以實物地租為主,貨幣地租并不占主體地位。毛澤東更是明確指出,當年尋烏農民所繳納地租,實物地租(谷物)占80%,按谷物價格折錢交租的“貨幣地租”占20%。而從《尋烏調查》可見,當時尋烏農村土地租佃還存在一些名目的“附加租”。例如,地主將田批給佃農耕種,五年一批的單批每石租收“批頭錢”一毛,十年一批的雙批則收兩毛或三毛;再如,當時佃農承租地主土地,要每一年或兩年給地主送一只“田信雞”,雙橋區佃農每年還要請地主吃一頓“田東飯”。[5](P140-141)
2.地租比率的博弈
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土地租佃的地租比率,盡管被有的學者認定為在50%—56%之間[8](P150),但依據對于當年尋烏地租比率的重新估算,如果將在當時農民維生中具有關鍵作用的土地“副產”(番薯、芋頭等雜糧)納入土地總產量計算,“實際地租率”就只有33%—37%。[9]另據我們在尋烏的反復實地調研,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各地僅有肥田的地租比率在50%及以上,貧瘠之田、山田則因無人愿耕而只收20%甚至于更少的地租。[10]
定格于當時尋烏土地租佃雙方的地租比率博弈場景,其一,雖然土地收獲采用“見面分割”之法,原定雙方各半,“名義地租率”為50%,但遇有“撮谷種”之情形,佃戶會在雙方分割前先撮出一部分補償因留秧田而來的損失。此種情形之下的地租比率,即便只計算“正產”,也明顯會低于50%。其二,分享土地收獲采用“量租制”分成之法的,主佃雙方原本約定分獲正產的5.6與4.4,但出于佃戶“窮困日多”的狀況和彼此利益的休戚相關,雙方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多按5:5的比率分享正產。其三,盡管在“定額租制”下,主佃雙方原已商定分成比例、租谷質量及“半荒無減”等,但在農業生產遭遇災荒或歉收之際,雙方最終多是“精冇照分”。[5](P136-142)這種情形下主佃雙方權衡實際的地租博弈,地租比率即便按正產計算也不會超過50%。其四,在客家民系聚族生活的尋烏農村社區,那些當時宗族民眾很可能“都有份兒”的社區“公田”是被出租土地的主體部分,本族人或村中鄰里承租耕種該類“公田”,還通常能照普通地租比率享受到“一至二成”[11](P595)的優惠。上述情形的博弈,便使得當年尋烏全縣原本呈4:6之勢的“見面分割制”與“量租制”,最終還是正產的各得半壁江山,甚或要低于正產的50%以下。
3.市場變化導致地租比率高低波動
19世紀60年代潮汕地區的開埠,使得尋烏因扼守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及其商品經濟腹地商貿孔道而商品經濟日漸興盛,獲利“更為豐厚”的工商經濟也不斷刺激和吸引著社會各個階層爭相逐利其中。這樣,承租“公田”與地富的土地求取生存發展保障就不再是農民維生的唯一首選方式,從而也使得土地租佃制度盛行下的當時尋烏農村土地租佃比率,因受到市場供求等機制的影響而一度呈下降態勢。
進入民國之后的尋烏,因長期受到戰亂等的影響而使傳統商道被堵塞,這也使得民眾的外向型生存發展選擇受限,民眾對土地的依賴性轉強,從而也同樣因市場供求狀況轉換而致使地租比率呈攀升之勢。至蘇區革命前夕,尋烏農村土地租佃的實際地租比率便由33%—37%上升為38.5%。[9]
(三)農產品流通依賴于市場交換
《尋烏調查》中對城鄉市場上眾多農產品的羅列,在說明當時尋烏城鄉商業繁盛的同時,也突出體現了其流通與市場交換的緊密聯系。
首先,尋烏的農村圩場與縣城市場充斥著各類農產品。循著毛澤東當年調研時的視野,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無論是在當年尋烏吉潭、牛斗光、留車、尋烏縣城、澄江、石排下等六大重要市場,還是在岑峰、篁鄉、三標等普通小圩場,大米都是其中主要售賣的農產品和商品之一,且毫無疑問地成為第一大生意;而柴火、豬肉、豬子、雞鴨、竹木器、各類小菜、魚、水果等農副業產品,都是“不小的生意”,也在當時尋烏城鄉圩場生意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5](P94-96)
其次,農產品在尋烏城鄉出口貨物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從表1可以看出,大米、茶葉等農產品不僅是當年尋烏最主要的對外出口貨物,還主要是通過境內外市場來解決其流通問題的。例如,在農地收獲物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大米,除了供應給城鄉居民食用之外,便主要是銷往福建武平和廣東平遠、梅縣等缺糧的鄰近區域;茶葉則80%以上銷往廣東興寧,向梅縣輸出的不足20%;木頭的出口,基本上都是本地木材商販協助廣東龍川商人收購,銷往龍川市場。[5](P52-54)。

再次,在當時尋烏城鄉進口及商道通過貨物中,農產品也居主要地位。油、豆、米、雞、牛、豬等主要農產品是當時通過尋烏商道,挑往尋烏各地市場或是廣東梅縣等地發賣的 “大宗”。以茶油的進口為例,尋烏進口的茶油主要來自于興國等地,僅澄江圩每年進口的茶油價值即高達十五萬元左右。而牛的買賣,除了給尋烏當地政府帶來豐厚的抽稅收益之外,還使得原本無牛的尋烏縣城出現了“每月逢一”(即農歷的初一、十一、二十一開市)的“牛崗”,從而既解決了農業生產對耕牛的需要和市場對肉牛的需求,也帶來了尋烏年均至少132 800元的牛市生意。[5](P48-51)
概括上述內容,清末民初尋烏的農業生產,從要素的配置,到市場交換的地租博弈,再到農產品的流通,都處于市場交換和商品經濟的裹挾之中,從而也為農民于無處不在的市場當中多元兼業與打工經商奠定了必要基礎。
二、市場中的兼業及打工經商
清末民初的尋烏農村,因人地矛盾尖銳、地權分配不均,使得農民難以停留在土地等傳統農業生產空間謀生;再加上近代潮汕地區開埠及商品經濟勃興的刺激,便使得家庭小農戶在勤力農耕求取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時,積極探索出了外向型工商兼業,努力打工經商的謀生路徑,從而進一步拓展了自身的生產發展與生活空間,也不斷加深著其與市場的緊密聯系。
(一)兼業打工常態化
耙梳相關史料可見,在清末民初尋烏貧困小農所從事形態多樣的兼業活動當中,奔忙于傳統商道和圩場充當挑米、挑鹽、挑豆、挑油、挑雜貨等的腳夫苦力是農村青壯年強勞動力進行兼業的最普遍方式;一根扁擔、兩條繩索或兩個籮筐即是他們謀生的重要工具。在水、陸運輸多靠“活人的肩胛”的清末民初,農閑之際的貧苦農民紛紛受雇于各類雇主,從事挑運、搬運等工作,構成了當時奔忙于贛閩邊省際商道“苦力”中的主體。因而,在當時的尋烏城鄉縱橫數百公里的繁忙省際商道上,與南來北往的貨流、物流緊緊相隨的,便多是兼業討生活的貧苦農民們。他們絕大多數是出賣勞動力,幫助老板挑運商品(米、鹽、油、豆、雜貨,也包括活的牲畜)南來北往,或是做排夫、船工、搬運工等賺取腳力錢。
盡管確切的農民兼業數據無從統計,但從文獻的相應記載中我們并不難窺測到清末民初尋烏農民兼業大軍之浩蕩。毛澤東便估算指出,僅是通過尋烏商道的挑腳夫數,自安遠挑雞鴨等至梅縣發賣而途經尋烏商道的日均100人以上,從石城、瑞金挑米至梅縣的日均300余人[5](P48-49);在尋烏羅塘至福建武平下壩之間,以及連通廣東興寧、平遠與尋烏篁鄉的商道上,兼業奔忙的各類腳夫苦力們更是 “如同螞蟻牽線”[12](P2-7),不絕于途。而據我們對包括尋烏在內的贛閩邊區的反復調研,受訪的老人(出身農民家庭者)幾乎都做過挑夫苦力,他們多同時兼營小額的油鹽、米鹽或是日用雜貨等的販賣小生意,僅少數人是專門替別人挑擔的挑腳夫。
盡管貧困小農充當“挑夫苦力”奔忙于省際商道辛苦異常,甚至還有“性命之憂”[13](P94),但作為其發展外向型兼業及尋求生活補添的重要方式,如是選擇既豐富了農民們的生產發展路徑,也使得貧困小農的身影得以多元活躍于當年尋烏城鄉的市場網絡當中。
此外,在農忙時節和農閑之際,受雇于各類雇主的短工或零工從事的多種打工行為,都是一種市場交換的兼業,也是農民適應市場需求常態化兼業的重要體現。如貧民多在農忙時節幫助地主從事犁地、收割等工作,農閑季節則主要通過幫地主摘木梓(茶子),幫助地主富農做房屋、冬翻土地以及處理婚喪嫁娶等急情大事的方式打短工或零工,兼取家庭農業收獲之外的收入以補家用。據調查,兼業等雜收占到了貧農家庭收入的1/3。[5](P170)
(二)家庭手工業的延續發展
由于毛澤東當年的調研對于尋烏城鄉的商業狀況格外關注,因而其《尋烏調查》文本對于尋烏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及其與城鄉商品市場的繁榮也有著較為全面的揭示。
其一,手工產品充斥尋烏城鄉市場。例如,尋烏城的木器店便向城鄉居民供應著多種生活用具。常見的有臺、凳、椅、桌、床鋪、腳盆、招牌等生活用具,以及學校使用的黑板、課桌椅等木器。再如,工農貧民要使用到的便板子、提桶、水桶、飯甑、菜板等也多是從“插花”圩期的圩場上購買。[5](P83-84)也正是因為如此,當年尋烏貧困小農向家庭手工業的拓展,在為其通過家庭手工業品帶來一定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當年尋烏城鄉市場商品的種類,滿足了民眾生產生活的多樣化需求,從而有力地助推了當年尋烏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其二,尋烏城鄉手工業者人數眾多、行業分布廣泛。在尋烏城2700余人口中,手工業者(包含手工工人、手工業主和商店店員在內)便多達297人,比例高達11%。行業分布則是遍及縫紉店、黃煙店、酒店、傘店、爆竹店、理發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飾店、洋鐵店、修鐘表店、屠坊店等;而在農村地區,農事閑暇時的農民也能兼做各類手工產品 (各種圓木和竹器),如飯甑、鍋蓋、桶子、水勺、腳盆、尿盆、竹椅子、簸箕、米篩、竹籃子等,有些農民甚至還能做臺、凳、椅、桌等技藝要求更高的手工品。[5](P99、P170)
其三,家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與手工業品的更新。梳理《尋烏調查》及相關史料可見,在近代商品經濟浪潮沖擊下,尋烏傳統家庭手工業及其產品除了部分破敗之外,還展現出與時俱進、發展更新的一面。例如,裁縫店做衣服,1920年前一概采用手工制作,十年之后變為“用機器的13家,手工僅3家”;衣服的式樣,則在短短的3年(1920—1923年)之內,就由興“破胸、方角、大邊的上海裝”轉為流行“七扣四袋身很長的廣州裝”了。再如,傘店制作洋布傘,木器店采用進步樣范制作木器,“乃社會需要的”打洋鐵店從無到有[5](P79-93),既說明了社會經濟發展與民眾生產生活的實際需求,也體現了家庭手工業及其產品在繼承原有技藝和樣式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更新與進步。
需要看到的是,作為城鄉商品(市場)經濟繁榮重要標志的手工業的發展,既與農民中的強勞動力兼做挑夫、苦力相輔相成合理利用了小農戶家庭的剩余勞動力資源,也為他們實現多元兼業、打工經商,以及推動城鄉商品經濟的繁榮產生了積極影響,從而也將家庭小農戶與商品市場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三)投身商海闖江湖
清末民初尋烏城鄉商品經濟的勃興,有效刺激了市場對于各類商品的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為家庭小農戶從事販賣小生意、投身商海奠定了必要基礎,從而助其不斷豐富多層次謀生致富的選擇。
首先,走村串戶“敲糖子賣”等,從事較低層次商業活動,為尋烏底層農民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便對當年尋烏農民以此種方式參與市場競爭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具體例證,一是興寧人羅義成,本是窮苦農民,早年就來到尋烏縣城及四廂“敲糖子賣”,并由此發財致富,最終累積了千元資本,在尋烏城穩穩當當做起了老板;另一是當時尋烏唯一“現存舉人”——古鹿蘋(雇農之子),小時候因家庭窮沒飯吃,便時常提個小籃子走村串戶賣小口(糖子、荸薺、咸蘿卜等)以換取微薄收入。[5](P63、P163)
其次,依據市場需求兼營農副產品小生意,是清末民初尋烏城鄉農民貼補家用及參與商品經濟的重要表現之一。在當年遍布尋烏各地農村形態各異的圩場中,農民多會依據自身家庭勞動力狀況,順應市場需求變化靈活從事各類小生意:其一,農民將平日節省下來的米加工成各類“米果”,在逢年過節之際,尤其是“會景”(迎故事或打蘸,均為客家傳統習俗)的時候,賣“板子”(即米果,有軟板子、鐵練板、鐵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魚子板、苧葉板、番薯板、印子板等多種)的農民便會來回穿梭于城鄉市場之間;其二,有糧食剩余的農民,在農業生產青黃不接、米價高漲之際,將米挑至市場發賣以賺取高額季節性差價;其三,缺乏本錢做小買賣者,則主要是上山砍柴火、種植各類小菜(芥菜、芹菜、藠頭、苦瓜等)或蓄養雞鴨等挑至市場發賣;其四,尋烏各地按照農歷“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開市的“插花”圩期,因“日日有圩、天天有市”而使得農民能夠隨時入市。《尋烏調查》所提及的潘登記、何祥盛、劉恒泰、范老四等水貨攤子,“并沒有開張門面的店”,而是一四七圩期在縣城擺攤經營,三六九圩期赴吉潭設攤趕圩。[5](P77-95)此外,在尋烏各地農村社區,還活躍著眾多半營生意半營農業的小店鋪。如《吉潭鎮志》便記載,清末民國時期,該鎮人口密集的村莊有多達上十家這樣的小店。這些小店主要面向本村民眾,本錢僅需十余個銀圓和一間小房子,主要售賣香紙、蠟燭、鞭炮、油鹽糕點等,這樣既可賺錢貼補家用,又方便了鄰里。[14]
再次,強勞動力農民在兼業做苦力的同時,從事長途販運兼營小生意,既豐富了其維生的手段,也助其投身商海。因自身資本的缺乏,當年贛閩邊地區強勞動力農民兼業主要是出賣苦力替商家或店鋪挑運貨物,或是在石排下、澄江、尋烏城、羅塘等上下貨物的地方搬運物資。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挑運辛勞后,他們或多或少累積了一定的“血汗錢”。當這些錢被兼業農民用來販賣食鹽、布匹和土特產等商品挑往尋烏城鄉自行發賣時,便轉化成了商業資本,既能給他們帶來不小的升值利潤,也使得兼業農民進一步地與商品經濟活動捆在了一起。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所特別提及的,水貨雜貨店店主張均益,最初即由做挑夫苦力累積資本,而后借助于五六年來不辭辛勞地幫尋烏城商人挑米、香菇等商品去梅縣,轉而自己販賣一些布匹、咸魚、鹽以及雜貨等商品回尋烏城發賣的方式進一步增殖資本,最后才在尋烏城開設起店鋪經營水貨、雜貨生意。[5](P77)
最后,成為商家商戶,專事工商業經營或以此維生。梳理《尋烏調查》及相關地方志史料可見,農民在累積或借貸到了一定資本之后,基于自身已經或即將脫離農業生產耕作的現實,他們多會在城鄉市場或墟鎮設攤開鋪,成為商家商戶,這既為他們的生產發展拓展了維生的空間,也在事實上成了當年尋烏城鄉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尋烏調查》文本所列舉的雜貨店主羅義成、藥材店主王普泰、伙店店主劉步權,就是此方面的代表。[5](P63、P78)
此外,清末民初尋烏地富階層的商業性質表現尤為突出。他們本身即是由農民力作致富或經營小商業致富上升而來,在實現自身經濟社會狀況上升流變之后,他們中有的堅守著以原有耕種土地求生存的傳統維生選擇,也有的加工米子發賣或放債給貧苦農民,還有的積極順應商品經濟發展潮流,競相逐利于“獲利更為豐厚”的工商經濟大潮。即便是當年已經成為尋烏全縣最大地主的潘明徵,在發家之初,僅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區區80余石(20畝)谷田,與一般中農并無本質區別。[15]其能實現自身經濟社會狀況的巨變,便是在堅持力農致富的同時,順應商品經濟潮流,靈活借助于市場網絡的延伸及其所提供的諸多發家致富機遇,廣泛聚集社會財富,從而不斷躋身農、工、商、學等行業,最終也得以成就傳奇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貧困小農兼業及打工經商的初衷在于“添補”生活所需,但上述行為的發生和完成,不僅滿足和保障了他們的基本維生需求,也在事實上加深了其農業生產、日常生活等與市場的緊密聯系,從而既使家庭小農戶的生產發展處于市場經濟的緊緊包裹之中,也因其向上發展而為現代城市的發展孕育了必要的工商資本。
三、日常生活與市場密不可分
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廣大農民時常遭遇的“禾頭根下毛飯吃”困境,以及近代商品經濟勃興刺激下其多元兼業及打工經商的外向型發展路徑,造成農民日常生活所需對于商品市場的依賴日深。
(一)日常吃穿通過市場調劑
聚焦清末民初尋烏城鄉大小市場上琳瑯滿目的商品,以及農民從市場上主要購買的鹽、米、油、豆腐、衣飾品等消費品可見,不僅“遠道而來”的各類洋貨需靠市場供應,而且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品也主要靠市場調劑。
例如,尋烏本地不出產的食鹽是農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也是當年尋烏城鄉市場最重要的商品。因此,僅有2700余人的小小尋烏縣城,卻有著“匯通”、“新發昌”、“韓祥盛”、“周裕昌”和“萬豐興”等五家鹽店。據毛澤東調查估算,這幾家鹽店生意做得多的可年收入大洋兩萬余元,少的也有六七千元的收入,五家賣鹽生意合計年收入十萬元左右。[5](P58)再如,盡管大米在清末民初尋烏對外出口農產品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意味米生意在尋烏城鄉市場的“失寵”。《尋烏調查》便顯示出,農業生產力水平較落后的時期,無地少地農民有限的農地收獲在交租、還債之后,往往會面臨“禾頭根下毛飯吃”的困境。換言之,當年尋烏城鄉人口眾多的無地貧民,在多元兼業及打工經商等賺取生活來源之后,也需從市場上購買或借貸谷米,這也正是當年尋烏農民從業選擇與別的地方不盡相同,以及大米成為市場主要商品之一的重要原因所在。
此外,當時尋烏農民通過市場購買各類衣飾物品,也體現了其日常生活與市場的緊密聯系。尋烏城鄉市場上品種齊全、色彩豐富的土布、竹布、竹紗、綢緞、呢絨、夏布等,是民眾衣料的主要來源。產自杭州的綢緞中的華絲葛、紡綢等,更是受到了城鄉婦女的青睞而變成了“每個女人都有”的頭帕。[5](P62)
(二)貧困小農仰仗市場借貸
縱觀清末民初尋烏農民的生活境況,前述諸多限制因素導致他們的生活時常遭遇困境,特別是進入民國之后贛閩粵邊區的長期戰亂使得農民艱難摸索出的外向型兼業道路被堵塞,許多貧民在遭遇災荒、婚喪嫁娶等大事急情,甚至于應對最起碼的日常生活所需,都不得不仰仗市場機制下的借貸來解決。
具體而言,一般年景,貧民承租地主土地所得農地收獲盡管相對有限,還要受到地租、債務等的分割,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仍能有限度地滿足貧民短時間內的基本生存需求。這樣,貧民只有在農歷三月要蒔田之際,或是農歷四五月青黃不接時節,抑或是過年過節,才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向公堂及地主富農借谷 (米)或借錢買谷(米);但在非正常年景,即農業生產遭遇災荒,或是貧民家庭遭遇婚喪嫁娶等大事急情之時,貧民維生就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宗族公堂或地富階層,通過市場機制尋求錢物等方面的借貸救助。至于鹽、食油、谷(米)以及農業生產工具犁、耙等實物的借貸,不僅本身多是商品或依賴市場供給,而且其借貸利息的計算和償還都是依據市場行情或利率進行的。
盡管上述借貸行為可能未必完全是由市場主導,但從其借貸的發生到完成,無不浸潤著市場因素的影響,且其借貸利息的高低時刻受到市場的影響并隨其變化而上下波動。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實已對農民的生活空間形成了無孔不入的態勢,貧困小農需要仰仗市場借貸賴以維生。
(三)豐富生活依賴市場取得
在談及清初尋烏民性、風俗之時,當地文獻多記載:“(吾邑)人民向稱淳樸,勤儉是其本能,耐勞實出天性。”[16](邑俗)“布袍蔬食,不艷華麗;士敦操,尚惜廉恥;民力稼穡,女勤紡績,燕(宴)會婚喪儉約,有唐魏之風。”然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尋烏文獻卻多稱當地風俗“(近今)稍尚侈靡,嗤樸素”[17](卷二《風俗》)。具體到毛澤東所調研的清末民初尋烏農村,即便是境況一般的農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追求豐富多彩的生活:當時的尋烏城鄉,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與富,一律頭上和手上戴著金銀等裝飾物,即便是再窮的女子,也都頭發上插著銀簪子,戴著銀耳環;“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則必定有手釧和戒指。如是風尚,也使得小小的尋烏縣城卻同時經營有七家首飾店。在社會用傘方面,凡屬“后生家”和“嫩婦女子”,不論工農商學何種出身,差不多一概都撐洋傘,而不再喜歡原來用的紙傘了。[5](P92、P82)
考究上述尋烏社會風俗及農民生活變化之原因不難發現,19世紀中期中國東南沿海的開埠,以及沿著尋烏城鄉商道不斷涌入的大量物美價廉的近代工業品充實了尋烏城鄉商品市場,從而較大地豐富和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是其重要誘因。盡管當年尋烏農村的一般農民基本維生都顯艱難,日常生活也仍承襲著儉樸的傳統,但隨著城鄉市場商品的不斷充裕,農民生活所需對于市場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其日常生活也正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而漸趨豐富多彩,這也進一步說明了農民日常生活與商品市場的密不可分。
總之,與前述貧弱小農發展農業生產、兼業打工等與市場聯系密切并無二致,清末民初尋烏家庭小農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始終浸潤著商品(市場)經濟的深刻影響。
四、家庭小農戶:尋烏商品經濟的“活水源頭”
清末民初時期,包括尋烏在內的贛閩粵三邊農村普遍面臨著人多地少的矛盾,深處山區的尋烏農戶,更是無法僅靠土地產出維持生活。但從前文所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尋烏的家庭農戶表現出了吃苦耐勞、勤儉自勵、發家致富的優點,他們本身就具有市場基因;加上潮汕開埠后對農戶經濟意識的影響,使得尋烏的家庭農戶在生產、生活等各方面都與商品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并且推動了尋烏境內外商道及市場的構建。在當時,就尋烏內部市場聯系而言,吉潭、牛斗光等幾大重要市場,以及遍布尋烏城鄉的24個主要農村圩場[18],將尋烏全境串聯成了一張彼此相連的大網;就其與外界聯系來看,位居重要商貿孔道地位的尋烏城鄉在事實上勾連著贛閩粵三省的省際商貿,南下廣東梅縣、福建武平,北上筠門嶺、瑞金等地的貨物客流多需在尋烏境內中轉或需要借助尋烏商道通過。正是在這縱橫交錯的傳統商道和星羅棋布的墟鎮所架構與串聯起來的巨大境內外市場網絡當中,出于求取最基本生存發展保障的本能需求,被視為亟待“陽光”與“雨露”滋潤的“馬鈴薯”們[19](P693),正以此起彼伏的身影、前仆后繼地為著美好幸福生活揮汗灑淚,從而在其身影活躍市場網絡的同時,也有力助推了當年尋烏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前行。這也造就了《尋烏調查》中所展現的尋烏(尤其是縣城、吉潭、澄江等地)商品經濟的繁榮景象,換言之,即家庭小農戶是當時尋烏商品經濟的“活水源頭”。
清末民初尋烏農村的個案充分表明,家庭小農戶經濟不僅不會阻礙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且本來就是商品經濟的“活水源頭”與創造者;同時,立足發財致富的家庭農戶經濟,其發展也須臾離不開商品經濟。以墟鎮與商道及其向外延伸的市場平臺,家庭農戶經濟與商品經濟形成多向互動,兩者高度契合,融為一體。顯然,將家庭小農戶經濟“靜止為”阻礙商品(市場)經濟發展的“小農經濟”或“自然經濟”的傳統觀點,不僅錯謬百出,而且也割斷了家庭小農戶與商品經濟“須臾難離”的內在聯系。
[1]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溫銳.理想·歷史·現實:毛澤東與中國農村經濟之變革[M].太原:山西高校出版社,1995.
[3]趙岡.重新評價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1).
[4]溫銳,游海華.勞動力的流動與農村社會經濟變遷:20世紀贛閩粵三邊地區實證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5]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溫銳.清末民初贛閩粵邊區土地租佃制度與農村社會經濟[J].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4).
[7]尋烏縣志編纂委員會.尋烏縣志[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
[8]陳榮華,何友良.中央蘇區史略[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
[9]楊麗瓊,溫銳,賴晨.蘇區革命前后贛南閩西地租率再認識[J].古今農業,2009,(2).
[10]尋烏縣立中學基金會管理委員會賃耕字契1—6號[A].民國檔案全宗號1[Z].尋烏:尋烏檔案館,手抄本.
[11]楊彥杰.長汀縣的宗族經濟和民俗[M].香港:國際客家學會,1996.
[12]武平文史資料(第5輯)[M].武平:政協福建省武平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1985,(5).
[13]Lillie Snowden Bousfield.Sun-Wu Stories.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2.
[14]吉潭鎮志[Z].尋烏:尋烏縣縣志辦,手抄本電子版.
[15]潘作體.一個文盲農民創業發富譽揚三省邊區的傳奇[Z].未刊稿電子版,1999.
[16]謝竹銘.尋鄔鄉土志[M].民國版(電子版).
[17](清)王衍曾,古有輝.長寧縣志[M].1907,活字本(電子版).
[18]尋烏文史資料(第3輯)[M].尋烏:政協尋烏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王立霞】
K207
A
1004-518X(2016)05-0123-0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家庭農場發展機制優化研究”(13BJY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