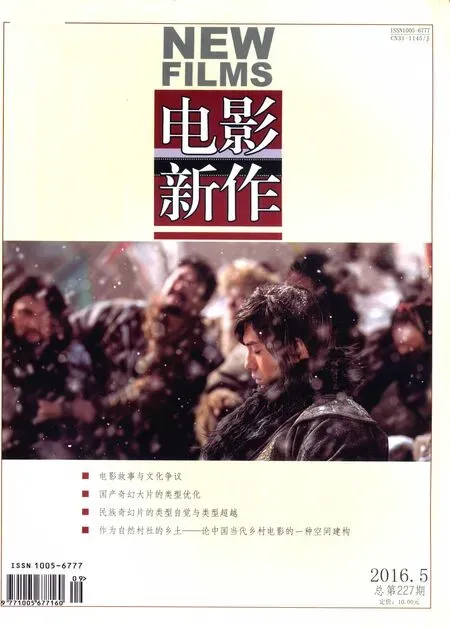從“外國式”到“中國的”
——郁達夫的觀影行為與電影認知
侯 凱
從“外國式”到“中國的”
——郁達夫的觀影行為與電影認知
侯 凱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郁達夫曾多次光顧影院。從他所留日記的記載中,可以梳理和呈現其作為一個影迷的足跡,并從中窺見其對影院與影片選擇的傾向和喜好。郁達夫亦曾介入電影批評領域,著文指點當時中國電影存在的問題。既對電影的本體有所觸及,又能窺見電影的外在影響。對于電影的認知以及中國電影的批評,顯示出其富有創見性的思維和前瞻性的視野。
郁達夫 影迷 中國電影 民族性
郁達夫,不僅是一位蜚聲文壇的作家,而且在平時還是一個時常光顧影院的影迷。他不僅長期流連在聲光電色之中,而且亦曾以清醒理性的姿態介入到電影批評的領域。與郁達夫關系親近的魯迅,同樣也是一個影迷,也曾參與到電影批評之中。魯迅曾言,“我的娛樂只有看電影”。①郁達夫又何嘗不是呢?②
郁達夫在對電影的觀看及認知方面,融合娛樂體驗、藝術感悟和社會思索于一體。既對電影的本體有所觸及,又能窺見電影的外在影響。對于電影的認知以及中國電影的批評,顯示出其富有創見性的思維和前瞻性的視野。對這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而言,這不應當是一個被簡單忽略的問題。
一、日記中的影迷身份與觀影行為
對郁達夫而言,日記是一種文學創作,“日記體”是散文作品里“最便當的一種體裁”。③所以,郁達夫將自己寫作的日記拿來發表和出版,在當時,可算是異于尋常。從這些日記來看,郁達夫的“日記文學”所涉時間并非持續,這與相對完整的魯迅日記有所差別。④在郁達夫日記中,1926年底至1928年2月是郁達夫載有觀影記錄的時間段,在此期間,郁達夫觀看電影次數共25次。其中,以1927年的觀影次數為最多,共21次,而這也是郁達夫書寫日記數量最多的一年。在這段時間,郁達夫長期居住在上海,有閑暇時間,有穩定稿酬,也有觀影條件。郁達夫可以通過選擇觀看電影這一形式,在上海這個國際化的摩登都市來達到娛樂和消遣的目的,獲得現代性的感官體驗。甚至可以說,同寫作一樣,郁達夫希望借助觀看電影來宣泄內心的壓抑與苦悶。當然,觀看電影這一行為,再深入聯系的話,則應當是與郁達夫的“創造社”努力倡導的新文藝運動的思想觀念相吻合,電影這一新興并且走向新潮的事物,本身即是注入文藝的新鮮血液,自然有助于新文藝的創作與發展。
觀影次數的統計僅是基于已經出版成書的郁達夫日記而言的,這并非意味著郁達夫在其他時期就沒有觀影經驗或失去了觀影興趣。有三點原因可以佐證:其一,正如前面所言,郁達夫將自己寫作的日記視為一種“日記文學”,既然如此,文學的寫作無法將生活原本模樣無一疏漏地記錄下來,某些事情或某個時間會被郁達夫有意過濾而不在文中提及。而且,郁達夫的日記有時并非是及時記載,這樣來看,有所遺忘也是在所難免;其二,郁達夫日記中未能涉及的年份中,其實也應當有許多觀影的經歷。比如在1926年12月2日,郁達夫觀看了一部外國影片,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看此影片,這是第二回了,第一回系在東京看的,已經成了四五年前的舊事”。⑤由此可以推測,郁達夫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曾看過不少電影了。
另外一個原因,便是人生際遇的多變所造成的遷徙流動,影響了郁達夫觀影的連續與穩定。在1928年3月6日,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晚上雨很大,想去看電影不成功,以后當不再出去看電影了,因為太費時間。”至此以后,郁達夫日記中果真未再出現觀看電影的相關文字。將原因歸咎于“太費時間”,應該可以理解為郁達夫當時的感性之話,而從此后的日記中,似乎可以窺見另有緣故。郁達夫在1928年4月與王映霞結婚之后,因為家庭經濟壓力,前往外地如安徽大學等擔任教職,為生計而疲于奔波,不再像之前那樣可以長時間居住在上海,而外地影業不甚發達,遠不如在上海觀影方便。在1930年3月至6月,郁達夫經診斷患有痔漏,疼痛難忍,無法正常寫作,更遑論外出娛樂。此外,郁達夫還曾前往福建擔任接近兩年的省政府參議一職。以至再后來,郁達夫去往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等報紙的文藝副刊。郁達夫多次的跨地奔波與忙碌營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難以穩定獲取觀影娛樂的一個因素。但是,即便在旅居海外的1941年7月,郁達夫還曾發表過一篇評價抗戰“大后方”地區制作的影片《火的洗禮》的短文。⑥由此可以看出,郁達夫還是繼續保持著對電影的關注和熱情。

郁達夫觀影統計表(1926—1928)
從根據郁達夫日記整理出的觀影表中可以發現,郁達夫去影院觀看的無一例外的都是外國片。我們揣測出其中的緣由,但是郁達夫的行為本身可能已經代表了一種立場,即國產電影存在的諸多問題,難以引發自己的觀影興趣。在這點方面,郁達夫與魯迅的行為也是很相似的,許廣平在《魯迅先生的娛樂》一文中憶述:“國產影片,在廣州看過《詩人挖目記》,使他幾乎不能終場而去。那時的國產片子,的確還幼稚,保持著不少文明戲作風,難以和歐美片競爭,實在也難得合意的選材。”⑦而且,郁達夫喜好選擇觀看那些根據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按照他的朋友趙景深所言:“達夫喜歡文學,因此,也喜歡看文學作品編成的電影,這與我有同嗜。我們只要看他的達夫日記集中屢載看文藝電影的記錄,便可相信。為了這種癖好,甚至連極小的戲院也要設法尋覓著進去觀光的。有一次我到武昌路的武昌大戲院(這戲院早已停業了)里去看賈克珂根主演的《賊史》,原作者是英國大小說家狄更司,湊巧就遇見達夫和他的映霞坐在后排。”⑧
另外,可以看出,郁達夫在影院的選擇方面,光顧次數最多的當屬北京大戲院。北京大戲院位于貴州路,從所處地理位置來看,影院與郁達夫的創造社出版部的地址(北四川路麥拿里41號)比較靠近,這應當是郁達夫優先選擇的理由之一。而且,北京大戲院在1926年11月19日才剛開業經營,對于初到上海的郁達夫而言,新戲院較之附近的其他影院,便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新鮮性和吸引力。而郁達夫曾經光顧的百星大戲院(福生路)、卡爾登大戲院(黃河路)、夏令配克影戲院(靜安寺路)、東華電影院(霞飛路)等,其實也都是位于郁達夫生活工作的周邊區域。
二、電影的辯證性認知與前瞻性視野
郁達夫不僅喜歡觀看電影,還曾專門著文,認真關注和深度思考過這個新興藝術的未來發展態勢。與其文學創作相比而言,郁達夫有關電影的文字實際并不多,但如果因此而忽視這些文字的存在,那將會是一個損失。雖然郁達夫自謙“關于電影的知識不多”,所寫的“本來是門外漢的鄙人”的“七扯八拉”,⑨但這些文字顯現出了他的睿智、深邃與獨特,是他留給后人的寶貴文化財富。1927年,郁達夫曾在《銀星》雜志第12期和第13期連續兩次發表電影評論文章——《電影與文藝》《如何的救度中國的電影》。其中,前文寫于1927年7月11日,后文作于1927年9月20日。細讀兩篇文章的內容,不乏頗有前瞻性與指引性的真知灼見。⑩
單從《電影與文藝》這篇文章的名字來看,郁達夫所要闡述的主要內容即可窺見。作為擅長書寫情感的作家,郁達夫將其細膩的筆觸投注到電影,卻不止于情感層面的評價,而是散發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彰顯出了一種帶有學術探究的意味。
在這篇文章中,郁達夫首先便對作為一種新興文藝的電影進行了一番詩意化的贊美。郁達夫說:“20世紀文化的結晶,可以在冰淇淋和電影上求之。”“同冰淇淋一樣的集成眾美,使無產者以低廉的價格,在最短的時期里,得享受到無上的滿足的,是近來很為一般都會住民所稱道的電影。”可以說,這番話語的筆調就如同郁達夫的散文風格一樣,恣肆坦誠而熱烈真摯。從中可以看到郁達夫想要闡明的觀點:電影,既是年輕的藝術,又是大眾的藝術。所謂“年輕”,在于其為“20世紀文化的結晶”;所謂“大眾”,則在于“使無產者以低廉的價格”而“為一般都會住民所稱道”。同時,他將“電影”比作顏色柔美香氣芳醇的冰淇淋,能夠“集成眾美”,并在“在最短的時期里”“享受到無上的滿足”。這個比喻實則與“軟性電影”論者所倡導的“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有某些相似之處,兩種論點都是基于娛樂功能的角度來認識電影。?當然,從提出觀點的時間來看,郁達夫的這篇文章發表于1924年,“軟性電影”論者則是在1933年提出的主張,相比而言,郁達夫要比他們早了十年,從中也可看出郁達夫對電影認識的前瞻性思維。當然,這里還要延伸一個問題,即“軟性電影”的主張曾遭到左翼電影人士的猛烈抨擊,而在語辭表達上頗為相近的郁達夫卻未有受到非議,此中緣由應當與兩者所處時代背景不同有關。“軟性電影”一派的主張出現在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如火如荼之時,自然與廣大民眾的現實意愿有所違逆,又因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使得“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的論戰升級,受到尖銳批判在所難免。而郁達夫寫就此文的時代,則是電影在中國的初創時期,遠不如20世紀30年代的興盛與成熟,更難以成為意識形態交鋒的焦點。
在對電影由衷贊美一番之后,郁達夫繼之引發出對電影未來發展前景的美好期待。他甚至斷言電影的將來“正是不可限量”。當然,對于電影的肯定以及未來的預期言語,絕非僅是停留在一腔熱情,而是建立在郁達夫對電影自身的特點認知基礎上的。他指出電影之所以能夠在短時期里得到長足進步的五種原因:“第一,電影是合成各種藝術長處的集大成者;第二,電影是藝術的立體化而且具有動的性質的;第三,電影是合乎近經濟的原則的;第四,電影的現實性和超現實性,都比旁的藝術易使觀眾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第五,電影是合乎近世的社會主義電影的理想的。”在此之后,郁達夫又對每個原因作了詳細的解釋。可以說,郁達夫從形式、內容、經濟、觀影心理以至更高層次的理想化期求(將電影作為宣傳教育的重要工具)等方面,指出了電影所具的諸種優勢,也因此,電影得以“進步之速”和“希望之大”。
郁達夫在對電影的特性給出了個人認知之后,進而指出電影這一新興藝術種類對文藝的重要功效。他認為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正因為有了諸多其他藝術所不具備的特長,才使得藝術變得更加鮮活靈動。這種鮮活靈動體現在:“使靜的文藝,能帶著動的意義,平面的文藝,能有具體的表現,貴族的文藝,能適合乎平民的口味”,“并且更可以使許多無意義的文藝變成了很有意義的東西。”實際上,在這里,郁達夫已經觸及電影在形式方面的特殊語言的使用了,也就是視聽語言。他在文中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說明:閱讀美國女作家的小說《Little Lord Fauntleroy》的時候,“所受的感動也只是平常,及到看了那張影片以后,覺得有許多地方,所得的印象竟要比讀書的時候深至數倍。”而讀Murger的小說《拉丁區的生活》里,“有幾段描寫,簡直使人討嫌,不愿意讀下去,而看到《LaBoheme》的時候,無論男女老幼或是懂藝術,還是不懂藝術的都不要緊,一氣看完之后,他們都不得不為糜糜流幾滴傷心之淚。”正是由于電影的特殊語言的介入,才使得原來的平面化的文字有了鮮活生動的直觀形象,對于普通觀眾而言,這要比簡單的閱讀文字所帶來的快感更具吸引力。
不僅如此,郁達夫還創新而辯證地指出文藝對電影的重要作用——“文藝也能同時促進電影的趣味一層,卻還不大有人提起過。”因為“大眾的藝術品,稍一不慎,就要流為填補低級趣味的消遣品,而失掉真正的藝術品的固有性質。在這里,郁達夫嚴肅地提出了電影需要提升內涵的創作品味問題。作為影迷,郁達夫觀看了許多外國電影,他認為“美國出品的許多平常的影片,都是千篇一律勉強地制造出來迎合這一種下劣趣味的。”而對文藝的注重,將會促使“這一種趣味轉向”,進而達成“提高一般趣味的目的”。
因此,針對尚在萌芽時代的中國影片制作趣味低劣以至肉麻的境況,郁達夫對處于這樣“一個危急的時期里”的中國導演和演員們提出了要求——“還有多讀真正文藝作品的必要”。他認為“要直接和文藝相接觸,把文藝的精靈全部吞下了肚之后,然后再來創作新影片”。而且這種“新影片”的“新”,重在于“一種精神上面,是在一種不失掉藝術的品位的氣質上面。”由此可以看出,郁達夫對電影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功能著意甚重,認為電影具有教化社會人心、提升大眾趣味、傳播藝術氣質的重要意義。這在當時電影認知觀念滯后的情勢下,郁達夫對電影的看法,是頗具超前意識的見地,也是實屬難能可貴的眼光。作為中國電影的奠基人與開創者之一的鄭正秋,曾經提出電影“得收改造觀念輿論之功,而逐漸走上藝術之路”“須含有改正社會之意義”的主張。?比較來看,郁達夫與鄭正秋的主張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彼此相通的。不過,從上述言論出處的時間上來看,郁達夫要比鄭正秋早了將近一年。由之可見,郁達夫在電影的認識上,顯示出了一種高人一籌的前瞻性視野。
三、民族性與創造性:建構“中國的”“新的”電影
郁達夫很少觀看中國電影,但他時刻關注著國產電影的發展情況。在《如何的救度中國的電影》一文中,郁達夫直陳當時國產電影所存在的諸多問題,同時提出個人的真知灼見,為中國電影的未來發展道路提出了富有創見性的意見。
首先對電影所具的“通俗性”特征予以肯定,他認為“電影成立的最大根據,就是要通俗”“因為太高深了,太專業化了,恐怕曲高和寡,銷不出去”。所以,電影“愈通俗愈好,愈能照一定的形式做出來愈好”。其實,郁達夫所謂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是與類型電影的創作觀念相通的,因為類型電影最顯著的一個特點便是在形式上的明晰可辨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可借鑒性,而這種特點恰恰是符合觀眾的心理期待,因而這種攝制策略往往能夠受到觀眾的歡迎,于是“形式”便重復性地在一系列影片中展示出來。
不過,郁達夫僅是在這篇文章中將此一筆帶過。很顯然,他的目的并非在此。從文中來看,他在舉出電影創作注重“通俗”與“形式”之后,列舉的是一個美國人所總結的電影創作20條“金科玉律”。但是郁達夫將此全部羅列出來,不止是對前述涉及的影片創作“形式”的一番佐證,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電影中同樣出現的這種“定則”是一種“不幸”。在此,郁達夫文章的真實意圖已經逐漸明晰顯現——“像這一種刻板的方法于影片的通俗化上,或者很有效力,但是我覺得導演家能少遵奉一點這些死規矩,也未始不可以使觀者得到一種清新的感覺。通俗化原不是病,不過刻板化卻是病。所以對于電影的通俗化,我不反對,但對于電影的刻板化,我卻大不贊成。”也就是說:中國電影需要通俗化,應當走類型化的路子,但不是簡單地將他國的方法拿來即用的“刻板化”。如果“死守了幾個通俗的原則,照列行去”,“那中國的電影,就一輩子也不會有出頭的日子”。在這里,顯示出郁達夫對中國電影現狀中所存在問題的思辨性認識。
既然能夠對中國影業狀況有著清醒的認識,那其中問題的解決方案,郁達夫心中自然有一些主張。為此,他提出了個人的建議,這應該是郁達夫此文闡述的重心所在。據此,筆者將其總結為兩點:
第一,擺脫“外國式”,彰顯民族性。郁達夫對此加以特別強調,“我們要極力地擺脫模仿外國式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中國電影出現。房子不必一定要洋房,坐車不必一定要坐汽車。妖婦淫婦不必個個是剪去頭發,畫黑眼圈的,就是鄉下的小腳婦人,穿了乾隆時代的衣服,天天在溪邊挑水的女人,她的惡毒淫艷,盡可以追過中西女塾的學生的。”對中國電影而言,一味地模仿他國電影而進行復制性的、雷同化的生產,無法熔鑄本國特有的民族文化內涵,是難以成為一個具備主體性的真正的中國電影而長期存在的。如今,中國電影的民族化問題依然是諸多學者參與討論的重要話題,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新世紀時期,中國電影界先后出現了兩次關于電影民族化問題的論爭熱潮,成為中國電影學術史上的一段重要事件。?而在中國電影的初創之期,郁達夫便已經明確關注到這個問題。雖然未能深入而詳細地展開說明,同時與后來的“民族化”問題討論時所處的歷史背景有所不同,但是如果從中國電影的理論話題討論的歷史中作一番檢視的話,郁達夫為中國電影“民族化”問題的討論所作出的開創性嘗試和積極性探析,其中包蘊的學術眼光和問題思維,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打破“死規則”,注重創造性。郁達夫在文章中指出:“只把幾個人面換一換的電影,我們不大愿意去看。我們所要求的,就是死規則的打破。我們要求有Originality的,有Creative spirit的東西。”這里觸及了中國電影的原創性問題,要打破規則的束縛,主張富有創造精神。
對于這種提議,郁達夫進一步作了解釋。他認為要建立“中國的”“新的”電影,這種電影“不是美國式的電影”,也不是“中國特有”的“古裝影片”,也不是“汽車會飛,電燈會說話的東西”。郁達夫對中國電影所要求的東西,實際上是“要Realistic同時又要Original的出品”。也就是說,既要注重真實性,又要具備創造性。雖然郁達夫沒有進一步提出具體的內容,但從其字里行間之中,可以體會出其主張的精神。
四、兩種向度的介入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郁達夫介入電影批評領域,雖然時間頗短,文章有限,但其中指出的問題,倒是超出同時代之人的眼光。在他的文章中,既對電影的本體屬性有所觸及,又能認識到電影的本地價值;既嘗試探討電影的功能作用,又強調民族電影的特殊意義。郁達夫嘗試從兩種向度介入電影的認識和評價,而從兩文寫作和發表的時間先后承接來看,這兩篇文章是存在著某種關聯的。
在《電影與文藝》一文中,郁達夫認識到電影于眾多藝術中的特有屬性,同時指出電影未來發展不可限量的巨大潛能,因為電影具有對受眾而言的特殊娛樂功能,并因其特有的影像語言而使得電影與其他文藝種類相比更具直觀性和趣味性,這使得電影可以作為一種教化的工具而存在。電影可以憑借自身創造出的有內涵和有素養的作品,達到提升普通民眾審美趣味的作用。而另外一篇文章《如何的救度中國的電影》,則重在思考電影之于中國的本土存在意義和發展道路,彰顯民族特色,主張創造精神。在電影傳入中國但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之時,窺見其未來發展前景的郁達夫,撰文呼吁電影的民族性和創造性,自然是對懷有深思熟慮的。
在20世紀20年代,雖然中國電影的創作還處于摸索階段,與之對應的是,相關的電影理論批評文章,多是零碎化和平面化的,也缺乏一定的邏輯性和深度性,但畢竟是體現出對電影的一定看法。而郁達夫所寫就的兩篇關于電影的文章,雖以外行人自謙,但通過兩種向度的嘗試性介入,由內及外,由洋轉中,文筆肆意而靈動,觀察獨到而深刻。與當時諸多遭遇創作癥結而不得解的內行之人相比而言,郁達夫的文章顯現出自己的遠見卓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郁達夫作為文人影迷,與周瘦鵑、包天笑等“鴛蝴”文人影迷還是有明顯區別的。這種區別在于,郁達夫對電影的認知以及介入電影的方式都明顯具有左翼文人的特點。30年代的左翼文人,除了郁達夫還有一大批,他們的電影批評極大地影響了電影創作,并催生許多思想進步的電影的產生,對中國電影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注釋】
①魯迅:《致歐陽山、草明信》,1936年3月18日,見于《魯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頁。
②研究“魯迅與電影”的相關論文和資料已經非常可觀,學者基本借鑒參考的是魯迅日記和魯迅寫過的幾篇與電影有關的文章。但是,專門研究“郁達夫與電影”的論文至今未有。本文研究所依據的資料也是郁達夫日記以及他曾經發表的幾篇與電影有關的文章。
③郁達夫:《日記文學》,《達夫日記集》,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版,轉自《郁達夫日記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頁。文中所涉日記內容,所依據的版本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郁達夫日記集》,以下不再專門加以標注。
④從1912年5月5日到1936年10月18日,除1932年2月因“一·二八”戰事爆發而失記幾天以及1936年6月因病重有20多天停頓外,魯迅每天都在寫日記。見于包子衍:《<魯迅日記>的發表與出版》,《魯迅研究文叢》(第四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頁。
⑤《郁達夫日記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頁。
⑥郁達夫:《有三點可取》,《星洲日報·每周影評》1941年7月13日,轉自《郁達夫文論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897頁。
⑦見于馬蹄疾輯錄:《許廣平憶魯迅》,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頁。
⑧趙景深:《文人剪影》,北新書局1936年版,第5頁。
⑨郁達夫:《如何的救度中國的電影》,《銀星》1927年第13期。
⑩本節引文都出自此篇文章,以下不多加注釋說明。
?黃嘉謨在《現代電影》1933年第6期上發表一篇名為《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的文章,“軟性電影”的說法由此而生。
?鄭正秋:《我所希望于觀眾者》,《明星特刊》第3期《上海一婦人》號,1925年7月27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
?張中全:《重讀新時期以來關于中國電影民族化的論爭》,《電影藝術》2005年第6期。
?關于左翼文人的電影批評,可參考薛峰:《論1910至1930年代“鴛鴦蝴蝶派”與“新感覺派”文人的電影批評》,上海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張曉飛:《1930年代中國左翼電影批評再解讀》,遼寧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侯凱,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