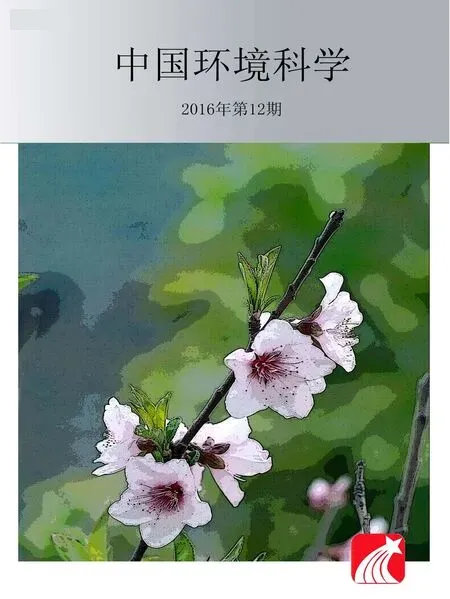洞庭湖浮游藻類功能群的組成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汪 星,李利強,鄭丙輝*,劉 琰,田 琪,王麗婧(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基準與風險評估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2;2.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國家環境保護飲用水水源地保護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12;3.國家環境保護洞庭湖科學觀測研究站,湖南 岳陽 1000;.洞庭湖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湖南 岳陽1000)
洞庭湖浮游藻類功能群的組成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汪 星1,2,3,李利強4,鄭丙輝1,2,3*,劉 琰1,2,田 琪4,王麗婧1,2,3(1.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基準與風險評估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12;2.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國家環境保護飲用水水源地保護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12;3.國家環境保護洞庭湖科學觀測研究站,湖南 岳陽 414000;4.洞庭湖生態環境監測中心,湖南 岳陽414000)
2013年3月、6月、9月及12月采集了洞庭湖11個斷面的浮游藻類,并對所采集的藻類進行了功能群劃分,結果顯示,洞庭湖的浮游藻類可以分為24個功能群:A、B、C、D、E、F、G、H1、J、LO、LM、M、MP、N、P、S1、SN、T、W1、W2、X1、X2、X3、Y,所反映的生境特征主要表現為對分層敏感、頻繁擾動且混合程度較高的渾濁型中-富營養型水體.不同時期調查的藻類優勢功能群存在明顯差異,其中,B(中營養水體、對分層敏感)、D(較渾濁的淺水水體)、J(混合型高富營養淺水水體)、MP(擾動頻繁的渾濁型淺水水體)、P(混合程度較高中富營養淺水水體)、Y(廣適性)在四次調查中的優勢度均>0.02,成為洞庭湖的絕對優勢功能群,洞庭湖藻類優勢功能群不同時期的演替規律為:3月MP+P+D+B經6月MP+J+P+D+B與9月MP+J+P+D+B+LO+Y轉變成12月MP+J+D+Y.CCA分析結果顯示,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受水環境因子影響較為明顯.整體上,T、pH值、DO、CODCr、NH3-N及TP是影響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優勢度;環境因子
同一類群中的不同種類可能具備相似的生態屬性,因此,生態學家們將具備相似生態屬性的生物體進行歸類,以此來簡化復雜的生態系統,并將該簡化后的生態群落定義為功能群[1].浮游藻類是一類極其多樣、多源的光合自養型原生動物或藍細菌,是食物鏈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的初級生產者[2],20世紀 70年代以來,功能群分類法在浮游藻類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且不斷被更新.截至目前,浮游藻類功能群的分類標準包含尺寸、形狀、生長策略、生態功能及生境特征等5個 方 面 .BSS(Biomass size spectrum)/NBS (Normalised Biomass Sizespectrum)、 TTSS (Traditional Taxonomic Size spectrum)以及PGS (Phytoplankton Geometric Shapes)法均以生物體的尺寸和形狀作為分類依據,這三種方法的優點在于不需要專業的分類學基礎且錯誤歸類的風險極低,缺點則是不能反映生物樣本的生態屬性以及所處生境的特征等[3-6].CSR(Competitive, Stress-tolerant and Ruderal strategists)法是 r/k (rete of increase/carrying capacity)法的衍生,主要反映藻類的生長屬性及策略,優點也是對分類學基礎要求不高,且錯誤歸類的風險較低,受到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并一直沿用至今[7].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FG(Functional Groups)法的提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方法能反映藻類的棲息地屬性、對環境的耐受能力以及水體的營養等級等各個方面[8-10],近年來也成為我國湖泊研究者們使用最為廣泛的方法[11-16].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28°30′N~30°20′N、111°40′E~113°40′E),長江中游南岸,西南有湘、資、沅、澧“四水”入湖,北有長江的藕池、松滋、太平“三口”流入,湖水經北部的城陵磯與長江相通,是我國第二大淡水湖泊、國內最大淡水濕地以及國際重要濕地和珍稀候鳥越冬棲息地,亦是長江洄游和半洄游魚類的產卵場、索餌場,具有調蓄、滯洪、維持長江中游水域生態平衡及下游水資源戰略安全等多項生態服務功能.因長年的泥沙淤積和圍墾,洞庭湖被分割為東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現有天然湖面2 691km2,洪道1 307km2.在自然和人類活動的雙重作用下,100多年來,湖泊迅速萎縮,生物多樣性顯著下降,部分水域出現藍藻水華,水情和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在以往的研究中曾提出溶解氧和氮是影響洞庭湖藻類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17-18],但浮游藻類的生長繁殖及水華的產生也與生境、水文、水動力等條件有著潛在的聯系[15],因此,對洞庭湖浮游藻類生長、形態及生態功能等的演替規律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采用 FG法對洞庭湖浮游藻類功能群特征進行分析,并通過典范對應分析(CCA)明確影響浮游藻類功能群演替的主要環境因子,以期為洞庭湖的生態與水質監管提供理論依據和技術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采樣位點設置與采樣方法
本研究共設置11個采樣斷面,如圖1所示,監測時間為2013年3、6、9和12月.藻類樣品的采集使用國際標準的25號篩絹制成的小型浮游生物網,于水體自下向上垂直托取定量樣品,用 5%的甲醛溶液固定保存.另取表層水樣 2L,搖勻,一部分原水樣直接分裝于250ml磨口瓶,用于測定總磷、總氮、氨氮、生化需氧量等常規水質指標.
1.2 水樣測試方法
水樣的生化需氧量(BOD)、高錳酸鹽指數(CODMn)、化學需氧量(CODCr)、總氮(TN)、總磷(TP)、氨氮(NH3-N)以及糞大腸菌群(E.coli)的測定方法參照《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19].其中,稀釋與接種法測定 BOD,酸性高錳酸鉀法測定CODMn;重鉻酸鹽法測定 CODCr;堿性過硫酸鉀-紫外分光光度法測定 TN;鉬酸銨分光光度法測定TP;納氏試劑分光光度法測定NH3-N;多管發酵法測定E.coli.pH值、水溫(T)、溶解氧(DO)的測定采用便攜式 pH 計和水質多參數測定儀(YSI)現場直接測定(水面下0.5m);參照《中國淡水藻志》[20]對采集的樣品進行分類、鑒定,藻細胞生物量計算等采用顯微鏡法[21].

圖1 洞庭湖采樣斷面示意Fig.1 Sampling sections of Dongting Lake
1.3 數據分析
1.3.1 浮游藻類功能群分類及生物量計算 參照2002年Reynolds等[9]和2009年Padisák等[10]以浮游植物生理生長特征及其環境適應性機制為基礎,在浮游植物生長的C-R-S策略分類基礎上,對具有相同適應性特征、易于在相同生境條件下共存的浮游植物種類進行功能分組.浮游藻類功能群生物量指的是功能群的代表性藻種(屬)的細胞生物量之和,通過各代表性藻種(屬)的生物量相加得出.比如洞庭湖藻類功能群B的代表性藻種(屬)包括小環藻和冠盤藻,那么該功能群生物量則為小環藻和冠盤藻細胞生物量之和.
1.3.2 浮游藻類功能群優勢度分析 優勢度根據藻類功能群的出現頻率及豐度來確定,用優勢度來表示[22]:y=fi·Pi.式中:y為優勢度,fi為第i功能群的出現頻率,Pi為第 i功能群豐度占總藻類豐度的比例,當 y>0.02時,定為優勢功能群[23].選擇優勢度>0.02的浮游藻類功能群進行典范對應(CCA)分析.
1.3.3 環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 采用主成分分析(PCA)中的因子分析法[24],將各采樣斷面的環境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溶解氧為逆指標,故將其先進行倒數變換,然后在 SPSS13.0中完成數據標準化),為了使每個主成分的意義更加明確,采用 Varimax最大方差法對因子進行旋轉,按照特征值λ大于1的原則提取出3個主成分,選擇主成分的因子載荷量>0.7的環境因子進行CCA分析.所有的數據分析均在SPSS 13.0軟件下進行.
1.3.4 典范對應分析(CCA) 采用 Canoco for Windows 4.5 軟件對功能群數據和環境數據進行CCA分析.浮游藻類功能群矩陣經過 lg(x+1)轉換,環境因子數據除 pH值外全部進行lg(x+1)轉換[25].CCA分析結果用功能群—環境因子關系的雙序圖表示,圖中環境因子用帶有箭頭的線段表示,向量長短表示其在主軸中的作用,線段所處象限代表環境因子與排序軸間的正負關系.分析時,做出某一功能群與環境因子連線的垂直線,垂直線與環境因子連線相交點離箭頭越近,表示該種與該類生境因子的正相關性越大,處于另一端的則表示與該類環境因子具有的負相關性越大.
2 結果分析
2.1 浮游藻類豐度變化及功能群劃分
從不同時期藻類生物量的分布來看(圖 2),3月藻類的生物量變化范圍為 0.08~2.59mg/L,最大值出現在大小西湖(S11),而萬子湖(S5)的生物量最小,整體來看,浮游藻類生物量從大到小依次為東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6月、9月和12月浮游藻類的生物量變化范圍分別為0.05~0.89,0.07~1.76,0.02~2.41mg/L,最大值均出現在大小西湖(S11),而坡頭(S1)的生物量最小,整體來看,浮游藻類生物量從大到小依次為東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
對所檢出的浮游藻類進行功能分類,如表 1所示,洞庭湖的浮游藻類可以分為 24個功能群:A、B、C、D、E、F、G、H1、J、LO、LM、M、MP、N、P、S1、SN、T、W1、W2、X1、X2、X3、Y.

圖2 洞庭湖2013年浮游藻類生物量的時空變化Fig.2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of Dongting Lake in 2013

表1 洞庭湖浮游藻類功能群劃分Table 1 Algal function groups division in Dongting Lake

續表1
2.2 浮游藻類優勢功能群及其分布特征
從不同時期藻類功能群的優勢度來看(圖3),3月浮游藻類的優勢功能群為D、B、MP、P、J、Y、X1,6月為J、MP、B、Y、D、P,9月為J、Y、P、MP、LO、D、B、X2,12月為Y、D、J、MP、X2、B 、P、X1,其中,B、D、J、MP、P、Y在4次調查中的優勢度均>0.02,成為洞庭湖的絕對優勢功能群.本研究中浮游藻類功能群的時空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子分析均在上述優勢功能群中展開.
從不同時期藻的功能群組成來看(圖4),3月藻類功能群 MP、P、B、D在各采樣斷面均有分布,其中,B在南嘴(S3)、鹿角(S8)和洞庭湖出口(S10)均占據絕對優勢,D在大小西湖(S11)占據絕對優勢,整體來看,MP、P自西洞庭湖至東洞庭湖湖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而B、D則呈現逐漸升高的趨勢(除 S3外),值得注意的是,萬子湖(S4)以Y占據優勢,而MP、P、B、D等優勢類群所占比例較小.6月各采樣斷面的主要功能群由3月的MP+P+D+B轉變成MP+J+P+D+B,優勢功能類型較3月明顯增多,其中,MP、J分別在東洞庭湖(S9)和大小西湖(S11)占據絕對優勢,整體來看,西洞庭湖與南洞庭湖的藻類優勢功能群組成均衡度較高,而東洞庭湖則以MP、J成為絕對優勢群落.9月各采樣斷面的主要功能群由 6月的MP+J+P+D+B轉變成MP+J+P+D+B+LO+Y,其中,J、Y分別在大小西湖(S11)和洞庭湖出口(S10)占據絕對優勢,整體來看,MP、LO自西洞庭湖至東洞庭湖湖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J、Y則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P、D、B在各采樣斷面所占比例相對均衡.12月洞庭湖整體以Y占據絕對優勢,各采樣斷面的主要功能群由 9月的MP+J+P+D+ B+LO+Y轉變成MP+J+D+Y,整體來看,MP自西洞庭湖至東洞庭湖湖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而J則呈現相反的趨勢;D在南洞庭湖所占比例明顯高于西洞庭湖和東洞庭湖,而Y在西洞庭湖和東洞庭湖所占比例則明顯高于南洞庭湖.

圖3 洞庭湖不同季節浮游藻類功能群優勢度Fig.3 Dominance of algal function group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Dongting Lake

圖4 洞庭湖不同季節浮游藻類功能群組成Fig.4 Algal function groups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Dongting Lake
2.3 環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為了使每個主成分的意義更加明確,采用Varimax最大方差法對因子進行旋轉,按照特征值λ大于1的原則提取出3個主成分,如表2所示,3月、6月、9月和12月的主成分累計貢獻率分別達到81%、94.5%、78.5%及92.8%.該主成分分析所得指標的載荷超過 0.7的即為主要影響因子,3月的主要環境因子為T、pH值、DO、CODMn、CODCr、BOD、NH3-N、TP、E.coli,6月的主要環境因子為T、pH值、DO、CODMn、CODCr、BOD、NH3-N、TN、E.coli,9月的主要環境因子為T、pH值、DO、SD、CODMn、CODCr、NH3-N、TN、E.coli,12月的主要環境因子為 T、pH值、DO、CODMn、CODCr、BOD、NH3-N、TN、TP、E.coli.

表2 Varimax轉軸后的因子載荷量Table 2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2.4 浮游藻類優勢功能群與環境因子的相關 (CCA)分析


圖5 洞庭湖不同季節浮游藻類優勢功能群與主要環境因子的CCA分析Fig.5 CCA analysis of algal dominant function groups and principal environment factor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Dongting Lake
選取藻類優勢功能群與主要環境因子進行CCA分析,如圖5所示,環境因子第一、二軸間的相關系數為 0,表明分析結果可信[26].3月的分析結果顯示,Y與DO呈現強正相關; J與pH值呈現強正相關;整體來看,DO、pH是影響3月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6月的分析結果顯示,W2、X1與T正相關性顯著;J、B、P、MP、D與DO、CODCr均呈現強正相關;整體來看,T、DO及CODCr是影響6月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9月的分析結果顯示,J與pH呈現強正相關;P與 CODCr、DO呈現強正相關;整體來看,pH、CODCr及DO是影響9月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12月的分析結果顯示,P、X1均與 T呈現強正相關;J與 NH3-N呈現強正相關;D、Y、MP、X2均與TP呈現較強的正相關;整體來看,T、NH3-N、TP是影響12月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
3 討論
3.1 浮游藻類豐度變化及功能群劃分
通過對洞庭湖不同時期浮游藻類的調查顯示,該流域內藻類功能群存在明顯的時空差異.從優勢功能群的代表性種類來看,3月浮游藻類以硅藻占絕對優勢,其次是綠藻和藍藻,6月以綠藻與硅藻占絕對優勢,其次是藍藻和隱藻,9月為以綠藻占絕對優勢,其次是甲藻、隱藻,硅藻所占比例顯著減少,12月則轉變為甲藻和隱藻占優,其次是硅藻和綠藻.1999年李利強等[27]、2012年汪星等[17]的調查結果均顯示,洞庭湖以綠藻門與硅藻門占優,藍藻門次之,陳格君等[28]對另一長江的典型通江行湖泊鄱陽湖的調查結果也顯示,浮游藻類的組成以綠藻門占優,硅藻和藍藻門次之,均與本研究的結果保持一致.可見,近年來,盡管土地利用、水產養殖及種植業等人類活動的不斷增多,洞庭湖藻類功能群的組成并未發生明顯改變.
從優勢功能群的生境特征來看,3月西洞庭湖以B和MP占絕對優勢,特別地,南嘴(S3)的B所占比例超過80%,B與MP功能群的生境特征均為頻繁擾動渾濁型淺水水體,這與西洞庭湖的幾個采樣斷面實際情況相符,S1、S3分別屬于沅水和澧水的入湖監測斷面,上游的開江春水夾帶大量泥沙且流速較大,導致水體較為渾濁,同樣地,S2、S4也受益陽資水的來水影響,水體混合度較高;南洞庭湖的萬子湖(S5)與橫嶺湖(S6)斷面受入湖河流擾動較小,水體流動速率相對較緩,適宜生境為混合程度較高的中-富營養型水體的 P型藻類生長,這也與洞庭湖水體屬于中-輕度富營養狀態的報道一致[29-30].S7-S8、S9-S11分別受湘江與長江回水的作用,水體重回渾濁,適宜B、D及MP等功能群的生長.6月以MP和J在各采樣斷面的優勢較為明顯,受上游來水的影響,MP在坡頭、南嘴、鹿角、東洞庭湖及洞庭湖出口的比例仍占據優勢; J的適宜生境為混合型高富營養水體,其比例則呈現自西洞庭湖到東洞庭湖逐漸增加的趨勢,并在大小西湖達到最大;鐘振宇等[29]、周泓等[31]、王麗婧等[32]、Wang等[33]的研究結果均表明,洞庭湖的水體富營養化狀態依次為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東洞庭湖,且大小西湖水體的富營養化最為惡劣,這些均與本研究中藻類功能群的分布狀況相符.9月MP與J的分布狀況與6月的基本一致,但J的比例有所下降,而Y的比例則隨之增加,Y屬于廣適性中營養功能群且在萬子湖和洞庭湖出口占據絕對優勢,究其原因,可能是9月屬于豐水期,湖區上游來水量增大,對水體有一定的稀釋作用,導致整體營養狀態有所下降,廣適性功能群比例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大小西湖仍以 J占據絕對優勢,其富營養化狀態不容小視.12月MP在東洞庭湖的比例明顯小于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東洞庭湖在該時期受長江回水影響明顯減少;Y在各采樣斷面占據優勢明顯,可見該時期洞庭湖水體營養狀況良好,究其原因,可能是枯水期上游來水減少,進入湖區的污染物總量降低,加之湖區的自凈作用,湖區適應中營養和廣適性的藻類生長;另外,該時期J的變化趨勢仍與其他時期的保持一致,三個湖區的水體營養狀態高低次序保持不變.
3.2 浮游藻類功能群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
研究表明,pH、水溫、溶解氧、總氮、透明度、總磷、氨氮、生化需氧量以及化學需氧量均能成為影響浮游藻類群落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
[34-40],本研究結果顯示,水溫、pH、DO、CODCr、NH3-N及TP是影響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其中,水溫成為P、W2、X1等多個功能群分布的主要影響因素,雖然洞庭湖屬于北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但其在不同季節以及晝夜的水溫仍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水溫必然成為該區域藻類生長的限制因子,對寒區安邦河濕地[13]、北方的烏梁素海[15]、深水型金盆水庫[41]、貴州高原的阿哈水庫[14]與三板溪水庫[42]等湖庫的研究亦表明,水溫是該區域藻類功能群結構變化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可見水溫對湖泊藻類生長及結構演替的重要性.藻類適宜在偏堿性的水體中生長,可見 pH對藻類生長的重要性,本研究中,pH則成為適宜富營養水體生長的 J功能群的限制因子.藻類的生長除了光合作用,同時也需要氧氣來完成呼吸作用,因此,DO成為B、D、J、MP、P、Y分布的主要限制因素,已有研究表明,DO與藻類生長呈顯著正相關[43],作為典型的通江湖泊,鏡泊湖的浮游藻類也受到 DO的限制[34].CODCr通常作為反映點源污染的常規檢測指標,NH3-N、TP則是反映面源污染的兩項重要監測指標.南屏水庫、竹仙洞水庫[44]、北京海子水庫[45]的研究表明, 磷是浮游藻類功能群演替的主要驅動因子,本研究中,J、B、P、MP、D均受CODCr的限制,可見有機污染物對藻類生長的影響之深,同時,NH3-N、TP兩項營養鹽指標也分別與適應富營養水體生長的 J、X2呈現強的正相關;研究表明[18],洞庭湖浮游藻類的生長主要受到氮(尤其是氨態氮)的限制,添加氨氮能明顯促進浮游藻類生物量的增加.洞庭湖作為長江中下游通江型調蓄湖泊,承接“四水”和“三口”,受上游來水影響顯著,同時,湖區周邊的人為活動也對洞庭湖的水質狀況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整體來看,洞庭湖的污染主要來自于上游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湖區周邊造紙廠廢水、農業用肥以及湖區內漁民的生活污水與垃圾滲濾液等,其中工業廢水則是CODCr的主要來源,生活污水及農用肥料則是NH3-N與TP的主要貢獻者,故CODCr、NH3-N、TP能成為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的主要限制因子.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繼續穩步發展,人類活動會更加頻繁,洞庭湖的生態環境質量問題應引起有關部門重視.
4 結論
4.1 2013年對洞庭湖 11個采樣斷面所采集的浮游藻類的分類結果顯示,洞庭湖的浮游藻類可以分為24個功能群:A、B、C、D、E、F、G、H1、J、LO、LM、M、MP、N、P、S1、SN、T、W1、W2、X1、X2、X3、Y.
4.2 洞庭湖不同時期的藻類優勢功能群存在明顯差異,其中,B、D、J、MP、P、Y在4次調查中的優勢度均>0.02,成為洞庭湖的絕對優勢功能群;洞庭湖藻類優勢功能群不同季節的演替規律為:3月MP+P+D+B經6月MP+J+P+D+B與9月 MP+J+P+D+B+LO+Y 轉 變 成 12 月MP+J+D+Y.
4.3 CCA分析結果顯示,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受水環境因子影響較為明顯.整體上,T、pH值、DO、CODCr、NH3-N及TP是影響洞庭湖藻類功能群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
[1] Solbrig O T. Plant traits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their role in ecosystem function [M]//: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 (Eds E.D. Schulze & H.A. Mooney), 1993:97-116. Ecological Studies. Springer-Verlag, Berlin.
[2] Rousseaux C S, Gregg W W. Interannual variation in phytoplankton primary production at a global scale [J]. Remote Sensing, 2013,6(1):1-19.
[3] Platt T, Denman K. The structure of pelagic marine ecosystems [J]. Rapports et Proces Verbaux des Reunions, 1978,173:60-65.
[4] Kamenir Y, Dubinsky Z, Zohary T. Phytoplankton size structure stability in a meso-eutrophic subtropical lake [J]. Hydrobiologia, 2004,520(1-3):89-104.
[5] Kamenir Y, Dubinsky Z, Zohary T. The long-term patterns of phytoplankton taxonomic size-structure and their sensitivity to perturbation: A Lake Kinneret case study [J]. Aquatic Sciences, 2006,68(4):490-501.
[6] Stanca E, Cellamare M, Basset A. Geometric shape as a trait to study phytoplankton distributions in aquatic ecosystems [J]. Hydrobiologia, 2013,701:99-116.
[7] Stanca E, Cellamare M, Basset A. Geometric shape as a trait to study phytoplankton distributions in aquatic ecosystems [J]. Hydrobiologia, 2013,701(1):99-116.
[8] Reynolds C S. Phytoplankton assemblages and their periodicity in stratifying lake systems [J]. Holarctic Ecology, 1980,3(3):141-159.
[9] Reynolds C S, Huszar V, Kruk C, et al. Towards a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reshwater phytoplankton [J]. Journal of Plankton Research, 2002,24(5):417-428.
[10] Padisak J, Crossetti L O, Naselli-Flores L. Use and misu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hytoplankton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 critical review with updates [J]. Hydrobiologia, 2009,621(1): 1-19.
[11] 董 靜,李根保,宋立榮.撫仙湖,洱海,滇池浮游藻類功能群1960s以來演變特征 [J]. 湖泊科學, 2014,26(5):735-742.
[12] 陳曉江,楊 劼,杜桂森,等.海子水庫浮游植物功能群季節演替及其驅動因子 [J]. 水資源保護, 2015,31(6):122-127.
[13] 武安泉,郭 寧,覃雪波.寒區典型濕地浮游植物功能群季節變化及其與環境因子關系 [J]. 環境科學學報, 2015,35(5):1341-1349.
[14] 李 磊,李秋華,焦樹林,等.阿哈水庫浮游植物功能群時空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子分析 [J]. 環境科學學報, 2015,35(11):3604-3611.
[15] 李 興,李建茹,徐效清,等.烏梁素海浮游植物功能群季節演替規律及影響因子 [J]. 生態環境學報, 2015,24(10):1668-1675.
[16] Liu X, Qian K, Chen Y. Effects of water level fluctuations on phytoplankton in a Changjiang River floodplain lake (Poyang Lake): Implications for dam operations [J]. 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 2015,41(3):770-779.
[17] 汪 星,鄭丙輝,劉錄三,等.洞庭湖典型斷面藻類組成及其與環境因子典范對應分析 [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2,31(5):995-1002.
[18] 李利強,黃代中,熊 劍,等.洞庭湖浮游植物增長的限制性營養元素研究 [J]. 生態環境學報, 2014,23(2):283-288.
[19] 國家環保總局《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編委會.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 [M]. 4版.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 2002.
[20] 齊雨藻,李家英.中國淡水藻志 [M].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
[21] 徐金森,鄭天凌,郭清華,等.兩種海洋細菌對赤潮藻的細胞生物量的影響研究 [J]. 海洋科學, 2002,26(12):57-60,67.
[22] Aksnes D L, Wassmann P. Mode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zooplankton grazing for export production [J].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1993,38(5):978-985.
[23] Lampitt R S, Wishner K F, Turley C M, et al. Marine snow studies in the Northeast Atlantic Ocean: distribution, composition and role as a food source for migrating plankton [J]. Marine Biology, 1993,116(4):689-702.
[24] 劉 瀟,薛 瑩,紀毓鵬,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黃河口及其鄰近水域水質評價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5,35(10):3187-3192.
[25] 王 華,楊樹平,房晟忠,等.滇池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與環境因子的典范對應分析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6,36(2):544-552.
[26] Kent M. Vegetation description and data analysis: a practical approach [M]. John Wiley & Sons, 2011.
[27] 李利強,張建波.洞庭湖浮游植物調查與水質評價 [J]. 江蘇環境科技, 1999,12(4):14-16.
[28] 陳格君,周文斌,胡春華.鄱陽湖五河入湖口浮游藻類及營養現狀評價 [J]. 湖北農業科學, 2013,52(9):2048-2052.
[29] 鐘振宇,陳 燦.洞庭湖水質及富營養狀態評價 [J]. 環境科學與管理, 2011,36(7):169-173.
[30] 黃代中,萬 群,李利強,等.洞庭湖近20年水質與富營養化狀態變化 [J]. 環境科學研究, 2013,26(1):27-33.
[31] 周 泓,歐伏平,劉 妍.“十一五”期間洞庭湖水環境質量狀況及變化趨勢分析 [J]. 湖南理工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1, 24(2):88-90.
[32] 王麗婧,汪 星,劉錄三,等.洞庭湖水質因子的多元分析 [J]. 環境科學研究, 2013,26(1):1-7.
[33] Wang X, Zheng B, Liu L, 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Lake Multi-biotic Integrity Index for Dongting Lake, China [J]. Journal of Limnology, 2015,74(3):594-605.
[34] 汪 星,劉錄三,李 黎,等.鏡泊湖浮游藻類組成及其與環境因子的相關分析 [J]. 中國環境科學, 2015,35(11):3403-3413.
[35] 沈會濤,劉存歧.白洋淀浮游植物群落及其與環境因子的典范對應分析 [J]. 湖泊科學, 2008,20(1):773-779.
[36] 劉鴻雁,徐云麟.鏡泊湖藻類生長和湖泊富營養化預測初探 [J].生態學報, 1996,16(2):195-201.
[37] Jiang Y J, He W, Liu W X, et al. The season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a large eutrophic chinese lake (Lake Chaohu)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40:58-67.
[38] 潘繼征,熊 飛,李文朝,等.云南撫仙湖透明度的時空變化及影響因子分析 [J]. 湖泊科學, 2008,20(5):681-686.
[39] Arhonditsis G B, Winder M, Brett M T et al.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phytoplankton variability in Lake Washington (USA). Water Research, 2004,38:4013-4027.
[40] 楊麗標,韓小勇,孫 璞,等.巢湖藻類組成與環境因子典范對應分析 [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1,30(5):952-958.
[41] 盧金鎖,張 穎,胡亞潘.深水型水庫中藻類功能群組演替及其與環境因子的關系 [J]. 環境工程學報, 2014,(11):4605-4611.
[42] 黃國佳,李秋華,陳 椽,等.貴州高原三板溪水庫浮游植物功能群時空分布特征 [J]. 環境科學學報, 2015,35(2):418-428.
[43] 游 亮,崔莉鳳,劉載文,等.藻類生長過程中 DO、pH與葉綠素相關性分析 [J]. 環境科學與技術, 2007,30(9):42-45.
[44] 張 怡,胡 韌,肖利娟,等.南亞熱帶兩座不同水文動態的水庫浮游植物的功能類群演替比較 [J]. 生態環境學報, 2012,21(1): 107-117.
[45] 陳曉江,楊 劼,杜桂森,等.海子水庫浮游植物功能群季節演替及其驅動因子 [J]. 水資源保護, 2015,31(6):122-127.
Composi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lgal function groups in Dongting Lake.
WANG Xing1,2,3, LI Li-qiang4, ZHENG Bing-hui1,2,3*, LIU Yan1,2, TIAN Qi4, WANG Li-jing1,2,3(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riteria and Risk Assess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2.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Drink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3.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tific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for Lake Dongtinghu, Yueyang 414000, China;4.Dongting Lake Eco-Environment Monitoring Centre, Yueyang 414000,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36(12):3766~3776
This research was performed at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in 2013 at 11sections of Dongting Lake, aiming to investigate the algal function groups. A total of 24 kinds of algal function groups were identified: A、B、C、D、E、F、G、H1、J、LO、LM、M、MP、N、P、S1、SN、T、W1、W2、X1、X2、X3、Y, which reflected the habitat characteristics with species sensitive to the onset of stratification, and which are adapt to frequently stirred up, inorganically turbid, and mesotrophic to eutrophic shallow lakes. The algal function groups was dominated by B (mesotrophic waters in small-and mediumsized lakes with species sensitive to the onset of stratification), D (shallow turbid waters), J (well-mixed, enriched shallow lakes), MP (frequently stirred up, inorganically turbid shallow lakes), P (well-mixed, mesotrophic to eutrophic shallow lakes) and Y (refers to a wide range of habitats) based on the dominant degree (>0.02)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ich were found on algal function groups across 11sampling sections in the four investigations. The successional law of algal function groups in different seasons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 MP+P+D+B in March, MP+J+P+D+B in June, MP+J+P+D+B+LO+Y in September, MP+J+D+Y in December.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choose the major potential stressors which influenced the habitat of algae by SPSS 13.0, and CCA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al function groups and major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It is indicated from the results that water temperature (T), pH, dissolvedoxygen (DO),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Cr), ammonia nitrogen (NH3-N) and total phosphorus (TP)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lgal function groups across the 11sampling sections.
Dongting Lake;algal function groups;dominance;environmental factors
X826
A
1000-6923(2016)12-3766-11
汪 星(1983-),男,湖北荊州人,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水生生物評價的研究.發表論文30余篇.
2016-06-02
“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2014BAC09B02);“973”項目(2012CB417004);洞庭湖江湖生態監測重點站項目(JJ2013-023)
* 責任作者, 研究員, zhengbinghui@crae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