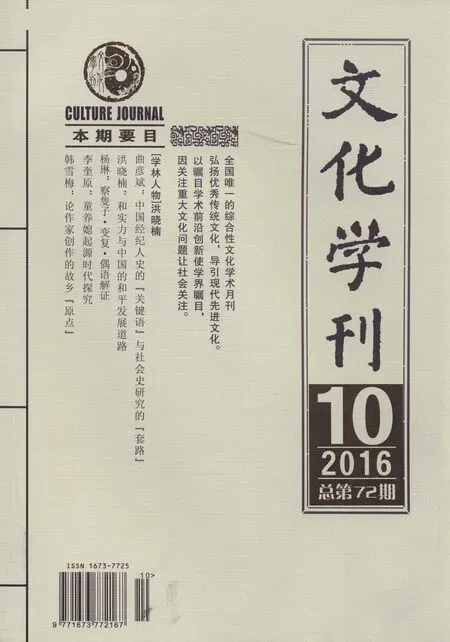中學西傳與自然神論
李錫明
(福建省泉州市委黨校,福建 泉州 362000)
?
【文化哲學】
中學西傳與自然神論
李錫明
(福建省泉州市委黨校,福建 泉州 362000)
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往的歷程也是中學西傳及西方認識中國的歷程。自然神論是西方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儒學的切入點,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歐洲思想運動的聯結點。自然神論源自古希臘,特指歐洲17至18世紀的自然神論,尤其是法國啟蒙時期的自然神論。歐洲的歷史變革,把傳教士傳來的中國儒學思想推上歐洲的歷史舞臺,融入歐洲歷史進程,對歐洲自然神論的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中學西傳;儒學;自然神論
一、中學西傳的聯結點
16至18世紀的歐洲正在延續著一場重大變革,中國文化西傳歐洲掀起了一陣中國熱,造就了一個中國的神話。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往的歷程也是中學西傳及西方認識中國的歷程,由于歷史上種種原因呈現突出的“單向交流”[1]特征。這個單向性的交流過程同時也體現在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解讀上,所謂中西文化“匯通”,在當時的歷史進程中實際上是西方“單方”認識,基本上沒有往來的融通。區別于器物物質文明的感知,西方關于中國文化的認知,最早始于傳教士,再就是漢學家,有人更是把傳教士,特別是入華耶穌會士,當作最早的漢學家。在藝術、文學和思想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器物和文化是彼此分割獨立的,形而上的思想認識往往游離于器物發展的先進程度,器物與思想文化各自保持了“固有的個性”[2]。文化交流表現為純粹思想認識的解讀。明清入華的西方傳教士通過書信、報告和著作等載體向歐洲介紹了一個歐洲傳教士理解、想象的歷史和現實中國,構筑了16至18世紀西方認識中國的思想基礎。在此思想基礎之上,沒有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解釋與自我的傳播,僅僅遵循西方文化的視角和維度,基于歐洲中心本位,尋找深藏在這些載體之中的中國思想文化,重新認識中國,甚至喊出發現了中國。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被當作他域的另類,處于被解讀、被建構的態勢,從而形成了當時歐洲認識中國的“中國觀”。
歐洲的中國觀建構主要產生在以“中國禮儀之爭”或稱“中國問題”為中心的一段歷史時期,即主要在歐洲16至18世紀的歷史時期。安田樸指出:“中國禮儀之爭還取得了另外一種成功,這就是迫使歐洲注意中國和孔夫子的思想。”[3]中學西傳的歷史脈絡和過程基本清楚,不會產生較多的爭議,但其背后緣由因果卻眾說紛紜,歷史影響的評判更是莫衷一是。朱謙之先生在《中國哲學對于歐洲的影響》談及,思想文化的接觸,中學東漸則在通商以外主要基于傳教和著述,把中國哲學之合理的部分傳入西方,成為“革命的導火線”。然而,陳樂民先生的《非作調人,稍通騎驛》則質疑“西歐的啟蒙運動竟是中國給‘啟發’出來的”。安田樸先生指出,不應該認為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是歐洲在歷史發展中所受到的唯一影響,日本、朝鮮、印度,以及突厥人,也對歐洲思想的某些方面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來,作為歐洲社會統治力量的基督教會勢力逐漸弱化,整個社會被一股世俗化趨向的浪潮激蕩沖擊,社會各方達成妥協,教會和貴族幾乎失去了至上的、絕對的統治力,但宗教依然是整個社會的核心議題,中學西傳初期的歐洲仍是一個宗教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從文化發展歷史規律的維度,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需要異質文化中有一個共同的聯結點。“自然神論”成為中國儒學介入歐洲思想運動的聯結點、切入點。“自然神論”以不承認人格神為基本宗旨,這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就有了內在的相類似的關聯性,也因此促使歐洲的自然神論注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哲學思想。
二、自然神論提倡理性
在西方哲學史中,自然神論主要以自然神學的形式存在于經院哲學中。自然神學的哲學源自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尋求事物背后的永恒本質,從具體形態的現實物質如水、火等中探究宇宙的本原、本體,但古希臘哲學的思維方式超越了對具體質料的感性認知,思辨的哲學認識從智性的存有即理智、理性中去追尋,崇尚人的理性能力可以認知世界、把握本原,包括獲得關于至上的神的認知。經歷了希臘化古羅馬之后,帕奈提烏斯首次提出自然神學的概念,并且提出三種形式的神學,即詩人神學、哲學家神學與政治家神學。西塞羅堅持以理性研究神學和宗教信仰,肯定理性在宗教信仰上重大的積極意義,從自然神學出發,批判政治家神學與詩人神學的神與人同形同性思想觀點。奧古斯丁進一步在批判政治家神學和詩人神學的立場上肯定了“自然神學”在宗教信仰上的重要意義,指出理性是神的根本特性之一,運用自然神學思想理論充分展現了信仰宗教的無形體性。安瑟倫在1077年的《獨語》中論證了上帝的存在是信仰存在的必要權威,并提出了思辨理性關于上帝的本體的論證理論,賦予上帝無法想象的、不可超越的偉大。托馬斯·阿奎那進一步提出著名的有關上帝存在的“五路”證明*“五路”證明即“從事物的運動或變化方面論證”,“從動力因的性質來討論上帝的存在”,“從可能和必然性來論證上帝的存在”,“從事物中發現的真實性的等級論證上帝的存在”和“從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來論證上帝的存在”。。赫伯特在1624年出版的《論真理》闡述了自然神論的特性及自己的看法,倡導自然神論的信條和觀念,為此被尊為“自然神論之父”。英國的自然神論在法國得到積極延續,法國神學家比埃爾·維雷在《基督教訓言》里把自然神論當作不信仰基督教神的思想理論,隨著基督教教義理性建構的不斷邏輯化、理性化發展,“自然神論”逐漸被賦予了與最初相反的意義。法國啟蒙思想家深受英國自然神論的直接影響,繼續提倡理性精神,以理性為至高的真理、原則和方法審視當時歐洲的一切。不同的是,17世紀英國自然神論審慎的傳統到了法國卻演變成了激進的反基督教專制制度的啟蒙思想運動。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自然神論直接把理性作為宗教信仰的基礎,認為基督教上帝是按照一種理性原則來創造世界的,創世之后,上帝就不再干預世俗事務,而讓世俗事務按照理性的原則存在和發展。自然神論的顯著特征是把上帝變成一個合乎理性的創世者,從而把基督教神學教義納入理性范圍來加以解釋、建構,用理性沖擊、突破和取代天啟形式的宗教教義。[4]
學界所說的自然神論往往特指歐洲17至18世紀的自然神論,特別是法國啟蒙時期的自然神論。廣義上來說,是把理性看作上帝的本質,用理性來限制或反對啟示和奇跡,主張基督教的要義就是那些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可以納入“自然神論”范圍。自然神論者提倡理性,反對蒙昧主義,批判各種違反自然規律的所謂“奇跡”,這成為當時擺脫傳統宗教的一種手段。說自然神論就是反對神學顯得過于籠統,忽視了自然神論攻擊神學的針對性、前提和底線。自然神論畢竟不是反基督教的,它把自然界的規律和秩序說成是按照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巧意安排的結果,沒有徹底超出宗教神學的范圍,其本意是反對中世紀教會不合理的教權及其某些相關的制度和理論。
三、中學西傳對自然神論的影響
毫無疑義,歐洲的自然神論在歐洲有其自身的起源和發展歷程,但歐洲在尋找自然神論的例證的時候,傳教士傳來的中國儒學思想融入歐洲變革的歷史進程,歐洲自然神論開始了與中國儒學的碰撞、交鋒,這對歐洲自然神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以自然神論作為對天主教甚至基督教進行攻擊的學說、理論武器,同樣也使用這個思想理論從他們的維度審視中國儒學的樸素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異質文化的交織就發生于此聯結點。到18世紀中葉,歐洲社會結構、哲學和科學等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革,在思想領域表現為思想家們開始直面現實社會的弊端,并要求闡明和確立新的社會秩序,基督教意義上的合理性審視被政治、經濟或道德上的合理性審視所取代。歐洲認識中國的重心隨之也發生轉移,人們更加關注與世俗王權相關的問題,許多啟蒙思想家開始借用中國皇權制度,攻擊歐洲不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
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領袖,與其他眾多啟蒙思想家相異,伏爾泰是中國和中國儒學最熱情的頌揚者和辯護者,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伏爾泰集中體現了啟蒙學者“百科全書”式博學的特點,一生都在批判封建專制制度,揭露和嘲諷天主教教會。伏爾泰批判封建思想的哲學基礎,就是他的自然神論。伏爾泰從小在耶穌會學院學習,受耶穌會宗教思想影響,與入華耶穌會士交往密切,十分了解他們關于中國的著述,以致伏爾泰的眾多著名著作中都有專門論述中國的相關內容,并形成關于中國的較為系統性的直覺認識。在探討世界起源和人類文明發展的研究過程中,伏爾泰認識到中國的古老歷史源流已超越出《圣經》教義范疇。基于對當時歐洲暴政的強烈不滿,反觀中國歷史上開明君主制度,伏爾泰轉而研究中國儒教,尤其是“仁”的思想理念,尋找批判的武器。他的整套哲學理論都明顯帶有中國影響的烙印,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其思想理論的啟蒙意義。伏爾泰流亡英國三年后發表了《哲學通信》,首次向法國人介紹了英國的哲學、文學及政治理論,他的自然神論繼承了英國自然神論提倡理性的思想傳統,堅持理性精神和力量,反對懷疑論對人之外世界的認識的否定,具有根深蒂固的英國淵源。
萊布尼茨的自然神論無疑是中國儒學思想對歐洲自然神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集中體現。萊布尼茨首先是哲學家,屬于自然神論者,他還是極富創造性的科學家,在數學、力學等方面都有造福后人的巨大成就。萊布尼茨將中國的儒家哲學稱作“自然神學”,認為是“與基督媲美的唯靈論”。1697年,萊布尼茨根據耶穌會士提供的材料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事》,出于其促進宗教大統一于基督的愿望,確信中西兩大文明必然有溝通的橋梁。萊布尼茨認為中國的哲學比古希臘的哲學更接近基督教神學。萊布尼茨認真研究宋儒的“理”,認為相當于他的第一位的“簡單實體”,從而成為中西哲學溝通的聯結點,也是兩種異質文明溝通的橋梁。萊布尼茨堅持運用理性原則論述中國人的自然神學,他是歐洲第一個以理性精神研究儒學的哲學家思想家,他根據入華耶穌會士關于中國的著述論證了中國儒學有與基督相似的思想觀念,并進一步指出中古人通過“理”來認識上帝。盡管在中國文化中缺少天啟的特征,但中國文化仍代表著對上帝的認識,仍是與基督教相融通的“自然神學”。萊布尼茨堅持中國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存在著超越性的至高神,反對把中國的神靈系統視為一種泛神論的觀點。中國儒學中那種既超越又內在的思想維度為歐洲理性主義哲學進入萊布尼茨-沃爾夫體系時代奠定了思想基礎。
[1]張國剛.16至18世紀西方認識中國的歷程[N].學習時報,2008-06-02(9).
[2][法]維吉爾·畢諾.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M].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
[3][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M].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47.
[4][美]約翰·奧爾.英國自然神論:起源和結果[M].周玄毅,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59.
【責任編輯:王 崇】

漢 光耀 宇
G634.51;B976
A
1673-7725(2016)10-0159-04
2016-08-05
李錫明(1965-),男,福建惠安人,副教授,主要從事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