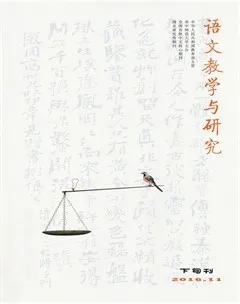《大衛(wèi)·科波菲爾》:慈悲是最美麗的天賦
魏天真
人們說查爾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國(guó)乃至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我個(gè)人還認(rèn)為他是所有異國(guó)作家中最符合中國(guó)讀者口味的。他的很多長(zhǎng)篇小說如《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遠(yuǎn)大前程》《老古玩店》《董貝父子》《艱難時(shí)世》《荒涼山莊》《雙城記》等,在我國(guó)都有廣大的讀者群,根據(jù)這些名著改編的電影也作為經(jīng)典為大家所熟悉。長(zhǎng)篇小說《大衛(wèi)·科波菲爾》,據(jù)說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一部小說,我覺得它也可能是最符合中國(guó)讀者心意、最能滿足我們的閱讀期待的作品。所以,我要借這一本書來說明他何以符合我們的口味。
這本書一開頭就讓我們看到了讓人放心、稱心的故事結(jié)局:功成名就的大衛(wèi)科·波菲爾在寫自傳。勤勞、善良、聰慧、單純的小伙子,最后有了自己可心的女孩,即使倆人在一起還要繼續(xù)勤扒苦作,也是充滿希望地一致協(xié)作著;忠直溫厚的長(zhǎng)者們也能踏實(shí)而安寧地度過余生,一眾好人都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地摸到了自己的幸福;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哈姆,似乎是個(gè)悲劇人物,但他的秉性、品質(zhì),卻贏得了尊敬,也對(duì)讀者心靈進(jìn)行了凈化,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嗎?那些壞家伙們,最終都付出了代價(jià)。當(dāng)然,在寫壞人作惡時(shí),作者并沒有失去風(fēng)度地作切齒的痛恨和憤怒狀;寫到他們的受懲或得到惡報(bào),也沒有顯出額手稱慶的失態(tài)。總之,書中那些陳陳相因的人生故事就像大自然的四季變化,色彩豐富而節(jié)律生動(dòng)。
善惡有報(bào),這大概是狄更斯講故事最符合中國(guó)讀者口味的地方,但狄更斯的善惡報(bào)應(yīng)觀念有跟我們有不一樣的地方,明白這一點(diǎn)很重要,善惡報(bào)應(yīng)對(duì)他而言仿佛是一種信仰。他不像我們國(guó)人把它當(dāng)作是一種安慰,更不會(huì)自居弱者而將它作為最后的砝碼。我們可能是因?yàn)樽约涸诓还降纳钪惺軅⑹苋瑁蛯?bào)應(yīng)當(dāng)作可以達(dá)到、應(yīng)該達(dá)到的目標(biāo),只有這樣,我們的為善為弱以及因此忍受的苦難才是值得的。但在狄更斯的書中不是這樣的。首先,他并不一定讓我們實(shí)現(xiàn)這樣的心理平衡,他也讓我們看到,人的善良、犧牲、奉獻(xiàn)不一定有相應(yīng)的酬報(bào),或者說善本身就是對(duì)善的一種回報(bào)。在《大衛(wèi)·科波菲爾》中的一些人,并沒有得到像我們通常所期待的那種善報(bào),比如哈姆、斯特朗博士;另一些人,他們得到的滿足換作是我們的話,就不一定是,甚至一定不是心滿意足,比如裴果提先生、姨奶奶、瑪莎小姐等人的際遇。其次,狄更斯讓我們看到,作惡的人,也未必如我們所愿地遭到所謂的惡報(bào)。小說寫到成年以后的科波菲爾和少年時(shí)代的朋友一起去參觀一座據(jù)說管理得很好的監(jiān)獄,這座監(jiān)獄的管理者是他們當(dāng)年的校長(zhǎng),這個(gè)校長(zhǎng)也是他們童年的噩夢(mèng)!他當(dāng)年對(duì)年幼的孩子們幾乎像個(gè)虐囚的酷吏,現(xiàn)在對(duì)那些屢教不改的罪犯又像溺愛孩子的家長(zhǎng)。更荒謬的是,那些罪犯居然那樣心安理地提出自己的要求,還那樣大言不慚地開脫自己,訓(xùn)誡他人。他們受到了什么懲罰?無論在肉體還是精神上,似乎都沒有。因?yàn)椋怏w上的懲罰在于限制他們的自由,可他們?cè)诒O(jiān)獄里就像在茶館里一樣自由自在;精神的懲罰訴諸人性及良知,可他們身上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如果說他們?cè)獾搅耸裁磮?bào)應(yīng),那就是讀者對(duì)他們的唾棄,并且由于小說對(duì)他們的丑惡言行和靈魂的刻畫,使讀者在現(xiàn)實(shí)世界能夠更加敏銳地辨識(shí)善惡美丑。如果說這是報(bào)應(yīng)的話,那也是人性的終極勝利,是人中丑類注定了的、象征性的失敗。
《大衛(wèi)·科波菲爾》真的是一本有道德教化功能的書,但它的道德教化也真的是潤(rùn)物細(xì)無聲的。首先,作家有一種一以貫之的仁慈,自自然然充盈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也自自然然流溢在這本書里,在細(xì)節(jié)描寫中,在對(duì)話中,在敘述語言中。就以小說中的一個(gè)很次要的角色“迪克先生”來說,從他的言行舉止和內(nèi)心世界的表現(xiàn),可以看到作者對(duì)每一個(gè)人的關(guān)切,即使是對(duì)迪克先生這么一個(gè)異于常人的人,也是那樣的真誠、尊重。小說寫到,到姨奶奶家不久,科波菲爾就與迪克先生成了好朋友。我們看看小科波菲爾眼里的迪克先生:
黃昏時(shí)分,我坐在長(zhǎng)滿青草的斜坡上,坐在他的身旁,看他注視著那高飛在恬靜的空中的風(fēng)箏。我心里時(shí)常想,風(fēng)箏把他的那顆心,從煩憂混亂的境地中帶出,飛上了晴空萬里。可是當(dāng)他一點(diǎn)點(diǎn)收起線,風(fēng)箏在美麗的晚霞中越來越低,直到飄飄搖搖地跌落在地,像死了似的一動(dòng)不動(dòng)躺在那兒時(shí),他才仿佛從睡夢(mèng)中慢慢醒來。
迪克先生是姨奶奶收養(yǎng)、監(jiān)護(hù)的一位遠(yuǎn)親,他曾經(jīng)被當(dāng)作一個(gè)心智不全的人遭受自家兄弟的虐待。現(xiàn)在,作者用孩子的眼睛看迪克先生,而讓我們獲得一種體恤他人的意識(shí)和能力,讓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可能會(huì)忽略的他人的需要,他人的美,他人的苦痛。有時(shí)候,作家也讓一個(gè)長(zhǎng)者把對(duì)孩子的教誨直接說出來,可他說出的方式是如此的貼切、動(dòng)人,以至于我們這些不在場(chǎng)的、不相干的、已經(jīng)成年了的自以為是的人也會(huì)被打動(dòng),銘記在心并且暗暗反省。當(dāng)姨奶奶親自為科波菲爾挑選了學(xué)校,送他進(jìn)學(xué)校,在和他告別的時(shí)候說的話就是這樣的。“千萬不要吝嗇,千萬不要虛偽,千萬不要?dú)埲獭!彼f,“你要能避免這三種罪過,我就永遠(yuǎn)對(duì)你充滿希望。”
如果說仁慈是作家的一種內(nèi)在氣質(zhì),幽默則是他的天生稟賦外化出來的風(fēng)度。關(guān)于幽默的例證不勝枚舉,我且用自己閱讀《大衛(wèi)·科波菲爾》時(shí)的聯(lián)想來說明狄更斯的種種幽默中的某一種特性。當(dāng)我讀到某些描寫時(shí),居然會(huì)想到我故鄉(xiāng)的某種生活氛圍或故鄉(xiāng)人的說話腔調(diào),比如想起母親小時(shí)候給我講的故事,其中之一是說一個(gè)人家死了男人,死得太突然,以至于棺材的油漆都來不及干。女人們撫棺嚎啕,十分地凄慘悲切。當(dāng)她們一邊摸棺材一邊抹眼淚時(shí),都染成了黑漆大花臉。她們舉頭抹淚之際,不免會(huì)看見別的女人的臉,特別是周圍的那些陪著留淚的人們也看見了……錯(cuò)愕之下,本來痛徹人心的哭腔里有了不由自主的笑聲,場(chǎng)面變得怪誕起來,但這怪誕也就是人世況味的一部分。狄更斯有的是那種本領(lǐng),他不說明、不明說,但讓你看見并感覺到那種況味。
由于仁慈、幽默,他的文本世界何其豐富而深邃!雖然被稱為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但他筆下的人物,絕不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可以概括和解釋的。在《大衛(wèi)·科波菲爾》中,眾多人物隨著科波菲爾的人生軌跡,出現(xiàn)在他的生活里,出現(xiàn)在讀者的視線中,“既順其自然,又合乎情理”(這句話出自姨奶奶對(duì)科波菲爾的贊賞和鼓勵(lì),當(dāng)時(shí)他剛剛結(jié)束學(xué)生時(shí)代,面臨職業(yè)選擇)。
- 語文教學(xué)與研究(讀寫天地)的其它文章
- 考而不死是為神
- 中國(guó)古代建筑特色
- 記憶里的味道
- 時(shí)間會(huì)告訴你答案
- 柔軟姑蘇
- 在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