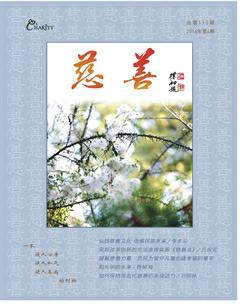中華傳統道德慈善文化要為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助力
陸鏡生
我們黨高瞻遠矚,提出兩個百年的目標:第一個百年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然后再展望第二個百年目標,一個更大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黨提出了“五大發展”的規劃和“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旨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理念。這種規劃和理念不僅是經濟學上的創新,也是社會倫理學上的創新。這種創新的源泉就是習近平主席說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治國理政中的大愛精神。國民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小康并非是完美圓滿的小康,社會公平和正義還只能是相對的,共享是承認差距,但要求把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一般而言,不論收入差距多少,社會上總會有人有“獲得感”,有人會有“失落感”。問題是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水平有了相應提高的人仍然有“失落感”,乃至比較富的人也有“失落感”。李瑞環同志曾說,有些人“端起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罵娘的人幾乎在不同社會階層中都有。古圣講“國者人之積”。你看這個國家上上下下的人,他們每天想什么、說什么、做什么,就知道這個國家存在的最大積習。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為什么罵娘的人如此之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在他的《市場、自由和國家》一書里說,“經濟領域的人是‘經濟人,非經濟領域的人也不例外,他們和經濟領域里的人一樣,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偏好。”我們國家是否存在這種狀況呢?原因在哪里呢?承載中華道德、慈善文化的儒釋道學說在近現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詆毀,正可謂“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怎敵它晚來風急?”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西方的功利主義價值觀、消費主義、工具理性被人們所崇尚。拼命賺錢和追求欲望的滿足取代了對生活意義的探求。人們對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存在著散碎雜拼的多元理解,看不清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和方向性指導,因此尚未真正地內化到我們的靈魂深處。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說過:“當我們為工具理性所擺布,無限追求效率、功利和成功時,它們也就消解了人的行為的價值意義,而陷入了目的迷失的境地。”
尤其嚴重的問題是人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愛國意識淡薄,許多人出國留學或工作,然后加入美國籍。丟棄了中國籍,意味著中國不再是自己的祖國了。他們不了解中華優良的傳統文化,不了解圣賢教育。這種彌足珍貴的文化和教育廣泛地流失,導致現代中年人和青年人身上幾乎看不到多少傳統的蹤跡。他們在物欲橫流、價值顛覆、意義迷茫、道德滑坡和精神家園失落的環境中,失去了對故土的歸屬感。他們拳拳服膺的根本觀念是什么?他們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可能是“美國夢”。什么是美國夢?美國夢就是美國媒體長期宣揚的:相信物質無限進步的線性發展過程,強調在“民主”統治下的社會里,個人不受束縛地積累財富是最高夢想。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來自對傳統文化的傳承,來自全社會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精神追求。當人們盲目地崇尚西方的個人自由,將“自我”置于自己生活核心地位的時候,這種“自我”會消解一個國家形成社會共同體所必需的獻身精神和社會成員之間的親密合作關系。我們不能不以沉重的心情,嚴肅地看待歸屬感和民族身份確定的削弱問題。我們對我們國家的外部環境要有清醒的認識。美國右派一直力圖以武力征服世界。他們認為,世界秩序必須迅速建立在美國軍事力量無可匹敵的超強地位的基礎上,并向世界各國推行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他們的新帝國大戰略是先發制人,提倡主權有限論,人權高于主權,無視和力圖改寫國際準則。我國的近鄰日本的右翼正在復活軍國主義,其鋒芒所向,直指我國。德國著名學者費希特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中說,“爭得勝利的,既不是臂膀的強壯,也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心靈的力量。”我們是應該到了重視“心靈的力量”的時候了。愛國靠的是每個中國人的“心靈的力量”。現在需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重點的擔當精神和家園情懷。而要有這樣的擔當精神和家園情懷,則需要中華傳統文化的以崇德弘毅、仁義共濟為重點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需要自覺培養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
當中國人民于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以后,將再接再厲,為更為偉大的目標,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這個偉大復興的核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然而復興傳統文化至今依然存在障礙。19世紀末葉以來,留洋歸來的所謂名流學者把中國歷史削足適履,硬套入西方社會發展模式,被說成是封建專制。歷史的真相是,秦統一后,實行郡縣制,此后總體趨勢是中央集權。郡縣制跟科舉制、官員流動制等相結合,維持了政治上的穩定。這同西方的所謂“五種社會形態”中的“封建社會”是不一樣的。其實最簡單的辦法是,查閱《大英百科全書》等西方辭書,把中西歷史比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說中國古代社會是封建社會實在是沒有根據的歷史判斷。至于說中國古代社會是專制社會,這更是無稽之談。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同。西方的國王是獨裁者。中國政治制度周朝就相當健全,漢朝就確立了。君權跟相權分得很清楚,像現代的公司,君主如同董事長、權力機構;相權是辦事機構,宰相相當于總經理。權責劃得很清楚。皇帝對重大事務并非一個人說了算,需要同宰相和各部部長商量。明朝以前,各部指三公、八座:三公是負責軍政事務的最高長官,八座是八種高級官員的總稱。宰相等高級官員對詔書從草擬到審核到執行都可以發表意見,封還詔書,即要求君主重新考慮。而諫官制度和史官制度等都是限制君權擴張的手段。在教育方面,皇帝不是用自己的語錄,而是用儒家和佛家、道家的經典。即使是清朝,皇帝也是用儒釋道的圣賢教育。比如雍正皇帝有一個“上諭”,指出“三教(儒釋道三教)理同”,并依之治國理政。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主要以身作則。古代的君主被稱為“天子”,意思是皇帝要替天行道,才能稱為“天子”,《左傳》講“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忠誠、信用、篤厚、恭敬,上上下下恪守它,這是自然的道理。這是君主替天行道應有的素質。《大學》講“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君主要做出表率,才能教育全國人民,大家來效法。這不同于西方的“君權神授”,無可比性。中國歷代王朝的覆滅,大多是因為末代皇帝昏庸好色,不是制度問題。君主只要守住圣賢的教誨,政權就會穩固。在20世紀,力辯中國古代社會不是封建專制的,是史學大師錢穆先生。他所著《國史大綱》至今依然是一本蘊含浩然之氣的史學力著,尤其是這本書的序言可謂光照日月。
稱中國歷史是封建專制歷史的名流學者往往同時說,儒家學說乃至儒釋道為代表的整個中華傳統文化是封建專制統治者奴役、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其影響由“文革”中的“四人幫”擴大到極致。改革開放以來,有良知的學者試圖公正地評價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近年來,力主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然而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負能量依然存在。前不久,一家晚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責儒家的“三綱”“五常”為專制主義者統治人民的手段。其實這是誤讀。“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意思是君、父、夫分別要為臣、子、妻做出好榜樣。“五常”是“仁、義、禮、智、信”。若是“五常”丟棄了,社會將如何?《左傳》說“人棄常(指五常)則妖興。”丟棄仁、義、禮、智、信,妖魔鬼怪都出來肆虐,天下能不亂嗎?沒有了仁義就沒有了人際的和諧,沒有了禮就沒有了恭敬心,對人際間必需的規矩就會持輕慢的態度。不守規矩的人肯定不會遵守法律。“智”是智慧,是善于明辨是非、正邪、利害、美丑等的悟性和能力。“信”是誠信。人沒有誠信,怎能立足于社會。讓人痛心的是,對儒釋道的誤讀比無知更可怕。
對于儒釋道,許多人認為它們是宗教,是有神論,因此跟它們保持距離,自然不會去讀它們的經典。這需要我們把道理說清楚,否則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話,儒家講的“仁愛”,佛家講的“大慈大悲”,道家講的“上善若水”就會被束之高閣。什么是“有神論”和“無神論”呢?基督教神學體系認定,“一神論”是“宗教”的特征。比如基督教,上帝聲稱是“唯一的真神”。在這種宗教文化背景下,否認或反對“一神教”的思潮就被稱為無神論。中國古代有佛教所說的“神不滅論”以及反對者的“神滅論”,此“神”僅指靈魂,不屬于西方有神論和無神論的范疇。中國無神論概念的出現,是在鴉片戰爭以后,跟基督教以空前的規模傳入我國直接有關。首先使用“無神論”概念的是國學大師章太炎。他提出的“無神論”的鋒芒直指基督教。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宗教”問題,更沒有出現過如西方那樣的宗教紛爭、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比如,梁武帝是信仰佛教(佛陀的教育)的皇帝。他的大臣范縝主張“神滅論”。有王公大臣和高僧大德六十余人撰文主張“神不滅論”,梁武帝并未采取行政措施來消除異見。范縝照樣當官,后來還當了更大的官。
儒家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呢?孔子說過“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的態度是“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注重現實的人。《論語·述而》講“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是不稱道。“怪”指怪異的事,“力”指好蠻力者,“亂”指子弒父、臣弒君之亂事,“神”指神鬼。孔子是教育家,不稱道怪力亂神,是因為講這些事無益于對人民的教化。《大學》講“明德、親民、至善”三綱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八目,是修身的綱要,這里沒有神鬼的地位。儒家講“天人合一”,“天”指宇宙自然的法則。天人合一是使天德下貫為人德,人德上齊于天德。天德與人德是統一的。這里也沒有神鬼的地位。
儒者終生進行“格物、致知”的修煉,努力擺脫世俗名聞利養的誘惑,懂得怎樣老老實實做人,并且在不斷的生命體驗中覺悟到“萬物與我為一”,進入“仁愛”境界,確立終極關懷和終極承擔,濟世獻身的理想和熱忱以此為源泉。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西方哲學講的主體跟客體的認識關系,而是心靈的感應。儒者悟到“萬物與我為一”,進入“仁愛”境界,就真正能“安身立命”。
國家宗教局前局長葉小文先生在《理論動態》第1620期上撰文說,“縱覽中國的文化在世界呈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全世界60億人口中,有48億人信宗教,12億人不信教。而中國近13億的人口中,信仰宗教人口約一億多人,近12億人不信教。如此說來,全世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集中在中國。”為什么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沒有成為幾大宗教的成員?葉先生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特殊積淀的結果,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人們,使他們‘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中國十億人至今沒有信教的歷史原因。”葉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儒家的“敬鬼神而遠之”是無神論。
中國古代沒有“一神論”的崇拜。佛教的“教”是教育的意思。佛不是神,他是“覺者”(覺悟者),覺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佛陀從事社會教育近50年,就是把覺悟到的宇宙人生真相告訴一切眾生,使他們都能覺悟起來。佛陀的一生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一生。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高僧大德一直做的是教育事業。歷代王朝都有兩個教育部:一個是孔孟教育部,由宰相管;另一個是佛陀教育部,由皇帝親自管。這是帝王與宰相在教育事業上的分權。儒釋道三種教育是文化多元一體,都是以“積德”為本。教育的目的是轉凡為圣。“圣”是指覺悟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為什么世界上稱佛教為宗教呢?這是源于西方來華傳教士看到佛寺里的佛、菩薩塑像,武斷地說是神像,并貶低為多神教。在傳教士眼里,多神教是低級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是高級宗教。基督教是在唐朝貞觀年間傳入中國,長期以來并未在中國站穩腳跟。18世紀羅馬教皇力主讓天主教的上帝崇拜取代中華民族的祭祖和祭孔,并干涉中國內政,康熙皇帝把傳教士全部趕走。中國自古有“慎終追遠”的倫理情懷,敬重祖先,講究孝道,從孝敬自己的父母,擴大到孝敬天下的父母。這是中華民族的“尋根”意識。它也是中華民族遇到外敵入侵時,海內外華人凝聚起來面對挑戰的文化紐帶。“宗教”這個詞是19世紀中葉由日本傳來中國。在此以前,中文字典、詞典中都沒有“宗教”這個詞。
我們人類居住在三度空間,四度、五度空間的生命,我們看起來像神仙一樣。佛家認為“依正不二,自他一體”(“正”指人,“依”指人的生存環境,兩者是一體。)所以佛家教導我們“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慈善是不講條件的,平等的。“同體”在《維摩詰經》中講“以眾生病,是故我病”。眾生苦、病,我們感同身受。宇宙是一體。一體決定不能分割。佛家明白宇宙人生真相,所以決定禁止求神、問卜、算命、看風水等。佛在《阿難問事佛吉兇經》里,說得很明白,像世間婚喪、一般應酬世俗禮俗可以做,但不能求鬼神保佑,不能求趨吉避兇。
佛陀把一切眾生看作教育對象,包括天界的各種天神。在佛經里講到佛陀在天界給天神說法講經。基督教等正統宗教講到天堂和地獄,主張以博愛之情待人接物,主張積德行善以便死后進入天國;倘若為非作歹,死后會墮入地獄。比如讀基督教《圣經》的人會有敬畏感,有對天堂的仰慕和對地獄的恐懼,從而對自己嚴加約束。這也是為什么全球多數人信仰宗教、世界各國的憲法都莊嚴地規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對于正統宗教所講的天堂和地獄,無神論者跟宗教信仰者不必辯論,因為歷史告訴我們,辯論不會有結果。但基督教等正統宗教關于不干惡事、只干善事和善惡報應等的教誨,的確是有著勉勵大家尊重法律和道德自律以及自覺慈善捐獻的客觀作用。另一方面,《圣經》中上帝聲稱他是唯一的真神,這就排斥了其他正統宗教。《圣經》的“摩西十誡”有這樣的話:“我是耶和華,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發慈悲,直至千代。”“祭祀別的神,不單單祭祀耶和華的,那人必要滅絕。”《圣經》的“馬可福音”講“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禮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這說明了上帝的所謂博愛并不博,只限于他的信徒。這表明基督教對外的絕對排他性和擴張性,對內的絕對封閉性和內聚性。這也是不斷發動宗教戰爭的內在依據。《摩西十誡》中講“不可殺人”(you shall not murder),不講“不可殺生”(you shall not kill)。這是“人類中心論”,人可以無情殺害動物,成為地球上的霸主。更有甚者,西方基督教教會直接在中國辦學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一直作為培養和傳播基督教,變中國為基督教國家的思想基地。早在1887年,傳教士韋廉臣在上海設立“同文學會”(基督教出版機構),就在一封信中寫道,“設立這個組織的動機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國人的武裝,使他們俯伏在我們的腳下。”基督教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文化工具。20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宣揚“以宗教自由為基石”的人權成為美國“新干涉主義”的武器。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提出“文化沖突論”,他特別提及美國基督教與中國佛教的未來沖突,其矛頭直指中國傳統文化。亨廷頓的學說已成為美國政府的國策。美國國會曾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宣稱要以國家力量進行基督教全球戰略的擴張。美國以國家力量推動基督教戰略擴張,不斷在“人權”和“宗教自由”領域向中國發難。我國著名學者文丁在其《〈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一文中,在評價美國基督教對華戰略擴張的態勢時指出,“它可以開動全部國家機器,從總統、國務院、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運作,許多教會組織和教會、院校協同配合,形成國家、教會和非政府組織各以不同優勢對外擴張,政治威脅、經濟收買、文化宣傳、合法與非法手段齊頭并進,以至于能夠在基督教歷來式微的我國,制造相當強的輿論,進入高等講堂和學書研究機構,地下教會敢于與國家法規公開對立。”事實上,美國在我國搞地下教會由來已久。它以文化的名義傳教。而長期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本土得不到普及,中華子孫得不到儒釋道的仁愛和慈悲精神的滋養,這給美國基督教在中國的地下教會以可乘之機。重要的是,我國具有中國特色的“三自體制”的基督教。三自(自治、自養、自傳)體制是中國基督徒獨立自主自辦的體制,是中國基督教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中國的國家主權在宗教領域的具體表現。我們要重視發揮佛寺、道觀、孔廟的社會教育作用,發揮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教會、清真寺等的社會教育作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中國人民的夢。要夢想成真,需要掀起一場復興中華優秀傳統道德和慈善文化的啟蒙運動,全國性的啟蒙運動。這一啟蒙運動的成敗命運掌握在兩種人手里:一是各級領導人,二是媒體人。這兩種人真正體會了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于中華文明。中國傳統決定了中國的特色。”真正覺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力抓好社會教育,利用無處不在、無時不入的電視系統和網絡系統,邀請和組織真正通曉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和慈善文化的學者、專家開展啟蒙講座,設立專門頻道。有這樣的社會教育的力度,才是為兩個百年目標助力。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認識到中華傳統道德和慈善文化的悠久和豐厚以及思想的深邃。它是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支柱。我們中華民族的子孫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僅靠法律制度這一強制手段來約束,更需要靠中華傳統道德和慈善文化的信念來延續我們中華民族的血脈,增強志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凝聚力。中華民族的興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定要靠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