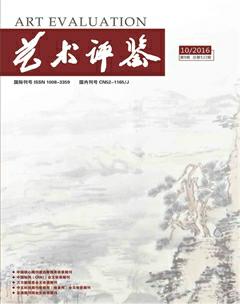俄羅斯文化中的圣愚
劉瑩
摘要:圣愚是俄羅斯文化中東正教的“神圣”與薩滿教“癲狂”“愚蠢”的結合體,這種精神亦在俄羅斯知識分子身上有所體現。十九世紀民族樂派的領軍人物巴拉基列夫就具有較為明顯的圣愚特質。本文從他的創作和生活方面來論述了巴拉基列夫的圣愚特征。
關鍵詞:圣愚 巴拉基列夫 民族樂派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6)19-0019-03
“圣愚”是俄羅斯文化中的特殊現象,指的是既“神圣的”又“愚蠢的”性格特征,也就是說有這么一種人,他們有著超乎常人的智慧,甚至可以預測未來,而生活中卻是類似瘋子一樣的習性或是有著非常極端的性格。這種說法最早來自于東正教的僧侶“癲僧”,一些俄羅斯著名人物身上都有這種圣愚的體現,如彼得大帝、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音樂家穆索爾斯基等。而作為穆索爾斯基的“引路人”,強力集團的領袖巴拉基列夫,更具備這種“圣愚”精神。
巴拉基列夫是俄羅斯十九世紀音樂史上一位承前啟后的人物,上銜“俄羅斯音樂之父”——格林卡,他領導的“強力集團”下啟二十世紀俄羅斯音樂的輝煌,并影響印象派和現代風格的音樂創作。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關鍵性的人物,卻最終與“大師”這個稱號擦身而過,這與他非常極端的性格不無關系。他幾乎沒有系統的學過專業的作曲技法,僅僅通過分析巴赫等人的樂譜獲得作曲知識,他注重俄羅斯民間音樂的發展,以西方作曲技法和俄羅斯民間曲調結合創作出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卻反對以西方技法為主的柴可夫斯基的創作;他培養了穆索爾斯基、鮑羅丁、里姆斯基-科薩科夫這幾位音樂家,卻最終與他們決裂;并且在創作之盛年就轉行不再從事音樂,直到逝世。
一、創作中的“圣”
巴拉基列夫1837年出生于俄羅斯的下諾夫哥羅德,1910年卒于圣彼得堡,自幼學習鋼琴。早年讀俄羅斯的神話以及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作品,學過一些基礎的作曲知識,憑著對音樂的熱愛,他分析了很多巴赫和貝多芬的樂譜,并成為第一個去高加索地區采風的音樂家。采風期間搜集了大量的俄羅斯民歌,編寫了《三個俄羅斯主題的序曲》,鋼琴幻想曲《伊斯拉美》就是結合了從高加索采風回來的俄羅斯民間曲調而創作的鋼琴幻想曲,其技藝之高深被稱為世界十大最難的鋼琴曲之一。
俄羅斯的土地廣袤壯麗,遼闊無垠,藝術家對這片土地充滿了深沉的愛,特別是俄羅斯的鄉村文化。鄉村是俄羅斯的靈魂,這片土地孕育了藝術家,孕育了俄羅斯精神,更孕育了俄羅斯精神。從格林卡的《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和《為沙皇現身》,到鮑羅丁的《伊戈爾王》,無一不凝聚著音樂家對民間文化的深情。
巴拉基列夫對民族音樂是如此的熱愛,他認為,只有運用民間音樂素材,才能使作曲家寫出這個國家的音樂珍品,他曾經寫過:“每當我悲傷的時候,我就會凝視銀色的伏爾加河,在纖夫燃氣的火堆旁邊聆聽伏爾加的船歌”。在《俄羅斯主題序曲》中,他就使用了當時非常流行的民歌“小白樺”的旋律。他的作品幾乎全都具有濃濃的俄羅斯民間音樂的風格,根據萊蒙托夫的詩歌寫成的管弦樂作品《塔瑪拉》就帶有豐富的東方色彩,并擁有豐富的管弦樂音色特征。巴拉基列夫極具音樂才華,能夠將淳樸而熾熱的俄羅斯民間音樂元素化成管弦樂的語言。
被稱為世界十大最難鋼琴曲之一的《伊斯拉美幻想曲》也成《東方幻想曲》就是一部技巧性極高的炫技性作品,快節奏的部分頗有他所崇拜的作曲家李斯特的風格,其中也不乏夢幻般的東方幻想因素。
巴拉基列夫的交響曲中,也是融合了大量的俄羅斯民間舞曲,如同奔跑著的俄羅斯音符。節奏歡快、內容熾熱,總能把人帶進俄羅斯節日的村莊。
1860年,巴拉基列夫沿著伏爾加河旅行,走到高加索地區采風,帶回了大量的民歌和舞蹈的節奏,并用這次采風搜集到的三首曲調寫下了交響詩《俄羅斯》。
他崇拜李斯特式的炫技,欣賞柏遼茲帶有標題的弘大篇幅,所以才會有《伊斯拉美》這樣的帶有濃烈的民族風格又炫技型的鋼琴作品。巴拉基列夫所追求的并不是優美或者動聽,他要的是一種能夠讓人沉醉或者舞動起來的名叫音樂的韻律,要有民間舞曲的味道,巴拉基列夫把民族的元素和西方的技法相結合,幻化成自己的音樂語言。
巴拉基列夫的管弦樂作品繼承發揚了格林卡《卡瑪林斯卡婭》的傳統,體裁都是用了當時西歐興起的“交響詩”這種單樂章標題性管弦樂形式,《塔瑪拉》則是根據萊蒙托夫的一則傳奇故事而譜寫的交響詩,作品亦受李斯特的交響詩《山中所聞》和《死之舞》的影響,對后來印象樂派的德彪西和拉威爾的創作也有些啟示。《李爾王》在更多方面則更接近舒曼和柏遼茲的作品。
二、性格中的“愚”
巴拉基列夫18歲的時候去了圣彼得堡,并結識了“俄羅斯音樂之父”——格林卡,格林卡深為他的民族理想所感動,鼓勵他作曲并讓自己的侄女也跟隨他學習。后來他逐漸認識了藝術評論家斯塔索夫以及鮑羅丁、居伊等四人。在斯塔索夫的極力宣傳之下,就產生了以巴拉基列夫為首的“強力集團”,即五人團。
巴拉基列夫有一定的音樂天分卻沒有經過很系統的學習,他熱心但是性格卻暴躁又喜怒無常。在剛認識居伊、鮑羅丁、穆索爾斯基他們的時候,他以自己不太專業的作曲知識來教授他們,和他們一起分析大師的譜子,并鼓勵他們大膽作曲。他和他的小組——“強力集團”為弘揚俄羅斯的傳統音樂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使其結合了西方的創作技法,為俄羅斯音樂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他們小組在當時也一直被稱為“巴拉基列夫小組”。
居伊曾經在論文《關于俄羅斯音樂的歷史與歷史學的幾點想法》中這樣來描述他們的學習:“我們形成了一個親密的青年作曲家圈子。由于沒有地方學習(當時尚無音樂學院),我們便開始自學。學習內容包括彈遍每一位大作曲家的每一首作品,分析批評其中的技巧和各個創造性方面。我們少年氣盛,批評苛刻。我們對莫扎特和門德爾松的態度十分不敬,視舒曼為門德爾松的對立面,雖然舒曼遭到人們的忽視。我們十分熱衷于李斯特和柏遼茲,崇拜肖邦和格林卡。我們爭辯得面紅耳赤,我們討論音樂曲式、標題音樂、聲樂、特別是歌劇形式”。①
巴拉基列夫脾氣古怪,性格專斷,對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并容不下跟自己的作曲理念相左的意見。1862年,他擔任圣彼得堡免費音樂學校的校長助理,并在校管弦樂隊任指揮,排練和演出他們小組成員的作品。最初指導他們創作并經常一起討論音樂,當他的兄弟們逐漸成熟,羽翼豐滿,對作曲有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就越來越不按他的方法創作了,他就大發雷霆,指責他們。漸漸的大家也與他疏離,他更加氣憤,最終與他們決裂。
當在創作上他找不到出口的時候,巴拉基列夫就變成了一個狂熱的宗教主義者,并且去相信了民間薩滿教的代表人物——女巫的語言,并認定自己是他們的精神救贖者。1871年他徹底與原來的圈子決裂,1883-1895年被任命為宮廷禮拜堂的樂長,后來自己寫了一首《C大調交響曲》,直到1910年去世,都沒再跟之前圈里的朋友再有聯系。
在東正教的傳統中,就時常會有一個圣愚式的人物——“癲僧”,即來自于俄羅斯東正教和民間薩滿教的結合,既是教士又是巫師,即瘋瘋癲癲又能夠預言。在很多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中都有描述,如穆索爾斯基的歌劇《鮑里斯 戈杜諾夫》里的預言家,普希金的小說中的癲僧等。現實中亦有伊凡雷帝時期的圣瓦西里和末代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身邊的拉斯普京,都是據說可以“通神”的預言家,但同時他們又是區別于常人的衣衫襤褸和精神錯亂之人。
肖斯塔科維奇曾經說過,穆索爾斯基身上就有這種“圣愚”精神。其實每個俄羅斯人身上都有這種精神,文學家、藝術家只是放大了這種特質。俄羅斯文學家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具有這種圣愚精神,巴拉基列夫無疑也是一個十足的圣愚。
三、錯過的“大師”
在俄羅斯廣袤的平原上,一年中有一大半時間是望不到盡頭的枯黃。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極其容易產生一種不著邊際的孤獨感,所以在俄羅斯人的性格里,有一半的憂郁,一半的極端,構成了兩極化的矛盾體。這種特質在詩人、藝術家身上有著極為明顯的體現,如文學家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音樂家穆索爾斯基、柴可夫斯基等都是如此,作為“強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巴拉基列夫,則更為明顯的表現出來這種極其容易憂傷又常常很偏激的矛盾性。
有些人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這種精神像火焰一樣燃燒起來,有的人則無法把這種矛盾體化成別人能聽懂的藝術語言,巴拉基列夫屬于后者。他有才華和對音樂無限的熱愛,然而由于沒有經歷過特別專業的作曲訓練,和他極端的性格,就導致了最終沒能有更加大部頭的,以及不朽的作品呈現給世人。
在俄羅斯音樂的進程中,作為繼格林卡之后點亮了民族樂派之火的“強力集團”的精神領袖,在培養了穆索爾斯基、鮑羅丁、里姆斯基-科薩科夫這幾位音樂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師級的作曲家之后,自己最終與“大師”的稱號擦身而過,變成了一個默默無聞的引路人,在引完路之后迅速退隱在歷史的大幕之后,可能當年的音樂家和評論家們也沒有猜到這樣的結局吧。
注釋:
① [美]格勞特:《西方音樂史》,余志剛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1996年版,第6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