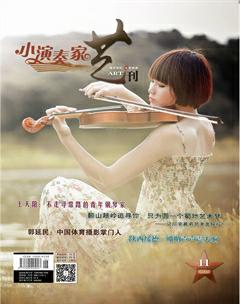張夢:踐行笙之夢
越聲

笙是中國古老的簧管樂器,也是世界上極早使用簧片發聲、并能演奏和聲的吹奏樂器。然而,人們對這件樂器了解不多,尤其在流行的民族器樂組合中,笙的使用率更少,原因何在?很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想了解其中的緣由。
◎越 聲
80后挑起大梁
張夢很年輕,卻是上海音樂學院這幾年重點培養的雙學歷演奏家、作曲家。他自小隨父親學習笙,后跟隨翁鎮發、翁鎮榮、牟楠和徐超銘等老師學習,現為中國民族管弦樂協會笙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音樂制作人,上海馨憶民族室內樂團笙演奏家、駐團作曲家,也是被中外笙圈子逐步認可的繼承人。
就前言中的緣由,張夢說:“一是因為了解笙樂器的人不多,甚至有些人從未聽過笙的聲音,這在于我們笙圈子推廣力度不夠;二是因為有些組合形式的樂隊需要的是演奏者站著演奏,笙雖音域齊全,但通常以坐姿演奏為主,傳統笙雖在演奏姿勢上均可,但由于音域有限,無法勝任新音樂形式多變的要求;三是由于笙的音色比較中和,在樂隊中有“溶劑”作用,但有些演奏家或作曲家認為笙的音色并不太有個性。其實,就我本人而言,這些問題更需要我們這一代努力去解決。”
為了改變笙在人們心中的傳統守舊印象,張夢在上海舉辦了一場笙味十足的顛覆性創意音樂會。在這場音樂會中,張夢化身為“大廚”,帶領一眾“食客(觀眾)”品嘗他和音樂界好友為大家精心呈現的八道“菜”。在這八道“菜”中,張夢通過傳統(各流派)、爵士、電子、世界音樂(即興)等多種元素,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技巧呈現出笙的多元表現力。
音樂會上的一道“西式甜品”引起觀眾極大興趣,這就是一首經典的爵士樂曲《Blue Bossa》,此曲雖被無數爵士樂手演奏過,用笙演奏卻很新鮮。張夢手中的笙仿佛化身薩克斯管,曲聲輕松慵懶,與低音貝斯手一唱一和、一清亮一低沉,宛若兩個人在進行一場充滿意趣的對話。
當晚,被譚盾看好的“招牌菜”是由張夢本人作曲、用簡約的素材以循環反復的手法創作而成的《童年回憶 》。樂曲融合了四種元素,首先由笙樂打頭,吹出充滿回憶的童年旋律《丟手帕》,此后又加入B-BOX等口技,用效果器疊加循環,以最簡單的節奏和元素,喚起觀眾對童年單純快樂的回憶。
音樂會結束后,一直潛藏在觀眾席中的著名作曲家譚盾上臺祝賀張夢,稱贊道:“他的音樂很有想象力,頗有新意,尤其在技巧的表現力和音樂的感染力方面有著恰如其分的平衡。”
張夢事后接受采訪時說:“我進入上海音樂學院學習后,逐漸發現中國民族樂器的滯后發展主要在于作品的缺少,以往許多民族樂器作品都是演奏家‘業余創作,這對笙的發展和推動顯然不利。”
特殊的藝術經歷和家庭環境使張夢深知傳統的深刻含義,深知自己淳樸的演奏風格、扎實的演奏功底和靈活多變的音樂觀念的形成正是根源于對傳統曲目千百次的研習。
后來,張夢報考了著名作曲家王建民教授的研究生,他聽過上萬張CD、學習了二十余種中外管樂樂器的演奏,早在本科期間,就憑借自己于2008年創作的《玄煙》獲得過上音創作、演奏雙項比賽第一。
兩代人追夢上海
張夢的父親曾在專業文藝團體擔任笙演奏員,后來為了提高自己在笙專業上的演奏水平,給上海的三十七簧笙發明者之一的著名笙演奏家翁鎮發先生寫信求教,自此遠在河南的張夢父親經常去上海求學。之后,他雖然轉業做與音樂無關的工作,但還是一如既往地熱愛笙,由此也讓兒子喜歡上了笙。
張夢回憶道:“自我認識并接觸笙這件樂器起,就一直十分喜歡它,從未產生過抵觸情緒。因為父親愛笙,他將自己對笙的感情言傳身教于我,進而使我也對笙萌生了熱愛之情。那個時候,我經常聽我父親在家或演出時演奏的作品,有翁鎮發先生的《暢飲一杯勝利酒》及改編的《達姆達姆》《沂蒙山歌》等。”尤其令張夢難忘的還是那首《達姆達姆》,正是這首樂曲讓他義無反顧地踏上了音樂之路。至今,張夢還時不時演奏這首樂曲。
“在古代道教音樂里,笙師都是要擅長十多種樂器的,我從小也想變成多才多藝的人。以我學習長號為例,當年小學里正好要組建軍樂團,老師看我具有一定的音樂基礎,就建議我參加。經過考慮,我選擇了長號這件銅管樂器,原因很有意思,我覺得這件樂器與其他管樂器不同,其他管樂器都要按鍵來吹,而長號則是拉的。其實,我后來學習其他樂器都是興趣使然。或許是習笙的緣故,之后自學的種種樂器無論中西管樂,還是西洋彈撥樂,我都可以算得上無師自通。我覺得音樂是相通的,樂器亦是如此,在演奏技法、作品的處理、音樂的感悟方面會有或多或少的相通之處,因此接觸其他樂器便更容易上手。”
張夢覺得不同的民族管樂器一定有著一脈相承的地方,這就是氣,我以為氣不僅是指氣息的運用,即一位演奏者在演奏過程中要注重把握好氣息,用不同的氣息演奏出有區別的聲音,更是指一種精神、一種氣魄。民樂是有魂的,同樣,一位優秀的演奏者要將這種氣場、這種民樂的靈魂演繹出來,不單單讓聽眾聽到純粹的音樂,更要讓聽眾感受到民樂的魄力。“作為年輕演奏者,我們在繼承老一輩演奏方法的同時,還需要開發出一些新的演奏技巧、 手法、舞臺表現和音樂概念等等。”張夢說。
好勝心讓我學習作曲
好勝心其實是每個孩子的“補藥”,用得好,會促進孩子的學習。張夢小學三年級時寫了一首笛子曲,興致勃勃地把樂譜拿給老師看,結果卻被潑了冷水,他現在還忘不了老師對他說的話:“你這么小,連書都沒念好,就想著作曲,老老實實演奏樂器吧!”說實話,張夢當時很受打擊,曾一度不再考慮作曲的事情。上中學之后,通俗、搖滾等音樂風靡,張夢又開始自己創作一些流行歌曲,當時完全是為了玩,還拿著吉他在班里與同學們一起彈奏,充實業余生活。
后來,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辦的現代派音樂會喚醒了張夢作曲的夢想,從那時開始,他自學作曲,并開始創作作品,讀作曲專業研究生也是希望自己能夠進行系統化、規范化的學習,進而從半職業轉變成為職業作曲者。
自從第一首三十七簧笙獨奏曲《玄煙》獲獎后,張夢一發不可收,創作靈感猶如黃河之水滔滔不絕,接著又創作了民族室內樂作品《荒寂》,并憑借這首作品參加了“民音杯”民族室內樂比賽獲得了優秀獎。除此之外,他還陸陸續續為各種形式的編制或獨奏樂器創作作品,如2010年為二胡與打擊樂寫的《雙聲子》榮獲了全國高等藝術院校二胡作品比賽銀獎。
除了給笙等民族音樂作曲,他還涉及不同領域的音樂風格,嘗試自己沒有聽到過的音樂。至今,他已創作了幾十首音樂作品,涵蓋古典、現代、爵士、搖滾、電子、世界音樂、實驗先鋒等不同類型。從小學習眾多樂器且積累了豐富的實踐演奏經驗,在一定程度上為張夢的創作之路奠定了基礎。
就像其他的世界音樂一樣,中國音樂也有自己民族的語言,自然要表現自己的特色,讓更多的人欣賞接受。千百年來,中國的音樂家們一直希望將我們的民族樂器加以完善,但衡量標準則應以不犧牲自己的優秀傳統為前提。
張夢告訴我:“我在上海曾組建過幾支樂隊,并在里面加入三十七簧笙的演奏,有時還將笙作為主奏,但我發現一個問題,與我一同做樂隊且喜歡笙樂器大部分是外國人。”
作為一名專業演奏家和作曲家,張夢時常仰望笙的光輝,堅守笙的傳統,保持民間的音樂底色,但他又是一位不安分的青年人,這份不安分使他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使他獲得傳統與現代,兩種觀察笙音樂及中國民族音樂的視角,構建起屬于自己的笙音樂世界。他希望自己和父輩深愛多年的笙表演與傳承能呈現出生機勃勃的新面貌和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他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在笙的演奏形式、笙曲的題材和風格等方面探索許多新的可能。
從張夢身上,我看到年輕音樂家勇于探索勇于實踐,踐行著自己的夢。正因為有這樣的年輕音樂家,近年來不斷有作曲家開始關注笙的演奏問題,并有大量的笙曲問世,有的是笙獨奏,有的則是笙樂器與西洋室內樂或混合室內樂合奏,還有的是笙協奏曲與民族或西洋管弦樂合奏。總之,林林總總的笙演奏形式也在不斷拓展著笙樂器的演奏與發展,也慢慢綻露出笙樂器自身的演奏特點及其特有的魅力。
“笙藝術的發展需要好的作品,我自己身體力行,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作曲家能為笙創作既能體現笙優秀傳統特色、又能體現傳統樂器現代話語的好作品,那么笙藝術的復興和傳承就會如虎添翼。”張夢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