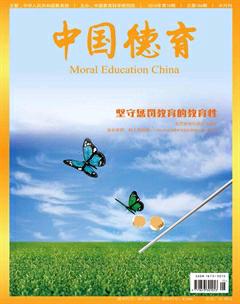一幕勝千言:不可被忽視的教育場域
韓國電影《釜山行》講述了單身父親石宇,為滿足女兒秀安回到媽媽身邊的心愿,帶其搭上開往釜山的列車。殊不知,在他們踏上列車的同時,被病毒感染的喪尸也進入了車廂。只要被喪尸咬到,人會立刻變為行尸走肉,由此,病毒在列車內迅速傳播。石宇為保護女兒平安抵達目的地,一路上想盡辦法。在即將到達釜山之時,石宇不幸被喪尸咬到,感染病毒。最終,為了確保女兒安全,石宇犧牲自己,跳下火車。
一、教育場域的特殊作用
(一)教育場域與教育環境的不同
在談及教育場域的作用前,我們必須區分教育場域與教育環境兩個概念的不同。教育環境包括物質環境和精神環境;教育場域囊括整個區域中的所有人事物。兩個概念看似都是在強調一定區域內的周遭情況,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教育場域擁有特定的教育行為,而教育環境往往缺少這一特定的行為,更加強調外部環境對于身處其中的人的一系列作用。
有學者有不同意見,認為在學校的教育環境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教育行為。其實,因為學校是特殊場所,它的很大一部分職能就是開展教育活動,因此不能包含在常規的場域和環境中。影片《釜山行》中,在物質環境方面,周圍充滿僵尸的車廂,給身處其間的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危機感;而在精神環境方面,幸存者們聚集在一起表達出的情緒通常是焦急、憤怒、悲傷等負面感受,無形中讓車廂內的人們感到壓抑。這些環境都沒有明確的教育目的和教育行為。而教育場域則是更加凸顯在整個區域內的所有人事物,包括實施的教育行為,給每一位身處其中的人帶來的影響。在教育場域中,一般都會有可以發掘的教育情節。
正如古語所說“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環境對于人們是有著重要影響的,無疑,任何特定的教育場域對于人的影響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教育場域對人的影響,并非像教育環境那樣溫和、循序漸進,從一定意義上講,教育場域對于人的影響是更立竿見影的。
(二)教育場域的強大力量
在教育場域中存在著特殊的情節和故事,這些情節和故事一旦發生,只要你身在其中,不論你是否采取教育行為、運用教育手段,在該場域中的各位就都已成為了這一事件中的主人公。當然,每個人吸收到的教育內容是大不相同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教育場域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被教育者,而那實施教育的主體就是教育場域本身。
《釜山行》影片中,幸存者從“大田站”再次上列車的時候,未被感染的人群遭到了喪尸的攻擊,分散上了不同的車廂。石宇救下散在其他車廂的女兒,歷經千辛萬苦抵達了大隊人馬所在的車廂。但當和大家匯合后,石宇一行人卻被認定已經被感染病毒,受到了眾人的驅趕和辱罵。
在這種情境中,女兒不停地哭泣仿佛也在證明著,她已經明白了父親的話:“在特殊時期只要照顧好自己就可以。”他們一行人被趕到另外的車廂,石宇只說了一句話:“秀安,請放心,爸爸一定會把你送到媽媽身邊!”隨即,女兒也終于有勇氣表達出對于石宇的情感,因為她害怕再也見不到爸爸。石宇曾經一再希望讓自己的女兒有能夠表達自己的能力,也曾經一度想讓自己的女兒學得自私一些,不過,那些冷冰冰的說教和石宇的身體力行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在這節充滿“殺氣”的車廂中,石宇沒有采取任何教育手段,也沒有講出任何說教的語言,女兒卻擁有了能夠表達自己的勇氣,學會了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這一幕,讓他感到非常暖心。當然,在這位父親心中,他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實施了特定的教育行為,表面上看,他也沒有采取任何教育手段。其實,這一特定的教育措施產生的影響和作用的主體不是來自于父親本人,而是來自于父親和女兒身處的這一場域。
在新車廂中,秀安沒有任何臺詞,但是卻一直在哭泣。石宇也僅只有很少的臺詞,只是臉上的表情讓人難以言說,畢竟他們剛剛經歷了極其殘忍的一幕:好不容易和未被感染的人們匯合,卻被殘忍地拒之門外!構成這一教育場域中的主體正是車廂中的大人們:在上車混亂時,秀安執意要把座位讓給他們;在得知有安全地帶后,秀安第一時間要告訴他們。秀安曾經認為他們是善良純潔、互愛互助的。可是這些人,現在因為自私,要將包括他們父女在內的這一行人趕到更加危險的車廂。在這受盡委屈的場域中,小女孩沒有和任何人發生言語和行為上的互動,也沒有人對小女孩實施某些特定的教育行為,由此我們有理由排除這些人為因素。誠然,我們不能否認環境給予小女孩的某些特殊作用,諸如那些如同廢墟般到處沾滿喪尸血的車廂,可是,這一環境對于小女孩的影響和作用是有限的,但當那些人為因素和特定環境結合到一起時,產生的這一教育場域,它的作用就遠遠大于這兩個因素單獨的相加。
事實上,教育場域并不是簡單地將某些特定的教育環境,與一些人為活動因素相加產生的。當我們去定義“教育場域”的時候,教育環境和人為因素是兩個不能忽略的重要部分。構成教育場域的另外一些要素,逐個單純的相加,其產生的作用無法逾越場域自身的強大作用。有一個形象的公式,若教育場域中有“N”個要素,每個要素的作用或影響力為“1”的話,那么“1+1+1+……+1 二、教育場域中兩種身份的互換 (一)教育場域的范圍與對象 劉生全在《論教育場域》一文中,認為作為一種客觀性社會存在而言,教育場域系指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參與者相互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以知識的生產、傳承、傳播和消費為依托,以人的發展、形成和提升為旨歸的客觀關系網絡。可以把場域設想為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場域的效果得以發揮,并且,由于這種效果的存在,對任何與這個空間有所關聯的對象,都不能僅憑所研究對象的內在性質予以解釋。 簡言之,教育場域是一切發生教育行為的場所,同時,在這一區域中的所有一切事物,無論其是否具有生命特征,都是構成這一場域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教育場域的范圍具有可塑性,封閉和非封閉的教育場域在現實的教育現場都是存在的。例如,影片《釜山行》中,在一節節車廂里發生了教育行為,那么在這一封閉環境中的各類人事物,就構成了明確的教育場域。另外,開放性強的教育場域也是常見的,試想在街上,我們看到一位母親正在教育孩子,無論是說教或是其他教育方式,作為路人,我們雖不是特定的被教育對象,但是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也會被這位教育者傳遞出的教育目的和實施的教育行為所影響。
(二)教育場域中的教育者與被教育者
在任何教育場域中,人們很難說清到底何種行為的產生將被界定為教育者或被教育者。那些實施教育并且對他人產生影響作用的人,通常被我們理解為教育者;而被教育者,就是那些實施教育的對象和被影響的人。但是就處在相同教育場域中的每一個人來說,你既可以被定義為“教育者”,也可以被定義為“被教育者”。
在影片當中,由于情況緊急,旅客們在轉移車廂的過程中,女兒秀安看到了一名年邁的老奶奶,因為膝蓋的疼痛無法站立。秀安看到此景,毫不猶豫地起身將自己的座位讓給了這位老奶奶。石宇雖在一旁默不作聲,但在轉移到另外一個車廂后,告訴自己的女兒,非常時期不必顧及他人,照顧好自己就可以了。秀安對此無法理解。接下來,當列車即將到達中途車站“大田站”前,石宇與朋友閔大尉通電話,得知了內部消息:一定不要跟著人流去主廣場,否則將被隔離。就在石宇帶著女兒從下火車的人流中單獨行動時,女兒從一個聽到石宇電話的流浪漢口中得知,爸爸帶她去的地方才是安全的。此刻,女兒的第一反應,并不是石宇在列車上教育的那樣“只要照顧好自己就可以”,女兒大喊道:“我要趕快去告訴其他人!”當然,石宇不由分說地反對了女兒,并持續告訴她那句“真理”。
石宇教育女兒特殊情況下只要顧及自己,這顯然是發生在列車上的教育行為,通常我們思維中的父母與孩子的教育活動大多是發生在家中,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室外的某些場域中開展的教育活動。教育場域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是可以發生在任何環境中的。
在以上的兩個情節中,最直觀的界定便是,石宇作為教育者在教育女兒。表面上確實如此,但被明顯定義為“被教育者”的女兒對于父親石宇就沒有任何影響嗎?當列車再次開動,為了讓幸存者成功轉移到安全的車廂,必須要將與僵尸相鄰的屏蔽門牢牢關死。冒著被喪尸咬到的風險,第一個沖上去的就是石宇,而這一行為的源動力就是在前面情節中,小女孩對于父親隱形的教育行為:在危機時刻,要考慮他人多一點!
在某些特定的教育場域中,表面上,看似是某些教育者對被教育者實施著教育行為,但是當這種顯性的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價值觀念發生分歧時,被教育者會對教育者產生一種隱形的作用。在這種作用下,顯性教育者的身份就會發生轉變,同時顯性的被教育者也不再是那個被動灌輸的角色。
【王朝,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黃蜀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