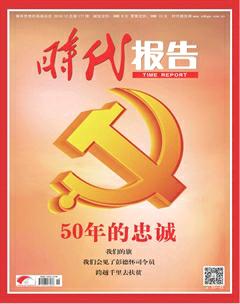我們的旗
李佩甫
編者:11月11日,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聯(lián)原主席南丁先生因病去世。南丁是新中國成立后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作家,是河南當(dāng)代文學(xué)60多年發(fā)展歷程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親歷者和領(lǐng)導(dǎo)者之一。南丁的小說語言簡潔、沉穩(wěn)、樸實而又閃現(xiàn)著智慧的光芒。他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但尋求以文學(xué)的方式進行表達,以老到的敘事、扎實的細節(jié)和鮮活的人物來表現(xiàn)作品的主題。小說之外,他的創(chuàng)作還涵蓋幾乎所有的文體,特別是其散文和隨筆,往往在不經(jīng)意間顯示出其深厚的文字功底、通達的人生智慧、開闊的個人胸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河南省文聯(lián)主席楊杰這樣評價他:“作為河南文藝界的一面旗幟,他用獨特的方式和這個世界告別,為自己精彩的一生完美收官,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就是他——南丁,一個成就斐然的文學(xué)大家,一個積極有為的文藝界領(lǐng)導(dǎo)者,一個睿智幽默、可親可敬的老人。”
他走了。
走得很平靜。很安詳。也很決絕。他走后,我們曾希望他能給我們托一夢,沒有。他不愿打擾任何人。可我還是看見他了。我看見他在空中飄揚。
他在病床躺了五個多月,在北京301醫(yī)院做了大手術(shù),幾乎切開了半個胸腔。可他一直在走,一直到他走不動的那一天。問他疼么?他搖搖頭,說:不疼。
他是安徽人,1949年背著行囊來到河南。在河南生活了66年,在河南省文聯(lián)大院里行走了60余年。自上世紀50年代起,他的作品《檢驗工葉英》《何科長》《良心》《被告》等就聞名全國,為此參加過全國的群英會;80年代以來,他的作品《旗》《尾巴》《兩個短暫一生的編年史》等作品,被文壇稱為開了中國反思文學(xué)的先河。可在這個大院里,無論年老年少、不分老幼尊卑,都稱他為“南丁”。既如說他當(dāng)了河南省文聯(lián)主席、黨組書記之后,人們?nèi)匀环Q他“南丁”。有了問題,人們說:“找南丁。”有了意見,人們說:“找何南丁。”于是,文聯(lián)先是有了專門接待作家的“客房”,后來又有了招待所、食堂、浴池,等等。記得有一次,農(nóng)民作家喬典運從南陽來,我們在省文聯(lián)的招待所里神聊至夜半,聊激動了,老喬說:“我去給南丁說。”當(dāng)夜就推開了南丁的家門。那時候,南丁的家門幾乎24小時對從下邊來的作者開放。凡有作者從下邊來,有什么要求,會自豪地說:“我跟南丁說了。”那就是這個大院的“通行證”。他的微笑,成了一個時代的標(biāo)志。
1980年,作為一個年輕的業(yè)余作者,我有幸參加了一個河南文聯(lián)舉辦的文學(xué)研修班。在這個班上,我們的輔導(dǎo)員作家徐慎先生告訴我說:“南丁想見你。你去見見他。”那時,我有點傻,羞于見他。我一個工人出身的青年,南丁在我眼里是“高山仰止”。過了一段,徐慎先生問我:“見南丁了么?”我嚅嚅地搖了搖頭。他說:“去。你怕啥,去見見他。”可我自覺沒寫出什么像樣的作品,還是羞于見他。一個月后,徐慎先生再問:“見南丁了么?”我很為難地說:“我,不好意思。”徐慎先生即刻說:“張斌,你領(lǐng)佩甫去見見南丁。”于是,當(dāng)晚老大哥張斌帶著我去文聯(lián)家屬院見了南丁先生。這天晚上,由于緊張,我已不記得自己都胡說了些什么。好像南丁也沒怎么說話,就那么默默地坐著。第二天,在一座談會上,南丁手里提一黑包,慢悠悠地走來,把我從座談會上叫出去,遞給我了一張“調(diào)干表”,說了兩個字:“填填。”此后,我就成了參與籌辦大型文學(xué)期刊《莽原》的四個青年編輯之一。
在那個時期里,受到南丁先生關(guān)照的并不是我一個人。先后調(diào)入的專業(yè)作家有楊東明、張一弓、張斌、鄭彥英、張宇、田中禾、齊岸青、孫方友。還有很多很多……也就不一一列舉了。翻開改革開放后的河南文學(xué)史,就知道先生作為“文學(xué)園丁”的高瞻遠矚了。
在改革開放之前,河南文學(xué)在長篇領(lǐng)域里幾乎是個空白:30年只有一部半長篇(據(jù)說一部是《黃水傳》,半部是當(dāng)時沒出版的《差半車麥秸》)。南丁先生可以說是當(dāng)之無愧的河南文學(xué)改革開放后的奠基者。作為河南大型文學(xué)期刊《莽原》的籌辦人,當(dāng)年南丁先生曾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拉起一支中篇創(chuàng)作隊伍,為河南的長篇創(chuàng)作打好基礎(chǔ)。”也是在這個時期里,河南最美的避暑勝地——雞公山一號樓(那是雞公山上一棟風(fēng)景最好的別墅),河南省文聯(lián)包了十年。那是專門給作家、藝術(shù)家改稿子、開作品研討會用的。于是,河南省文聯(lián)有了七家供作者發(fā)表作品的刊物,有了一支四代同堂的文學(xué)豫軍,有了每年上百部、集作品的涌現(xiàn)。
南丁先生退休后,仍是河南文學(xué)的“定海神針”。先生一直積極地參加各種文學(xué)活動,常幽默地稱自己為“八○后”。他笑瞇瞇地往會場上一坐,會議的氣氛就格外活躍、生動、熱烈。
南丁先生走了。先生活得尊嚴,走得尊嚴。
南丁先生走了。他走向了大海。中原文壇痛失一代大纛,寫下這些文字,何依?何依?我哭我疼。
南丁先生走了。這預(yù)示著一個文學(xué)時代的結(jié)束。那么,也或?qū)㈩A(yù)示是一個新的文學(xué)時代的開始。
愿南丁老師一路走好。上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