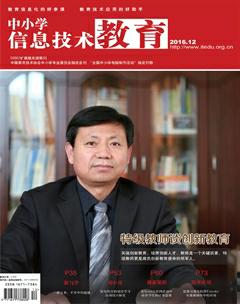神秘的自然博物館探尋之旅
說起博物學(xué),《辭海》里說,博物指“能辨識許多事物”。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博物的解釋是,“舊時對動物、植物、礦物、生理等學(xué)科的統(tǒng)稱”。縱觀自然科學(xué)史,曾出現(xiàn)過許多著名的博物學(xué)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文藝復(fù)興時期的達·芬奇、近代的達爾文。
雖然達·芬奇在繪畫、物理、生物方面有著卓越的成就,拿當下時髦的詞來形容,他是一個“跨界”的科學(xué)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博物學(xué)家。由此可見,博物學(xué)是一門古老的學(xué)科,許多現(xiàn)代學(xué)科都是從博物學(xué)中劃分出來的。而對于孩子們來說,大自然充滿著神秘和魅力。重溫博物學(xué),與大自然親密接觸,進行探究和探索,是一件充滿魅力的事。
然而,博物學(xué)包羅萬象,涉及諸多學(xué)科,應(yīng)該如何入門?項目制學(xué)習(xí)是一個好的選擇。從興趣出發(fā),通過項目設(shè)置和任務(wù)的完成來達到學(xué)習(xí)目標。特別是,有很多場館,比如自然博物館、動物園等,是孩子們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們學(xué)習(xí)的好機會。
楊曄老師就是一個博物學(xué)“達人”,大學(xué)時就已成為《中國國家地理》的青少版——《博物》雜志最年輕的專家顧問。經(jīng)人推薦,他參加了 BBC紀錄片《美麗中國》的攝制。如今,楊曄在開發(fā)更多的自然教育課程,如生物探索課系列、地球探索課系列、宇宙探索課系列、菜市場博物學(xué)系列等各類博物科普服務(wù)。他試圖把公益性的科普活動改造成趣味與知識、旅行結(jié)合的教育經(jīng)營模式。
同時,對于不能夠抽出大量時間跟隨像楊老師這樣的博物學(xué)“達人”走進大自然、走進場館的學(xué)生們來說,如果可以利用在線資源和AR技術(shù)體驗一下“身臨其境”的感覺,那將會極大普及博物學(xué)的學(xué)習(xí),增強學(xué)習(xí)體驗。設(shè)想一下,如果學(xué)習(xí)變成來一場尋寶、探險的游戲,豈不是更加有吸引力?
由此,上海喵爪決定做一個大膽的嘗試,利用自行開發(fā)的西游Go AR 社交游戲,將其與自然博物館等場館相結(jié)合,通過楊老師的博物學(xué)設(shè)置及體驗,讓孩子們通過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平臺或場館資源,學(xué)習(xí)博物學(xué),感受大自然真實世界帶來的樂趣。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一個Field trip游學(xué)項目:自然博物館探尋之旅。
這將是一個游戲化教育的典型應(yīng)用。
把找到并學(xué)習(xí)辨識出相應(yīng)的植物作為完成任務(wù)的一個標志,完成一項即可以通過掃二維碼進入到下一輪,直到完成所有的任務(wù)——這就是游戲通關(guān)制。完成任務(wù)可獲得獎勵,完成關(guān)卡的孩子們可以領(lǐng)取他們的專屬妖怪或其他形式的獎勵。孩子們可以獨自一人,也可以與班上同學(xué)或是其他學(xué)生一起去玩“playlist”,共同探尋目標,學(xué)習(xí)相關(guān)知識。
這將是一場開在自然博物館的課程,也是一場社交游戲。孩子們在興趣的引領(lǐng)下,以游戲的方式,到自然界、博物館里開展關(guān)于博物學(xué)的親身體驗,相信這將是一次無與倫比的價值體驗。
正如世界知名博物學(xué)家E.O.威爾遜所說,博物學(xué)“可以是從山巔上眺望的一片森林狹長的遠景,可以是圍繞在城市街道兩旁的一片雜草,可以是一頭鯨魚躍出海面的剪影,也可以是淺塘里水藻上長出的茂盛原生物”。身邊的博物學(xué)無處不在,興趣是最好的老師。讓孩子們在興趣的指引下,帶著對神秘大自然的好奇心,以游戲通關(guān)的方式,完成博物學(xué)的學(xué)習(x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