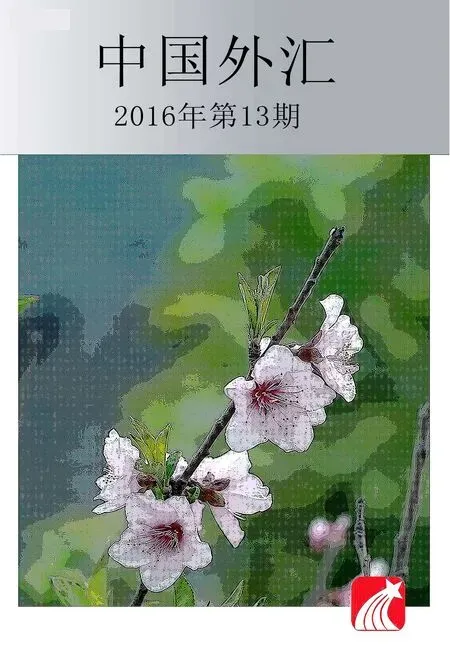闖關金融衍生品市場
文/董澤宇 編輯/丁小珊
闖關金融衍生品市場
文/董澤宇 編輯/丁小珊
企業在進行衍生品交易時應注重風險控制,從治理結構、激勵手段和風控能力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以真正發揮其平滑市場價格、規避風險的作用。
在現今的國際市場中,金融衍生品已經滲透于多種影響力極大的商品和服務當中,如國際信貸的資金成本就部分取決于利率衍生工具和信用違約互換,國際能源價格變動也受制于石油和天然氣的衍生金融工具。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持續推進,中國企業國際化程度也在逐漸升級。面對國際市場價格日益加劇的波動,“走出去”的企業對衍生品的作用應更加重視。
國際市場的開放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條件,但由于衍生品業務的風險控制手段屢屢失效,企業難以取得預期的收益,甚至可能要面臨投機行為導致的金融敗局。企業如何從風險控制的角度,分析工作失效的深層原因,進而強化對衍生品業務的監管,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對衍生品的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需要強有力的治理層參與。從風險導向型審計的角度來看,衍生品風險具有突發性和難以控制的特征,一旦風險事件發生,企業除了被迫履行合約很難有其他的選擇。這意味著事前風險防控的意義遠遠超過事后的風險應對。而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是風控手段有效運行的前提之一。巴林銀行危機是最著名的衍生品投機事件之一。該行交易員尼克里森突破層層監管,大量投機日經225股票指數期貨合約,最終造成9億美元衍生品交易損失。這一巨額虧損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雖然審計機構曾多次就異常情況提示治理層注意,但最終都不了了之,甚至在風險暴露的當年,公司高層仍然向其賬戶撥備大量保證金款項,最終導致銀行破產清算。回顧衍生品風險案例,治理層缺位的現象比比皆是,嚴重破壞了企業的風控環境,且一旦治理結構的權力過于集中,則風控措施很可能形同虛設。這是因為,在不注重風險控制的經營層手中,衍生品往往被用于杠桿投機。例如在中航油事件中,就是由于公司領導層獨斷專行進行境外石油衍生品投機而釀成巨虧;中信泰富經理層也是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進行了巨額金融衍生品交易。
為應對此類風險,首先,公司董事需要更新知識,積極參與衍生品業務管理。對于衍生品業務,企業治理者應該提出兩個問題:各種情況下衍生品組合可能虧損多少?最有可能虧損多少?回答這些問題并不易。第一個問題通常需要借助壓力測試,第二個問題則需要通過更為復雜的風險價值模型進行測算。公司董事雖然無需事必躬親,但在明確風險戰略時必須克服技能短板,建立明確的風險管理指導方針。其次,董事會應當強化對風險控制部門的管控。建議相應的部門負責人應由董事會專門委員會進行任免和管理,并直接向董事會負責。同時,治理層應當將衍生品風險敞口當做經理層考核評價指標之一,并要求衍生品交易部門的負責人定期在董事會上對衍生品交易情況進行匯報。
合理化激勵手段
企業的激勵制度是引導企業發展的風向標,但如果激勵手段不合理,則會成為誘發投機行為的直接原因。其主要表現在投資目的上以投機獲利取代了套期保值,因而在金融衍生品品種選擇方面不夠科學謹慎,以及在企業內部風險控制制度層面管理失效。追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公司的薪酬激勵制度沒有起到引導企業管理層控制風險的作用。而在鼓勵冒險的激勵制度下,往往會產生非理性行為,如果缺乏懲罰管控措施,更會使經理層在風險承擔上有恃無恐。
不合理的激勵手段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在獎勵投機者。日本殼牌昭和石油公司曾買入合約金額為64億美元的遠期合約規避匯率風險,但該公司當時正常經營情況下美元匯率的風險敞口僅為9億美元。最終,由于匯率波動釀成該公司巨額損失,且大部分損失與風險規避毫無關系,而是由純粹的投機活動引起的。事實上,該公司的外匯交易部門在遭受外匯損失時不僅沒有及時止損,反而大大增加了交易量,希望豪賭一把從而挽回損失。但最終事與愿違,釀成事故。交易部門甘冒風險的最大動機正是來自于企業過分偏好風險的激勵制度,而專注利潤忽視風險控制也正是投機行為難以抑制的原因。
為避免這種權責上的不對等給風險控制工作增加負擔,企業應合理設計激勵手段。第一,對衍生品業務的不相容職務,應當嚴格進行分離管理,相應,對不相容職務的匯報對象也要充分進行隔離。風控部門應越過管理層直接向董事會負責,這可以從根源上為風控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二,無論是盈利性投資業務或套期保值業務,在設置員工的激勵標準時都不應僅僅考慮交易的經濟收益,而是應當將風險敞口的變化也列為重要的評價標準,充分聽取風控部門對衍生品交易情況的獨立意見,在激發員工積極性的同時管控風險。
創新風險管理方式
在控制金融衍生品風險的過程中,傳統的財務管理往往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在表外負債的確認方面。以規避美元升值風險的不同方法為例,使用貨幣市場避險法會在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為人民幣借款和美元存款,而美元期權交易則會在利潤表上顯示為期權的成本;但如果交易部門采用遠期合約規避風險,以規避會計部門的檢查,則不會在財務報表上留下痕跡,并會導致無法追蹤。在虛擬經濟大力發展的當下,表外負債很大程度上成為企業利用某些創新性的手法規避會計監督的投機行為。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如各種奇異期權的使用,給相關的審計工作增加了難度,也是風險控制手段難以生效的原因之一。
同時,衍生品價值的確定也是監管面臨的難點。對一般金融工具來說,資產的公允價值與潛在風險是相對應的。而對于金融衍生品而言,由于杠桿的存在,他們產生的潛在收益或損失可能遠遠大于其在計量日的名義價值或公允價值。因此,僅依靠披露二者進行估計是不準確、不可靠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會引起誤解。企業對表外負債風險的發生以及風險程度大小是難以預測的,因而當風險實際發生時,往往會超出企業的控制范圍,對企業造成意想不到的打擊。
鑒此,在量化衍生品風險的過程中,不應該只考慮金融工具的面值或市場價格,而應當關注衍生品的風險敞口。通過對衍生品工具的在險價值測算,可以較為準確地衡量衍生品在一定概率下可能給企業造成的損失限度。同時,應當就相關風險的重要指標形成風險預警體系,定期監控風險規模,并結合企業自身條件進行壓力測試,將風險規模限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避免風險失控。
發揮套期保值的避險作用
套期保值的目的是利用衍生品市場上的收益去平滑現貨市場的波動。然而,刻意的放松交易紀律,或是管理不嚴導致錯誤的交易決策,都可能放大交易風險,從而給企業造成巨額損失。在眾多風險案例中,投機行為往往以套期保值作為掩護,兩者之間模糊的界限,很容易成為風險控制的盲區。
連接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重要環節是衍生品對沖比率的確定。適當的對沖比率可以達到套期保值的目的,而在高收益的誘惑下刻意扭曲對沖比率則會形成投機。在中信泰富的案例中,對沖在澳洲鐵礦投資的匯率風險僅需要18億左右的澳元衍生品就可以達到目的,但是其簽訂的外匯合同涉及的金額卻高達97億澳元,已經遠遠超出了套期保值的需要,投機的動機顯而易見。
要真正發揮套期保值的避險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企業要重視對沖期限的配比,做好風險防控。在德國金屬公司的案例中,由于采取“一對一”式的對沖策略,使遠期的石油空頭頭寸總額與近期的期貨合同多頭頭寸總額對應,造成多頭和空頭頭寸的期限嚴重不符。這種過猶不及的對沖策略使公司面臨的石油價格風險大大增加,使計劃中的套期保值行為變成了投機行為。
第二,要考慮套期保值商品現貨的變化情況。金融衍生品與其基礎產品間存在著聯動關系,基礎產品市場的任何細微變動都會通過杠桿作用在衍生品市場上成倍放大。如果從業人員在套期保值的過程中不考慮現貨形式,而一味地堅持計劃數量,很可能導致投機行為并帶來風險。
第三,在風險控制的過程中,不能把衍生品業務看作單純的交易行為或是財務行為。任何套期保值策略有效的前提,都是將其與企業經營業務密切關聯起來。在確定對沖比率和配比期限時,應當采取集體決策的形式,充分考慮公司經營現狀并尊重生產部門的意見,讓衍生品工具真正發揮套期保值的功能。
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衍生品業務承載著企業對沖風險的良好愿望,然而不恰當的風險控制反而會使其形成更大風險。對于剛剛接觸相關業務的企業來說,在不具備良好的風險控制環境、欠缺風險控制能力的情況下,貿然大規模接觸衍生品業務,其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對于相關的風險控制建設絕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而應該深挖內在的因素,從治理結構、激勵手段和風控能力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尤其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伴隨著對國際市場的了解逐漸深入,更應當慎重對待衍生品業務。只有科學地進行風險管理,才能使這柄“雙刃劍”不傷害自身,在國際化的進程中走得更穩。
作者單位:國家開發投資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