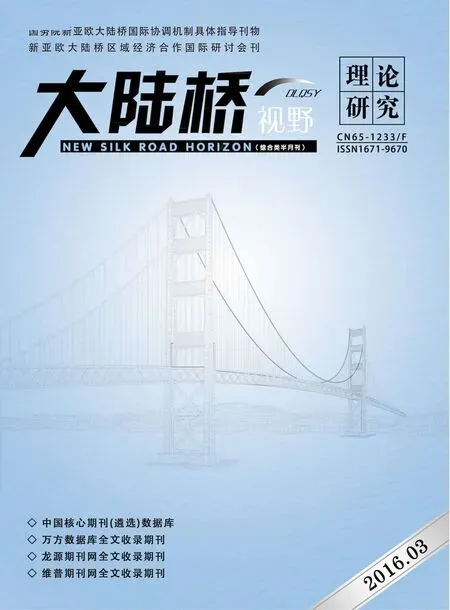從闡釋學角度淺析歸結論對“文化派”的誤解
尚靜雅/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
?
從闡釋學角度淺析歸結論對“文化派”的誤解
尚靜雅/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
【摘 要】在翻譯研究領域從語言研究層面進入文化研究層面的時期,文化學派為翻譯研究帶來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春風”,為翻譯學的發展注入一股新鮮的血液。與此同時,代表語言研究學派的翻譯歸結論認為文化派脫離了文本,極大限度的挑戰了傳統翻譯價值觀。該文從闡釋學角度針對歸結論對“文化派”的翻譯觀擯棄一切制約翻譯行為的規范的誤解進行分析。
【關鍵詞】誤讀的合理性;歸結論;“理解的歷史性”;“視閾融合”
國際翻譯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初,由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層面轉入了文化研究層面,使研究從文本內轉向了文本外。正當文化派在翻譯研究領域轟轟烈烈發展之時,歸結論的相關學者對其提出了質疑與批評。但即便如此,筆者對其認為文化學派脫離文本,間接支持了“亂譯”這一看法有些不同的理解。以下就從闡釋學角度進行分析。
一、關于闡釋學中的“理解的歷史性”和“視閾融合”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歷史的,理解的歷史性又構成了理解的偏見,進而決定了理解的創造性和生成性(1992)。正所謂“詩無達詁”,不同的讀者由于個人閱歷、所處環境和文化的不同,再加上個體本身的差異性,對同一首詩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體驗。但這并不意味著該詩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可能,只是對于不同的讀者它呈現了不同的意義,其他存在的可能相對處于隱形狀態。人是歷史的存在,有其無法擺脫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局限性(張德讓 2001)。譯者首先是原文的讀者,在自身理解上就會有不同的見地。其本身不同的“前理解”就預示了文本意義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性。其次,譯者作為原文的“代言人”在向譯語文化讀者解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在其翻譯中帶有個人理解,或許在無意之間便導致“誤讀”“錯譯”。 其次,譯文的讀者在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上不免又會結合個人“前理解”生成第二次“誤讀”。 甚至,有些讀者(包括譯者)對作品理解是原作者在創作之初都沒考慮到的,但卻助成了翻譯作品的成功,使之獲得新的價值。在伽達默爾看來,根本就無所謂歷史的真面目,理解不是一個復制的過程,理解者總是帶有自己的偏見,并充分肯定了偏見對理解的意義,認為正是這種“合法的偏見”構成了理解的歷史性因素(Munday Jeremy 2001)。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總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無論是理解者本人,還是理解的對象文本,都處于歷史的發展演變之中。這種歷史性就使得對象文本和闡釋主體都具有各自的處于歷史演變中的“視閾”,因此,理解不是簡單消極的復制文本,而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腦力勞動(張德讓2001)。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視閾,而理解者具有現今的具體時代氛圍中形成的視閾。兩種視閾之間存在著各種差距,這種由時間間距和歷史情境變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無法消除的。伽達默爾認為,“人類生活的歷史運動在于這個事實,即它絕不會完全束縛于任何一種觀點,因此,絕不可能有真正封閉的視閾”。因此,翻譯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兩種視閾的碰撞與磨合,形成新的視閾,亦或者是一種視閾對另一種視閾的取代(1992)。由伽達默爾的觀點看來,作品的重譯很有必要性。重譯不意味著過去的譯作就是毫無價值的,只是隨著歷史的發展,理解者的視閾有了新的變化,譯者需要讓原作的視閾和具有時代氛圍的新視閾之間做出新的碰撞,創作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譯作。
二、歸結論對誤讀合理性的誤解
前面在“理解的歷史性”中談到了翻譯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些“誤解”“誤譯”。關于誤讀的合理性,難免使人誤解,和“亂譯”搞混。歸結論針對“翻譯即改寫”“翻譯即操縱”對文化派提出質疑,認為“文化派”的翻譯觀擯棄一切制約翻譯行為的規范,“隨便怎樣搞都行”,將誤讀的合理性主觀化降低了門檻,對其翻譯實踐的活動本質提出了質疑,認為“他們(文化派)從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等方面論述文化對翻譯的制約關系,認為翻譯從選材到發揮作用都受到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詩學、審美取向和譯者、讀者、評論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以及我們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著作用。文化派的這一判定本身無錯,卻不是科學的判定,只是簡單的經驗歸納(趙彥春 2005)。”
三、闡釋多元性的合理性
其實從闡釋學角度來看,以上觀點不過是對闡釋多元性置換了闡釋有效性觀點的認同。但事實上伽達默爾是主張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本身的主題上,即把精力集中在文本對后來的闡釋者所表達的意思。
他認為翻譯首先是一種哲學解釋學對話,它是譯者與文本的對話,而不是譯者與作者對話。對母語文本的閱讀理解解釋同樣也是對話,但惟有對外語文本的閱讀理解才更好的體現了對話的性質。文本始終是譯者的出發點,本質上是區別于其他文本的。如魯迅曾說過“(一部)紅樓夢單是命題,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了《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1981)。盡管不同的譯者由于自身的“前理解”對《紅樓夢》的命題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認這些命題來自《紅樓夢》而非《三國演義》或是《西游記》,這些命題都是對《紅樓夢》的理解,但由于自身無法擺脫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局限性,對其的認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能否認其在本身特殊性和局限性領域的有效性。而文化學派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即結合不同的前理解,對原文本給予了新的闡釋,這些譯本都是原文本的一個側面,沒有任何一個版本和原文本等同,但同時也豐富了原文本。文化派所強調的是應當充分認識到譯者及其譯入語文化的有限性,在具體研究當中不能忽略這些客觀事實,同時,并不否認原文本的價值。筆者個人以為,文化派探索的是影響翻譯的各種因素對翻譯造成的客觀影響,及其在具體操作中是如何影響的,這些是研究“如何譯”的基礎,只有認識到這些因素各自的“威力”才能更好的指導我們的翻譯研究。
“理解的歷史性”使得譯者在翻譯過程不可避免存有一些個人的偏見,但不能就此全盤否認了譯作本身的價值。這些“誤讀”為翻譯工作者對研究翻譯學提供了多種研究視角,任何一種都具有其獨特的價值。而“亂譯”則是毫無價值可言的,不能因為擔心“亂譯”現象的出現而主觀違背事實發展的規律,使其成為逃避多元化的借口,束縛住譯者的創造性。
現在的理解會變作未來的“前理解”,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也并非靜止不變的,所以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更新的。理解者的“視閾”也在這個過程中時刻變化著,因此新舊兩個“視閾”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碰撞著,形成新的“視閾”。但是,一些作品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結合時代的要求給予重新翻譯不意味著曾經的譯本就是錯誤的。這種過去發揮一定價值的“誤讀”、“誤譯”是應當給以充分肯定的。不同的文本需要隨著時代所需做出相應闡釋,這并非毫無價值的“亂譯”(張寧寧 2010)。魯迅在《非有復譯不可》一文中曾強調了重譯的必要性,他認為即便是有好的譯本也需要重譯。比如20世紀50-70年代,《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大陸被視為是禁書,因此那時的譯本著重表現的是資本主義潦倒的一面,其中有大量奢侈舞會場景的描寫以及青年一代追名逐利等描寫,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9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重譯本,此時人們對其的態度大有不同,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對蓋茨比的經歷感同身受,從而對其十分推崇。50-70年代的譯本在90年代讀者看來或許是可笑,甚至不可理解的,但在那個時代的確為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相應的貢獻,不能武斷地否認曾經譯本的價值,要結合其所處的文化背景予以考慮(孫毅鴻 2010)。
不管是由于個體差異還是時代變化產生的“誤讀”、“誤譯”都具有無可取代的翻譯研究價值,只有從這些成長的痕跡中才能發現翻譯學的客觀規律,促進翻譯學的發展。
此外,筆者以為倡導“百家爭鳴”,看似拓寬了作品合理性,但實則不已,這里的“改寫”不意味著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寫作,那些不具有研究價值的作品仍是不值一提。現如今的翻譯已不僅僅局限于以前傳統意義上的翻譯,如果說傳統的翻譯是為了達到最基本的溝通意義上的翻譯,那如今的翻譯就是隨時代進步的“個性化”的翻譯,而文化轉向也是應時代發展所需產生的。當然這個所謂的“個性化”并不是毫無規章的“胡譯”“亂譯”,任何“胡譯”“亂譯”的譯者未免也太低估了當代讀者的閱讀欣賞水平。作為翻譯研究者,觀察分析這背后的相關因素似乎比主觀上給翻譯規定一些條條框框要實際的多,只有掌握這些“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詩學、審美取向和譯者、讀者、評論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避免主觀隨意性,才能更客觀的掌握翻譯的規律。只有這些經驗性的信息歸納好,才能進一步規劃出科學的判定標準(謝天振 1999)。
四、結語
文化派在提出權力關系、贊助者、意識形態等方面,論述文化對翻譯的制約關系的同時并沒有否定原文本的價值,并沒有提倡“亂譯”,只是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視角,以便更好的觀察翻譯這一過程,從而更好的指導翻譯教程。闡釋學中關于“誤讀”“誤譯”對此給予了很好的解釋。但歸結論對此的質疑也是同樣具有價值的,它促使學者在學習研究的過程中要冷靜理性的看待研究領域中出現的新觀點,只有這樣才能翻譯研究的發展不脫離正軌。
參考文獻:
[1]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New York: Routledge.2001.
[2]胡適.建設理論集(導言)[C].1935.
[3]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4]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孫毅鴻.對《了不起的蓋茨比》多次重譯的評析[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6]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7]張德讓.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與翻譯研究[J].中國翻譯,2001(4).
[8]張寧寧.哲學闡釋學視野下的翻譯研究[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9]趙彥春.翻譯學歸結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
尚靜雅,女,1986年10月生,河南許昌人,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教師,研究生學歷,翻譯理論與實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