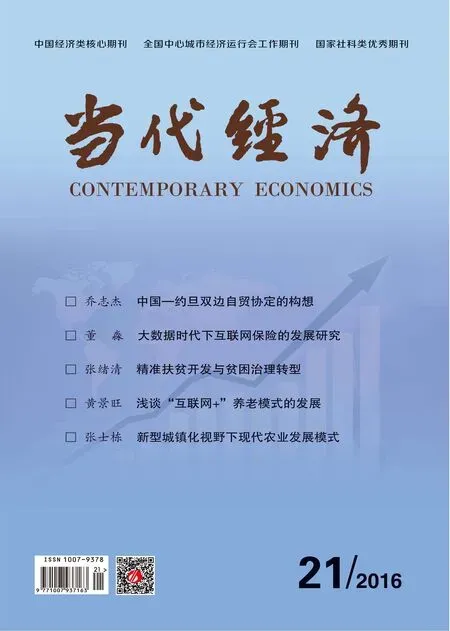農民利益表達研究綜述
萬紅斌
(武漢理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3)
農民利益表達研究綜述
萬紅斌
(武漢理工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3)
本文對國內外農民利益表達這一研究領域進行簡要的回顧后,把農民利益表達在研究路徑上歸結為注重表達策略與手段的資源/關系視角和傾向情緒表達的情感/意識視角;從農民利益表達如何上升到政府議程設置高度以及如何由個人表達轉向集體表達這兩方面來討論農民利益表達效果。
利益表達;資源/關系;情感/意識;政府議程
我國目前的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再加上農民本身作為弱勢群體,表達利益的方式有限,導致我國目前因農民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發。為此,對農民利益表達問題進行文獻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回顧已有研究基礎上,將從農民利益表達研究路徑以及農民利益表達效果兩方面對文獻進行歸納分析。
一、農民利益表達研究路徑
1、資源/關系視角
資源/關系視角在研究當代中國農民利益表達中具有重要地位,帶有明顯的經濟學研究取向,深受斯科特思想的影響。斯科特重點描述了東南亞農民采用諸如嘲笑、偷懶等小動作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資源/關系視角側重分析農民在抗爭中所運用的手段和策略。
裴宜理認為中國民眾通過抗爭表達利益的方式都是在遵守規則。李連江、歐博文兩位學者通過研究提出“依法抗爭說”。他們認為,農民是運用國家政策和法律維護自身經濟政治權益不受地方政府侵害,是一種政治行為。為了超越李連江、歐博文的“依法抗爭說”,于建嶸進一步提出“以法抗爭”。 “以法抗爭”是直接運用法律武器作為自己抗爭的手段,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色彩。但是,應星以“合法性困境”為邏輯起點,通過四個案例總結出“草根動員”的弱組織性特征和非政治化取向,直接批判于建嶸的觀點,即農民抗爭具有強組織性與政治性。應星也提出了“以氣抗爭”,認為利益沖突是農民維權的原發性基礎,“氣”是行動再生的推動力量。吳毅認為“合法性困境”的邏輯起點本身并不牢靠,它忽視了轉型中國政治特征的復雜性和過渡性,簡單化了行政權力和人際關系網絡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基于此,吳毅認為,農民利益表達之難以健康和體制化成長的原因,更直接歸因于鄉村社會各種既存“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的阻隔。董海軍在“以法抗爭”的基礎上發展出了“以勢抗爭”,認為弱者身份可以成為農民抗爭的一種資源。折曉葉研究了中國農民在本土非農化壓力、城市化暴力情況下所采取的利益表達策略,認為農民的表達手段是通過運用“韌武器”,即采取非對抗的方式來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
因為我國利益表達渠道的局限性以及農民本身資源的稀缺性,從“依法抗爭”到“以勢抗爭”往往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一個更適合農民自身情況的新的解釋框架——“以身抗爭”逐漸建立起來。王洪偉通過對艾滋病人抗爭行為的研究,發展出了“以身抗爭”,認為身體作為一種資源本身就可利用來表達利益。黃振輝的表演式抗爭,韓志明對“鬧大”現象的研究以及徐昕提出的“以死抗爭”都是“以身抗爭”典型。田先紅認為以往農民抗爭的研究沒有跳出農民弱者地位開展維權的范圍,他通過個案調查發現,農民牟利型利益表達開始凸顯。
農民除了通過“以身抗爭”動用內在資源外,還可以動員自身的關系網絡表達利益。吳毅認為,失地農民與基層政府官員本身就包含于一個復雜的人際關系網絡之中,在網絡中的人各自掌握一定的資源并且與其它成員之間以互惠的方式履行各自的義務,身處網絡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既躲不開又自覺運用這一資源。正是這一義務使得失地農民在表達利益時,可以動用各種資源和社會關系對其利益表達的客體——基層政府施壓。馮仕政認為一個人的經濟地位高,他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越大,表達利益的方式越有效,反之則選擇沉默。石發勇研究發現,不僅民眾善于調動自身關系網絡表達利益,地方政府也用關系網絡來動員民眾的支持,化解社會矛盾。
2、情感/意識視角
持情感/意識視角的研究認為,抗爭者之所以采取行動,不是出于怨恨、憤怒、就是出于責任感或自覺的倫理意識。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書中特別強調“生存倫理”對東南亞農民反抗的獨特重要性。李培林指出:利益格局變動確引發社會沖突數量的增多,但“利益變動本身尚不足以導致沖突行為的發生,由利益變動導致的不公平感和對現狀的不滿才是沖突行為產生的直接根源”。(李培林,2005)劉能從社會運動和集體行為的研究傳統中,綜合出了一個解釋框架,認為怨恨是都市集體行動的關鍵變量。何艷玲通過對城市經濟抗爭的研究發現,公平感、心理因素也是導致環境沖突的原因之一。如果把農民抗爭的情感因素歸于怨恨、不公平感,那么理性意識決定抗爭者采取何種行動。有學者認為,農民抗爭行為是理性的。當農民合法的權益受到損害時,其在選擇抗爭的方式時會考慮“成本-收益”,表現為抗爭過程中理性計算意識。在具體的抗爭方式上,相較于正規而繁瑣的法律抗爭,農民往往采用法律之外的抗爭方式,抗爭的結果取決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即使是極端的“以死抗爭”,仍然是基于理性考慮的,因為“局外人認為行動者的行為不夠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動者的本意,用行動者的眼光衡量,他們的行動是合理的。”(詹姆斯?S?科爾曼,1999)吳長青認為農民抗爭行動本身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策略范式的解讀范圍,其忽視了抗爭行動的道德邏輯與倫理因素。因此他將倫理帶入到農民抗爭的研究之中,認為: “倫理在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中國社會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更是中國農民抗爭行動的重要維度。”(吳長青,2010)
二、農民利益表達效果
1、議程設置
農民利益表達要想取得效果,必須使得其表達的問題被政府關注,進入政府的議事日程,而對問題界定便是進入政府議事日程,解決農民利益表達問題的第一步。弗蘭克與布萊恩認為人的偏好是固定但多維的,只要對問題做出不同的界定就能影響人們對事件的偏好,從而決定事件能否進入政府的議事日程。 “問題的定義形成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過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過程。”(詹姆斯?E?安德森,2009)王紹光根據議程提出者的身份以及群眾參與的程度不同區分出來六種類型的議程設置模式,總體可認為中國是自上而下的議程設置模式。但是,農民是社會抗爭的直接參與者,他們本身就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在定義社會問題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然而,與官僚、利益集團以及企業家等社會上層而言,農民由于受到知識水平、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們反而缺乏界定問題的能力。面對利益侵害,通過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不能有效地解決他們的利益訴求,他們往往通過向公眾和社會訴苦,展示其困境,表達內心的不滿與訴求。但是,一般的訴苦行為并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利益訴求進入政府議程是充滿競爭的過程,政府本身沒有足夠的時間、資源以及意愿去考慮其中的大部分訴求,只有競爭中獲勝的問題才能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因此,社會問題必須要通過焦點事件、指標、符號、反饋等來促使政府部門關注這些問題。格斯頓也認為社會問題進入政府議程需要“促發機制”,也就是一個重要事件,給政府產生壓力。就此而言,農民利益訴求要想進入政府議程,最快捷的方式便是激烈的個體或集體行動,在視覺上給公眾以沖擊,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從而增加政府解決問題的壓力。
盡管農民通過激烈的個人或群體性事件能夠自下而上的把利益訴求進入政府議事日程,但是解決問題的路徑依然是自上而下的。金登認為,社會問題進入政府議程并且能夠得到解決需要問題流、政策流以及政治流的結合,他稱這樣的結合點為“政策之窗”。當“政策之窗”被打開的時候,政策制定者以及參與者必須迅速采取行動,抓住時機以便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基于此,農民利益訴求的有效解決還必須等待政策的成熟,滿足政治需求的考量。
2、個體到集體的轉化
農民利益表達群體的規模會影響表達效果,集體的利益表達效果明顯會強于單個人的利益表達。但是作為個體的農民抗爭并不會自然轉化成集體抗爭。奧爾森認為,作為理性的個人,在采取行動前會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存在沖突,個人理性并不是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并且集體行動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在很多情境中,集體不行動才是自然結果。為了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奧爾森提出了兩種方式解決此困境,一是個體如不參與集體行動,便受強制;二是“選擇性激勵”。(奧爾森,1995)但是于建嶸認為奧爾森的“選擇性激勵”理論對于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解釋力不夠,為此他提出了“壓迫性反應”的觀點。他認為中國農民之所以維權抗爭,是因為“集團”外部“壓迫”超過他們忍受的閥值,而不是基于“集團”內部的“賞罰分明”做的選擇。鄧大才認同阿羅不可能定理,認為個人偏好只有在嚴格條件下才能加總形成集體偏好,而農民以家庭為行動單位,只有面臨生存威脅時,才會參加集體行動。
早在奧爾森之前,勒龐從心理學角度去解釋個人為何參與集體行動。他認為,只有形成了共同感情與思想的團體才能成為集體,集體心理支配著集體行動。因此,集體心理的形成過程決定集體行動發生的內在機制,而集體心理來源于人類共有的本能和情感。(勒龐,2005)基于此,國內文獻中也有通過感情心理方面去研究個人為何參與集體行動。郭景萍認為喚起參與者的情感認同是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黃嶺峻通過對農民工集體行動發生機制的研究后發現,只有通過共同意識的構建才能使個體不滿傳導為集體不滿,從而參與集體行動。
[1] 李培林等著.社會沖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2] 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層[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3] 吳長青.從“策略”到“倫理”:對“依法抗爭”的批評性討論[J].社會,2010(2).
(責任編輯:梁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