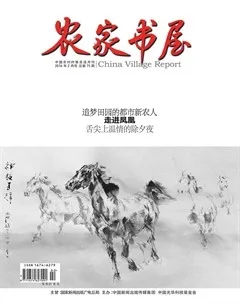春天二題


春雨江南
春風又綠江南岸。還在“草色遙看近卻無”之時,春雨就像一位喋喋不休的老者,把一些紛紛揚揚的語言灑進鄉村的每個角落。古人不見今時雨,今雨曾經灑古人?灞橋折柳催人別的煙雨,清明時節紛紛下的斷魂雨,不管是淋在古人身上,還是灑在今人臉上,都飽含著無盡的詩意和故事。于是,我獨自一人在纖塵不染的細雨里漫步,令思緒遐想翩翩,去感受或探求古人的詩情畫意。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是杜牧的名詩。本來,它那自然灑脫、清麗淡雅的風格就足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如今在綿綿春雨中吟來,怎能不令人陶醉?
許仙和白娘子因雨而結緣。一曲《千年等一回》讓多少人蕩氣回腸,“雨心碎,風流淚,西湖的水,我的淚”,“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煙”,閃著微笑的江南雨,多么像白娘子那肝腸寸斷的淚水!相會斷橋中,清明佳節雨紛紛,不是突如其來的一場雨,怎能成就一段千古奇緣。
細雨飄著,路旁的花枝在雨中簌簌抖動,不時有一陣雨珠和花瓣掉落,如同一曲縹緲傷感的弦樂。要是林黛玉看到了,她一定會唱著《葬花詞》,把這些花掃起來哭哭啼啼地葬了。花濃雨密,香霧迷離,我更多地想起了李清照。她晚年避難江南,丈夫既死,孤身一人,聽著江南的春雨,觸景傷懷,哪有半點林黛玉般的無病呻吟。“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喪夫之痛與國破家殘、故土難回的深切哀愁交織一起,然后寄托于春雨身上,難怪李清照看著閃著微光的江南春雨,會發出“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的無限感慨。江南雨是為李清照下的,弱不禁風的林黛玉畢竟沒有那份滄桑與坎坷,最多只能“為賦新詩強作愁”罷了。
“春雨貴如油,下得滿地流”,阡陌間,農人披著蓑戴著笠正在忙著農活。“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在雨中吟著張志和的《漁歌子》,眼前卻無法重現古人垂釣圖,更沒有古人那份恬淡安適的情趣。如今這紛擾浮躁的塵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誰還繼承或保留古人的那份閑情逸致?山上雨霧如煙如夢,給人一種溟蒙蒼茫之感。也難怪,晚唐詩人杜牧雖才情橫溢,可面對江南春色卻感嘆起歷史的煙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或許在杜牧心中,春雨才是江南的精魂。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青池塘處處蛙”。漫步池塘邊,雨還在淅淅瀝瀝下著,可愛的梨花掛滿了晶瑩的雨滴,顆顆如玉。叢叢梨花在雨中依偎,綻放著少女般清純的笑臉。“梨花一枝春帶雨”,柔弱的梨花能經得住幾番風吹雨打?此情此景,不由得讓我想起“杜鵑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這樣的花與詩,澆上這樣的纏綿春雨,營造出一片憂傷的美麗。“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因為雨,曾發生了多少趣事軼事,也因為雨,文學史上產生了多少不朽詩篇。
細雨霏霏,如詩似夢。如果能和知己共撐一把油紙傘,緊緊地靠在一起,漫步于鄉間古道,傘外春雨迷蒙,傘內談古論今,不亦樂乎?于是,我“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雨巷》)在江南聽雨,一定要找一個多愁善感而富有浪漫情趣的人同行,可是,人生得一知己難啊!春雨還在淅淅瀝瀝,應是良辰美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春雨江南,誰與我歸?
野菜飄香
常常夢見孩提時代剜野菜的情景,清明節前后,田畈剛剛泛青,每到假日或放學后,我們便提著竹籃,呼朋引伴,飛快地往田野跑去。
我們剜得最多的是黃梗菜。荒田里,紫云英叢中,黃梗菜多得像滿天的星星。黃梗菜葉似薺菜,梗紫紅色,還開著精致的鵝黃小花。
剜黃梗菜要用一根筷子大的鐵絲,一頭彎成鉤狀,另一頭安上木把,使用時,將鉤往黃梗菜兜頭一插,稍一扯就能和根拔出。
吹面不寒楊柳風,其時的田野空氣濕潤,陽光和煦。我們這些孩子們在春光里跑著跳著,還唱著《黃梗菜》的童謠:黃梗菜,開黃花。剁精肉,請親家。親家坐上,親母坐下,頭對頭地跟你說話……
春天不可不食苦菜。苦菜古稱荼。《詩經·谷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說的就是苦菜。陸璣《疏》曰:“荼,苦菜,生于田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本草衍義》謂:“四月小滿后苦菜秀者也。四方皆有,在北則冬凋,生南方者冬夏常青,葉如苦苣而狹,綠色差淡。折之白汁出,味苦。花似野菊,春夏皆旋開。”
家鄉的苦菜一般長在空氣濕潤的山腳下和小溪邊。清明前后,葉肥梗壯,掐其嫩莖,用沸水淖過,再浸泡一些時間去掉苦味,做成腌菜,外加大蒜、辣椒、生姜等佐料,食之稍苦,卻清香醉人。也可切碎后用來炒飯吃。早先,苦菜象征著貧窮與饑餓,被稱為救荒菜,民諺有云:“春風吹,苦菜長,荒湖野灘是糧倉。”
苦菜除了極高的營養價值外,還有清熱、涼血、解毒三大藥效。今日苦菜成了人們崇尚的綠色食品,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都市人的餐桌。
蕨菜古稱薇菜,《詩經·南召》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商朝時的大夫伯夷、叔齊被后世稱之為節操高尚的人物,薇菜也就因此成了清高守節的代名詞。
蕨菜多生于陽坡、溪邊、蔬林下,它的梢頭彎成了一個拳頭似的小葉卷,顏色暗黃,稍有絨毛。待蕨未展時,摘其葉柄,經沸水淖過后,用來炒臘肉,風味甚美。也可用鹽腌成酸菜或曬成干菜。蕨菜根還可制成高級淀粉。
竹菇只長于竹林中,它像一把小傘,大如茶碗蓋,殷紅如血。春雷響過,南風勁吹的雨后天氣最宜竹菇生長。熊榮《西山竹枝詞》詩云:“亂峰排闥小橋東,修竹參差不計絲。二月南風一夜雨,釘頭菇子滿山紅。”
一到春天,我們便去撿竹菇。尋尋覓覓,不管柴里、草里,還是刺蓬里,只要能找到一叢叢一簇簇的竹菇,便會心花怒放。
竹菇用來燒肉或煮面,稍加一些蔥花,便香氣濃郁,令人食欲大增。
陽綠的學名叫鼠曲草,周作人《故鄉的野菜》中所謂的黃花麥果是也。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鼠曲草,生平崗熟地,高尺余,葉有白毛,黃花。”
陽綠,三月間水靈靈嫩滋滋地長在向陽的田間路邊,摘其嫩莖洗凈后放在碓臼里舂成糊狀,再和上糯米粉做成清明餅,蒸熟后色澤像翡翠,食之韌性十足,清香四溢。家鄉有風俗,清明餅要送給鄰里相互品嘗。每個清明餅里,似乎都蘊含著一種濃濃的鄉情。
家鄉還有許許多多美味的野菜,比如生長水邊的水芹,其身姿挺拔亭亭玉立,聞起來有一股獨特的清香,故又稱香芹。用來炒臘肉,味勝萎蒿。
時過境遷。如今我遠離故鄉,住在都市的鋼筋水泥樓叢中,每日吃的是農藥化肥澆灌出來的大米飯、大棚里生長出來的反季節蔬菜和飼料喂養出來的魚肉,花色品種雖說齊全,卻是味同嚼蠟。我常常夢見兒時剜野菜的情景,越來越懷念故鄉眾多美味的野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