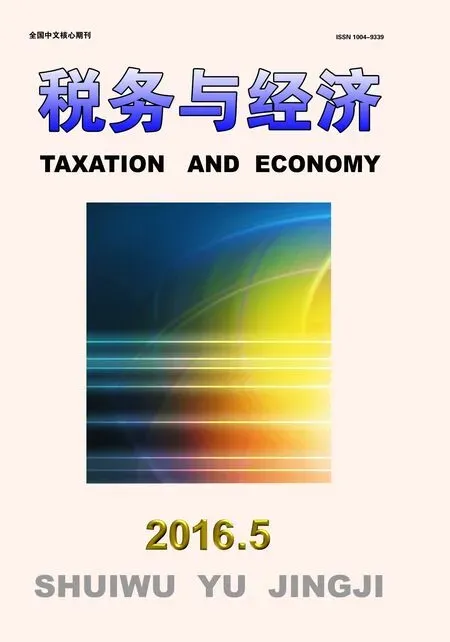歐盟航海碳稅政策:行業影響與應對策略
陳繼紅,張 浩,羅 萍
(1.上海海事大學 交通運輸學院,上海 201306; 2.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綜合運輸研究所,北京100038)
近年來,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下,碳排放問題引起了全世界各個國家的關注。節能減排、綠色理念與技術創新在世界海運業也同樣備受重視。歐盟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區域一體化組織,近年來不斷突破國際氣候變化相關國際公約框架,在針對國際航空業單方面強制實施碳稅政策并不奏效的情況下,又針對國際海運業征收所謂的航海碳稅。該項政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受到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中國作為海運大國,擁有大規模的海運船隊,海運戰略利益也將受歐盟航海碳稅政策的負面影響。本文具體分析歐盟航海碳稅政策的相關背景與主要爭議,剖析歐盟實施航海碳稅的真實目的,并在探討這項政策對中國海運業影響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應對策略和政策建議。
一、歐盟航海碳稅政策實施的背景與爭議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府京都市的國立京都國際會館所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三次會議制定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京都議定書》(簡稱《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為全世界溫室氣體減排、保證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了一個國際性的政策法規框架,但就其中具體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種責任分擔形式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歧很大。[1]2012年12月8日,在卡塔爾召開的第1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本應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被同意延長至2020年。[2]
然而歐盟直接摒棄了上述國際法規框架和政策精神,于2000年率先單方面啟動了“歐盟氣候變化計劃(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歐盟低碳政策也因此正式形成。2003年 10月13日,歐盟議會通過了《關于在歐盟內部建立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機制的指令》(Directive 2003 /87 /EC),為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ETS)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礎,依據該決議,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于2005年1月開始運作。2008年11月,歐盟通過法案決定將國際航空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實施。[3]在歐盟把航空碳稅納入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EU-ETS)后,俄、中、美、印度等29國代表于2012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相關會議討論,針對歐盟的航空碳稅問題共同簽署了《莫斯科宣言》,一致反對歐盟單方面強制推行航空碳稅行為。迫于各國壓力,歐盟對航空碳稅進行了有條件暫停執行。[4]而就在航空碳稅遭多國聯合“抵制”后不久,歐盟又拋出了航海碳稅的計劃,于2012年6月制定出航空和航海運輸業碳排放稅征收價格單。[5]不僅如此,歐盟委員會于2014年11月又通過了一項旨在減少國際航運業碳排放的法案,這是首個針對國際航運業碳排放的監管法案。該法案要求船舶監測其碳排放指標,監控影響氣候變化的污染物指標;該法案的提前期較長,預計從2018年1月開始執行,而且針對總噸位5000噸以上的船舶實行。[6]
歐盟開征航海碳稅的消息一經發布,各方質疑、抵制聲音不斷。同很多國家一樣,中方堅決反對歐盟就國際航空、航海碳排放問題采取單邊措施。各國對于歐盟實施航海碳稅持不同的意見,其主要爭議焦點在于碳稅責任大小是否有區別。多數國家認為國際航空、航海碳排放問題必須在多邊框架下通過充分協商找到解決辦法,不能脫離《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法律框架,更不能違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但是歐盟認為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碳排放問題上應當負有完全相同的責任,航海碳稅應當適用于所有國家。歐盟的單邊強制征稅行為不得人心,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估計也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二、歐盟征收航海碳稅的真實目的
名義上講,歐盟減少航海碳稅旨在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改變當前海運全球污染的現狀。然而船舶使用的燃油等化石能源在使用過程中除了排放二氧化碳之外,還會產生大量的其他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CO)、碳氫化合物(HC)、氮氧化合物(NOX)、二氧化硫(SO2)、顆粒物(PM)等大氣污染物。國際海事組織在MARPOL73/78附則Ⅵ中規定,到2012年在全球范圍內將遠洋船舶使用燃料的硫含量降到3.5%,到2020年降到0.5%。[8]歐盟航海碳稅僅局限于二氧化碳等等氣體的排放,卻沒有對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有合理的限制規定,遠不如IMO等世界組織的相關規范系統而全面,因此歐盟脫離國際框架的單方面的航海碳稅政策對世界海運污染的真正治理的目的和作用值得質疑,其不科學性和不嚴謹性顯而易見。
征收碳稅只不過對碳交易進行轉嫁,并沒有真正減少碳排放。歐盟征收航海碳稅 “治標不治本”,通過這種方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碳排放給環境帶來的不良影響。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歐盟征收碳稅不過是通過買賣來調節控制碳排放量,以碳稅交易機制平臺為基礎,對各個排放源進行一定的調節,在本質上根本無法控制減排源頭。相對來說,海運業具有運距長、運量大并大量承擔國際貨物運輸等特點,海運業與其他運輸行業相比其整體節能效果較好以及單位運量的污染程度也較低,海運業單位碳排放量也同樣相對較低。[9]國際貿易和全球貨物運輸高度依賴海運這種運輸方式,對海運業征收碳稅將極大增加海運運輸成本,而又無法從根本上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只是極大地增加了海運貿易的實際運輸成本和削弱海運貨物貿易的競爭力。
實際上,缺乏有效可行的環保治理機制是環境矛盾產生的主要原因。航海碳稅會對航運發展并不完善的國家造成很大的沖擊,但歐盟沒有充分考慮對各國的差別對待,并未制定相應的保護與扶持機制,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海運業。更重要的是沒有相關部門能保證歐盟征收的航海碳稅最終會被用于環保或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項目中,也沒有相關的資金應用的公示,碳稅的資金流向成謎,因此歐盟制定碳稅政策未必能合理地解決環境問題。歐盟強制征收航海碳稅的目的引發國際社會的懷疑和思考。
1.歐盟獲取直接的經濟利益。“航海碳稅”對歐盟來說不只是所謂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的措施。航海碳稅使歐盟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向各國航運公司征收稅費,其規則由歐盟制定,由它決定是否收取停靠在歐盟港口的船舶稅費,所以歐盟占據了相當大的主動權。如果“航海碳稅”成功實施,其利潤相當可觀。這些政策將給歐盟帶來巨大的財政稅收收入,由此解決歐盟內部的債務危機,緩解歐盟各國的財政問題。
2.歐盟謀求政治利益和全球海運事務話語權。歐盟推行這一碳稅政策不僅可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還會帶來綜合的政治利益和話語權。如果歐盟在航海行業的碳排放體系得以實現,可以預見,歐盟在航海業嘗到利益甜頭后,可能還會在鋼鐵、電氣、造船、煤炭、石油等等眾多行業推行推廣所謂的全球性的減排方案,從而實現更大的經濟利益。如果歐盟在全球各個行業都首先推行打著環保綠色的旗號實際上為自身謀利的政策,就會在道德和利益的制高點上謀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話語權。
3.促進歐盟綠色能源技術向全球出口推廣。征收航海碳稅可以拉動各國對綠色低碳材料以及相關產品的消耗使用,而歐盟恰恰在新興的綠色低碳材料、環保能源技術方面領先于世界很多國家。[10]其他國家要想符合歐盟制定的碳排放準則,就需要對本國的船舶碳排放量進行控制,從而需要對船舶進行綠色技術方面的改造,歐盟恰恰可以提供綠色技術、材料方面的支持。因此歐盟可以依靠其他國家引進其先進的技術和材料來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今天,尋訪團一行來到杭州始版橋,印刷專業的學生朝拜行業始祖——畢 ,今年是他在杭州發明活字印刷970年。烈日炎炎,尋尋覓覓,見人就問,無人知曉。最后,在一片住宅廢墟上,有人告之這可能就是遺址。不禁唏噓中國印刷之父畢 的發明地竟然如此境遇,但愿是我們搞錯了。我們一直在反省自四大發明之后,中國于世界現代科技文明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4.間接提升歐盟海運發展競爭力。歐盟以稅費的形式征收航海碳稅,表面上看似乎是在為全球環境改善做貢獻,不應該受到其他國家的質疑。但是作為征收資金的管理方,歐盟極有可能將這部分資金用于自己麾下各國海運公司的節能減排或者在技術方面的支持,從而間接地降低歐盟內部海運公司的營運成本,變相削減其他海運公司的發展競爭力,使歐盟海運業處于更加有利的競爭地位。
三、航海碳稅政策對中國海運業的影響
中國國際貿易貨物90%以上由海運方式來完成,海運業在中國的國際貿易和對外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目前的發展規模來看,海運業是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貿易發展的支柱性產業,目前中國海運船隊運力規模1.6億載重噸,約占世界海運船隊總運力的9%左右,居世界第3位。[11]但是我國海運業整體水平還較低,管理相對落后,船隊結構不合理,海運完整的產業鏈體系還不完善。[12]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堅持實現海運業節能減排的目標,同時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歐盟單方面強制推行航海碳稅政策,無視發展中國家海運業發展的實際,對我國國際海運相關行業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挑戰。
1.嚴重削弱中國產品海運貿易競爭力,損害中國制造加工業利益。中國與歐盟的出口貿易關系穩定并持續發展,為亞歐海運市場運輸量的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主要運輸產成品的國際集裝箱海運量在這一國際區域市場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和發展,1995年以來,20年內亞歐航線國際集裝箱運輸量增長了5倍多,這與太平洋航線集裝箱貨運量增長1.5倍多形成鮮明對比。世界上最主要集裝箱大船也均配置在亞歐海運市場,這條航線市場10 000~20 000TEU的超大型集裝箱船舶占比高達85%左右。[11]
中國向歐盟出口的產品主要通過海上運輸通道完成,而且出口的產品大都是低附加值的日常生活用品,對成本比較敏感。歐盟如果征收航海碳稅,將直接影響到經營這一國際區域航線市場的海運公司,進而使其成本轉移到中國海運出口的商品上,較大程度上增加中國海運出口成本,進一步壓縮這一海運市場的海運企業和中國出口商品的利潤空間。無論歐盟如何設定碳稅的起征點及稅率,都會增加海運成本,這種成本增加最終的表現是海運成本的上升和中國商品價格的上漲,導致中國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失去價格優勢,致使中國商品更加滯銷,進一步加重中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尤其是對中國中小型制造加工企業造成更大影響,出口商品將受市場限制,而短期內技術轉型又難以實現,將進一步壓縮企業生存的空間。
2.對中國海運發展相關產業鏈體系形成打擊。歐盟強制征收航海碳稅將激發國際海運業的綠色革命和形成清潔能源船舶等新興海運產業,傳統的船舶建造和設備制造業將面臨嚴峻挑戰甚至淘汰。而目前我國的造船業雖然具有規模較大的優勢,但在船舶核心技術、關鍵設備制造等方面競爭力明顯不足,主要依賴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進口。中國的清潔能源和綠色造船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難以滿足目前國際海運業對綠色、低碳的要求,大多數船東對于綠色船舶的選擇余地較小。同時中國現有航運隊伍老舊船舶比重較大,技術要求相對較低,排放較大,而即使是新造船、新加入營運船舶也可能難以滿足或將推行的碳排放標準。而且中國海運體系龐大,目前擁有和控制的船舶規模巨大,要完成新型船舶的更替是一個漫長且代價高昂的過程。歐盟主要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積累了較為先進的綠色造船經驗和擁有先進的節能低碳技術,如果歐盟成功將其碳排放交易體系推廣到國際海運業,征收航海碳稅,將激發海運公司船舶更新的意愿,歐盟的綠色造船和節能技術也將逐步打開中國的國際海運市場,這對我國的造船工業和船舶裝備等海運關聯產業體系將造成嚴重打擊。
3.對中國海運服務轉型和技術升級帶來現實挑戰。從15世紀新航路開辟開始,歐洲的船隊就出現在世界各海洋上。直到歐洲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貨運中心在世界范圍內由歐洲向美洲再向亞洲和中國等區域不斷發生變遷,先后形成了以倫敦、奧斯陸、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高雄、釜山、上海、天津等不同區域的國際港口貨運中心。[13]目前亞洲尤其是中國集聚了世界主要的港口貨運中心,全球20大集裝箱港口中,16個來自亞洲,中國占有10席。[11]然而在世界海運格局漫長的變遷過程中,全球港口貨運中心盡管在不斷轉移,但高端的海運服務中心卻從未發生轉移,直到現在,歐洲尤其是倫敦始終是全球最活躍的海運服務中心,那里聚集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海運金融、海運保險、海運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務。全球主要的海運機構和組織也大多設立在歐洲,全球主要海事技術標準和規范的制定和實施框架也大多來自歐洲。
與歐洲相比,中國目前的海運服務體系極不完善。目前,中國的海運服務還主要集中在生產作業和海運輔助服務等傳統領域。中國的港口生產作業和船舶運輸等的海運生產服務具有不可替代優勢,貨運代理、船舶代理、船舶修理、船舶理貨等輔助服務業相對完善,但海運經紀、海運金融、海運保險、海事法律等高附加值海運服務以及航運咨詢、船舶檢驗、航運技術研發、航運教育培訓等知識技術服務明顯薄弱。[14]歐盟強制力推航海碳稅,將對中國的海運傳統生產服務造成威脅,迫使中國的海運服務轉型升級。盡管目前中國政府積極倡導中國海運業健康發展及其轉型升級[15],但中國的海運服務長期以來過度依賴傳統生產領域,高附加值服務和技術知識服務發展與當前中國海運生產規模嚴重不匹配,也無法快速擺脫這種海運生產服務模式,海運服務轉型和技術升級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歐盟憑借其在海運技術和高端服務上的絕對優勢快速推行航海碳稅,實質上在打擊中國海運傳統服務的同時也在世界海運市場強制推行其海運服務和技術標準,進一步主導世界海運業發展的話語權,這給中國未來海運服務轉型升級帶來了極為嚴峻的挑戰。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
1.堅持合理的國際政策機制立場,廣泛尋求國際合作。歐盟推出的航海碳稅政策引起了世界很多國家的聯合抵制和反對。中國政府也應堅定立場,對歐盟不顧國際社會基本法律框架和世界海運業發展不平衡的實際而提出的航海碳稅予以堅決反對。中國應與歐盟主管機構開展對話談判,闡明自身的立場和措施,同時聯合相似立場的國家,協調外交行動,從政治層面給予歐盟壓力。總體上堅定維護國際統一框架,即積極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法律框架,反對違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和公平原則。在具體國際協調合作方式上,中國應加強與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反對歐盟征收航海碳稅的國家以及國際海事組織IMO等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與它們聯合起來采取行動,反對歐盟強行實施單方面立法的做法。[16]參與他國和國際組織對歐盟的訴訟,聯結發展中國家采取更多的聯合行動,在國際組織的協調機制下,藉此達成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解決方案,而非歐盟單邊碳排放交易機制。[17]
2.積極參與國際碳稅規則制定,爭取相應的話語權。盡管目前歐盟推出的航海碳稅政策在國際國內都存在爭議并遭到反對,但綠色低碳海運發展模式是不可逆轉的,國際社會對海運等行業的低碳減排趨勢具有高度共識,只是在具體的責任形式上有較大的爭執。部分發達國家堅持的“非歧視”原則與發展中國家要求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長期存在沖突,因而目前在市場機制方面的談判將比已經通過的技術標準方面的談判更為艱難。
在“航海碳稅”問題上國際海運國家尚未形成統一標準,這為中國政府參與“航海碳稅”規則制定和標準的談判提供了一定的機會。中國政府應當積極參與國際海運組織有關節能減排措施的謀劃與制定,力求提升中國海運業的影響力,爭取和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在海運碳排放稅相關談判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所確立的應對氣候變化制度原則的指導下,積極有效地發揮作為國際海事組織A類理事國的作用,努力倡導符合中國海運業發展利益的碳排放交易國際框架。
3.完善國內碳排放交易機制,探索國內海運碳稅政策。歐盟的碳排放體系早在2005年就已經建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多國參與的排放交易體系,是歐盟為了實現《京都議定書》確立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而設立的國際性氣候政策體系。它將《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目標分配給各成員國,參與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各國,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量核配規劃工作。[18]我國在“十二五”期間也已經開始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市場,并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等地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未來中國要進一步完善碳排放交易體系的具體機制。[19]而在國際海運業,在歐盟航海碳稅咄咄逼人的態勢下,中國必須加快探討自己的航海碳稅政策模式。
中國擁有大規模的海運船隊,航海碳稅對中國這樣的海運大國的影響十分巨大。從戰略利益考慮,為將歐盟的航海碳稅政策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限度,中國在加強國際合作對話的同時,應加快完善國內碳排放交易機制,建立適合中國的航海碳稅政策。現階段,中國海運業以及全球范圍內其他海運國家反對歐盟航海碳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征收的問題,而是責任區別的問題。目前對中國來說,探索合理的碳稅征收政策機制,不僅有利于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也是保護相關產業的客觀要求。從具體策略來看,中國海運業可以考慮與國際合作和自力更生兩條腿走路。
一方面,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對話和國際海事相關組織機構的談判,為中國海運業發展轉型和船舶更新爭取必要的緩沖時間;而這一關鍵的緩沖時間往往意義重大。例如已經通過的《1973 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則 VI 修正案確定了“新船設計能效指數”和“船舶能效管理計劃”兩項船舶能效標準。經過談判,包括中國、巴西、印度等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獲得了4年寬限期來改進科技以施行此兩項能效標準。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加快完善國內碳排放交易機制,建立國內海運碳稅政策,避免受制于人。歐盟之所以單方面提出航海碳稅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盟在海運船舶節能技術、政策以及碳稅機制等方面具有優勢。中國要避免受歐盟的碳稅政策的牽制,就必須探索建立屬于自己的并符合國情的海運業碳稅機制,以使中國海運業以及其他相關產業可以有規則可循,共同承擔起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擺脫遭受歐盟航海碳稅規則的限制,并對歐盟不公正的航海碳稅政策形成反制。
4.加大海運節能減排科技投入,推進中國綠色海運發展創新。節能減排和綠色海運既是大勢所趨,同時也是未來國際海運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和利潤增長點,因此,中國應加大科技資金投入和政策保障,積極推進中國海運業綠色節能減排技術的建設。加強政府、企業和相關院校三方的科研合作,推動海運節能減排、綠色船舶替代能源以及智能航運等方面的研究投入和產業發展。在健全船舶能源消耗管理體系,完善海運節能減排監測、考核制度的基礎上,優化海運業用能結構,促進清潔能源在海運業的推廣應用,開展LNG動力船舶、港口設備等清潔能源試點示范和推廣工作,推進主要港口碼頭船舶岸電設施工程的實施;同時加強綠色海運標準體系建設,制定完善的船舶能效規范、清潔能源動力船舶檢驗規范等標準規范,并健全防治船舶污染管理體系,實施船舶污染排放限值標準,加強船舶防污設施和設備開發建設。通過科技創新與技術推廣應用,從根本上減少我國海運業船舶油耗、降低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量。這樣,即使歐盟果真強制實施航海碳稅,中國也可將本國海運業由此造成的損失和消極影響控制在較小的范圍內。
5.與國際接軌,積極實施中國海運“排放控制區域”政策。中國不僅要關注碳排放和碳交易問題,還應與國際接軌,實施綜合的中國海運排放控制政策,彰顯海運大國責任,從而避免和應對歐盟片面追求海運碳排放控制和實施航海碳稅政策。在海運減少排放問題上,中國海運“排放控制區域”政策顯得極為重要和意義重大。
在2008年修訂的國際海事組織IMO《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附則VI框架下,國際海運業防治船舶的SOx 和NOx 等多種污染物的排放。目前這一公約簽署國已經在全球范圍內設立四個排放控制區(Emission Control Area,ECA),包括只執行SOx 排放控制(及間接控制顆粒物)的歐洲北海和波羅的海ECA,以及同時控制SOx、PM 和NOx 排放的北美洲和美國加勒比海地區的ECA。[20]中國也是該公約附件VI 的簽署國之一。中國交通運輸部于2015年12月發布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區實施方案》,提出在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三大水域設立船舶排放控制區(ECA),在這些中國沿海水域設立一定范圍,對進入其中的船舶排放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顆粒物濃度進行限制,從而控制船舶大氣污染。未來中國應以自有的海運ECA政策為契機,致力于改善區域空氣環境,落實中國綠色海運發展戰略,并逐步淘汰落后產能,助推海運產業結構調整,推進低硫燃油生產、港口岸電、清潔能源、船舶發動機和尾氣后處理等海運減排技術發展。這一政策的有效實施有助于發揮中國作為海運大國在國際船舶減排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彰顯中國積極履行國際海事公約的負責任大國形象。
6.推進中國海運業服務轉型和技術升級。目前中國海運服務優勢主要集中在港口作業和船舶運輸等海運基礎生產環節,高端航運服務和海事技術標準主要受控于歐盟等發達國家,高端航運服務發展嚴重滯后,海事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國際海運標準規范和標準制定的話語權也相對不足。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海運發展的關鍵環節受制于人的問題,有效降低歐盟航海碳稅對中國國際海運業的影響,還必須加快推進中國海運業服務轉型和技術創新升級。
未來中國海運業的重要任務是完善海運服務產業鏈,在傳統海運服務規模優勢的基礎上重點發展高附加值海運服務和海運知識技術產業。加快中國海運服務功能在港口生產、船舶運輸、貨運代理、船舶代理等基礎服務優勢向更高層次和協同發展的方向轉變。重點發展海運金融、海運保險、海運經紀、海事法律等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服務產業;積極推進中國海事服務技術創新,培育船舶檢驗、綠色船舶、海事規范、海事公估、海事信息等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五、結 語
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是當前世界海運業面臨的共同課題,各國均有責任和義務減少海運污染和排放。但各國的實際情況和國情不盡相同,必須在國際統一的框架下履行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而不應是某一區域或國家單方面的行動。歐盟不顧現有國際公約相關規范,對各國的實際情況完全不予考慮,單方面制定航海碳稅政策并強制執行,對世界海運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海運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和沖擊。
歐盟在國際海運業強制推行航海碳稅,將削弱我國海運貨物出口貿易競爭力,尤其是對我國海運產業體系的建設形成強大壓力,直接剝奪了我國海運產業服務轉型和技術轉型的緩沖時間。從中國海運業總體發展狀況來看,在海運服務上目前僅具有港口作業和船舶運輸等規模上的優勢,在高附加值和技術規范等關鍵領域還沒有話語權。盡管目前我國已經開始積極推進海運服務轉型和技術升級,綠色船舶、綠色海運等規劃也在加緊實施,但是我國在這一領域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技術發展和運營經驗不足。如果歐盟貿然征收航海碳稅,由于我國大量的船舶和相關海運技術還不能達到其綠色標準,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將要付出很多不公平的海運成本,那么必將導致我國的海運市場份額大量減少,嚴重削弱我國海運實力,損害我國海運業的發展利益。
盡管如此,綠色海運和節能減排將是國際海運業的主流趨勢,中國需要積極應對歐盟航海碳稅政策。應堅持合理的國際政策機制立場,廣泛尋求國際合作,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法律框架,聯合推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同時就國際航海碳稅目前的爭議,有效發揮作為國際海事組織A類理事國的作用,積極倡導符合我國海運業發展利益的碳排放交易國際統一框架。歐盟強制征收航海碳稅,對中國海運業來說的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也相應地觸發了中國海運業加快轉型升級的動力。一方面,中國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和國際海事相關組織機構的談判,為中國海運業發展轉型和船舶技術更新爭取必要的緩沖時間。另一方面,必須加快完善國內碳排放交易機制,建立國內海運碳稅政策;并與國際接軌,積極實施中國海運“排放控制區域”政策,加大海運節能減排科技投入,推進中國綠色海運發展創新和海運服務發展轉型升級。
[1]Rosen A.M..The Wrong Solution at the Right Time: The Failure of the Kyoto Protocol on Climate Change[J].Politics & Policy,2015, 43(1):30-58.
[2]Grunewald N,Martinez-Zarzoso I.Did the Kyoto Protocol Fail?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the Kyoto Protocol on CO2Emissions[J].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6, 21(1):1-22.
[3]朱曉勤,王均.對美英航空碳稅案判決的幾點質疑[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4(5):13-23.
[4]劉衡,黃志雄.論歐盟航空碳稅“停擺”的原因與啟示[J].法治研究,2013,10(9):63-70.
[5]孫家慶.歐盟航海碳稅壁壘下我國綠色航運產業鏈的構建[J].航海技術,2013,(6):73-75.
[6]張鈺羚.歐盟航海碳稅違法性探析——兼談國際社會的態度及中國的應對[J].世界環境,2015,(4):85-85.
[7]Psaraftis H.N..Green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
[8]Cullinane K, Bergqvist R..Emission Control Areas and Their Iimpact on Maritime Transport[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2014,28:1-5.
[9]Asariotis R, Benamara H. Maritime Transport and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M].London:Routledge,2012.
[10]華金秋,等.歐盟發展低碳經濟的成功經驗及其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45-47.
[1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R].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15.
[12]陳繼紅,真虹.基于灰色關聯的航運產業集群競爭力評價與應用[J].交通運輸系統工程與信息,2009,9(5):110-116.
[13]Hattendorf J.B.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4]陳繼紅,真虹.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先行先試政策[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4(5):665-671.
[15]國務院.國務院關于促進海運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32號)[R].2014.
[16]Shi X,Zhang Y,Voss S.Actions Applied by Chinese Shipping Companies und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2013,5(4-5):463-484.
[17]陳斌.碳稅邊境調整的困境與發展[J].稅務與經濟,2011,(1):104-107.
[18]馬海涌,等.國際碳市場的風險、監管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稅務與經濟,2011,(6):54-57.
[19]周文波,陳燕.論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現狀、問題與對策[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1,(3):12-17.
[20]Carr E W, Corbett J J. Ship Compliance in Emission Control Areas:Technology Costs and Policy Instrument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5,49(16):9584-9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