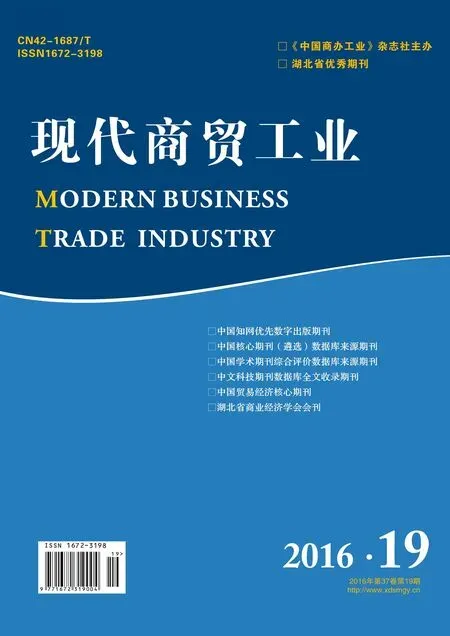守望鄉土的精神感知
杜 樂
(陜西學前師范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0)
《生死百年》是閔良先生的第一部長篇文學作品,由黃河出版社傳媒集團陽光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讀罷此書,心中涌起的是陣陣對于歷史發展進程中平凡人生活艱辛的五味雜陳。輕拂封面,隱形暗紋的乳白色似乎象征著中華民族質感而又豐厚的歷史發展。幾片看似無意飄零的落葉好似那滄桑的變遷。因為來到寧夏讀書,因為對于文學執著的愛好,一部《生死百年》讓我感受到的了寧夏作家在現今這個浮躁且追名逐利的社會下,仍舊保持一份鄉土情結的可貴。作者閔良先生以平實的敘事方式記錄了一個四川名叫舉人灣的山村百年變遷中,家族間的生死情仇,深刻地折射出在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人生存的苦難,艱辛以及對于人性本身的關注與呵護。
回望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不論是魯迅,王魯彥,沈從文,汪曾祺到新時期高曉聲,賈平凹,陳忠實,還是福克納,馬克·吐溫,肖洛霍夫,馬爾克斯等都不約而同地將文學眼光與思考聚焦在生于斯,長于斯的這片養育著自己的熱土。鄉土文學,以其承載著審視歷史發展與關照人性幽微的擔當,產生了極富豐沛的思想內涵與引起思索的優秀作品。這一部《生死百年》也正是這以創作路徑的感染下,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回顧與講述了百年變遷中,家族所走過的愛恨情仇,沖突與抗爭。筆墨間飽含著“濃得化不開”的鄉土情結。
小說中,作者以其平實,質樸的語言記錄下載歷史發展的車輪下,一代代中國人真實且艱辛地生存狀態,更多地迫使這群以土地為根本生產資料的中國人接受新生且變幻莫測的時代變遷。作者在行文中,以作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寫起,飲食男女最能反映人類生活境況。哥哥與“我”的搶食,“我和哥哥經常為爭論對方是否真的處于饑餓狀態而大打出手”,但卻也可以因為“吃”,“我們”竟也能“忘記了過去的不愉快,彼此原諒了對方,我們就像一對新婚燕爾的夫妻,進進出出都拉著手。即使晚上睡覺,我們也越過原來橫在中間的父母相擁而眠。當然,大人們并不知道我們這樣要好源于共同的利益。”甚至就連年邁的“奶奶”也很“健吃”。這樣“上有健吃而不能做營生的奶奶,下有待哺的孩子,我的父母就在這樣的環境中成天奔忙著。”“饑餓”是人類最根本的生理需求,作者將幾代人對于食物的渴望描繪得淋漓盡致,也從最基本的生存層面真實折射出時代發展中,不變的是人性中最真實的一面。用寫實的手法,完成回望故土的文學化方式。用飽蘸深情的筆觸感受那個時代人性的幽微與生活的艱辛,進而深刻思索百年歷史變遷中,中國人生存的艱辛與苦難。“吃竹筍蟲的填肚,與饑餓的人試圖剝瓜子解圍的處境居然出奇一致,面前一大堆瓜子,哪怕手腳并用,肚子也永遠難飽。”多年后“我小心翼翼地捧著巴掌大的細瓷飯碗,里面慢慢盛著一碗亮晶晶的白米飯,沒有紅薯,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從來沒想過吃干飯不需要紅薯。”在小說文本前后的比照之下,作者記述了鄉土社會的生活體驗,真實地反映出時代變化,民族生存的深刻主題。因為在歷史對生命的嚴酷考驗下無非兩種結果,一是死亡,一是活著。歷史在冥冥中注定了一些人的命運,無論你如何掙扎你都不能逃脫,在歷史面前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卑微的弱者,無意識的消亡者。小說中如此描寫比比皆是,中國人在生存的艱難面前總是出人意料的可以活下來。一個苦難民族在歷盡滄桑之后,背負著沉甸甸時代變遷的印記。
與此同時,一個民族或地域文化最為核心的便是鄉土風俗的描寫。中國自古就有釀酒,品酒悠久的“酒文化”。詩文中就有曹操“何以解愁,唯有杜康”的人生感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軍旅豪邁,還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女子憂思。因此,作者在小說中,不惜用大段的文字描述四川不同于別處的“酒文化”,小說中書寫有關“酒文化”就顯得很有鄉土特色。因為“我和母親如此痛恨父親并非空穴來風,我親眼見過的就有好幾場,那些燒酒在他們面前跟白開水差不多,正因為如此,多年后我才理解‘川人好酒’的真實含義。”就連“門市部里碩大無朋的酒罐與廠房里散發著香味的酒槽一起構成鎮上最明顯的標記。”這一點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凡鄉土作家都會以鄉土風俗的記述作為其顯著特點。汪曾祺啟蒙筆下高郵地區風俗畫小說,魯迅筆下紹興老家的“咸亨酒店”,“社戲”的回憶等等,都是將鄉土中國中最能凸顯其地域本色的典型風俗大加描寫。在風俗習慣中,審視自我,深挖中國人伴隨時代變遷的心理變化,進而對人本身的生存進行深刻關照。這沉靜而又不嘩眾取寵的寫作方式,在時下喧嘩與騷動的時代中,顯得質樸而又富于人文關懷厚度。作者用沉痛而又傷感的筆尖,敘寫歷史滄桑變化當中,生命堅韌的可貴,也同時體現出作者以一種無意識的寫作方式表現出對鄉土的眷戀與深情,表現出與五四那一代啟蒙文學家對于人性,生存境況的深切關照的一致。無論是祥林嫂,九斤老太,閏土等的人物塑造,亦是對“三味書屋”,“社戲”等的典型環境的書寫,魯迅筆下構建的是紹興老家的鄉土生存變遷。而小說中,作者主要用四代人的生活變化,愛恨交織完成對鄉土生活的書寫,從而深刻挖掘民族心理,講述內心深處生命與歷史變化的抗爭。
在仔細且饒有興致的閱讀小說過程中,作者有意識地塑造了“和尚”這一人物意象,象征著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化中最值得珍視的部分。數次出現的“和尚”總是以一種遠離政治,遠離社會發展,遠離紛擾的世事糾纏的姿態“點化”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最簡單卻又深刻地生活哲理。這好似莊周“逍遙游”般思想的高度,將人的思考調整到遠離塵囂的境界來審視宇宙萬物和世界的紛爭,但卻也有孔子積極入世的向上精神。在作者的筆下,不動聲色地完成中國幾千年深厚儒道的耦合。小說中,作者在敘述“文革”中兩位和尚在口蜜腹劍大獻諂媚之后,將完全不明事理,破壞道德生活秩序的“綠軍裝”帶上了“不歸路”,天龍寺最后的和尚,似乎象征著深厚的傳統文化中,舍生取義的俠者風范,渴求人類失落的文明與道德。另一方面,也好似浮華背后作者新中國保留了一份美好且純美的凈土,是對人性的呵護與關照,也是對世間生靈的憐憫。
立體且真實的塑造“和尚”這一道德意象中,作者將人生簡單卻又常常忽略的哲理蘊含其中。小說文本中,這樣描寫,“和尚向他攤開右手。閔正千不解地問,什么?和尚說病呀,把病都拿來我才能給你治呀。閔正千下意識地再身上抓了抓,然后雙手停在半空中,和尚哈哈大笑說,連病都拿不出來,我怎么給你治呀?施主你沒病。說罷,和尚起身就走,還念叨萬物不垢不凈,不生不滅,煩惱由心,病痛由身。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得不感慨,作者獨特的文學構思,從而深刻卻又具體的加深了小說文本的文化歷史厚度。作者深厚的文化素養與其文本所呈現出的小說意蘊無疑更加呈現出作為鄉土作家根深蒂固地對于沉甸甸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敬仰與鄉土生活的眷戀。這也區別于時下奪人眼球但又空洞乏味的流行文學作品形成了鮮明地對照,進而突顯出作者對于文學的堅守與其清醒的認識。
作為典型鄉土小說作品,我還窺探到作者在用一種直白的敘事方式,用看似簡單的文學書寫形式,呈現出生命的強韌。作者在敘寫時代變遷中,以符合典型時代大眾文化敘寫時代特征。費翔“故鄉的云”,郭敬明的《悲傷逆流成河》,“非誠勿擾”中寶馬女的哭泣等等都顯示作者在觀照鄉土的同時,與關注時代發展相同步的社會發展的時代性。縱覽小說文本,作者筆下百年變遷的描述中,雖沒有《白鹿原》般大開大合,不似《紅高粱》般熱血沸騰,但卻記述的是質樸濃郁鄉土家族的變遷,真實卻又感動人心。
[1] 閔良.生死百年[M].銀川:陽光出版社,2011.
[2]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