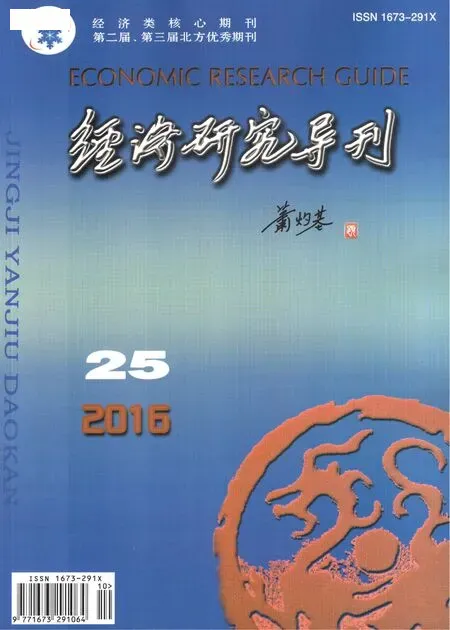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問題
崔志宏
(北京物資學院,北京 101149)
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決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問題
崔志宏
(北京物資學院,北京 101149)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需要再進行一次思想解放。中國房地產市場近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尤其近十年來的超常規發展模式暴露出來的問題、帶來的隱患、積累的矛盾不能允許按照原有模式走下去,必須通過思想解放,深化包括政府財政體系、政府管控體系甚至是政治架構模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來解決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遇到的以房地產市場為典型的發展問題。
房地產;市場;改革
中國進入21世紀,經濟實力為重點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提升。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得益于中國制定的改革開放政策。經歷了嚴重壓抑的中國經濟,通過改革開放煥發出蓬勃生機,綜合人口紅利、豐富的能源以及整體穩定的國內社會環境等等因素,中國獲得了超常規的發展。但是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國際市場的變化,傳統的外向型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很難想象在世界市場生產相對過剩的情況下,中國能夠僅僅依賴世界市場保持自己的高速發展。
21世紀初,擴大內需的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認同。要利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人口是決定潛在消費的最主要因素。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的消費市場不應該得不到重視。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根據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教育、住房、醫療不可避免地成為擴大內需的突破口。本文僅論證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問題,房地產等成為刺破中國高儲蓄率文化的尖刀。
一、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的突出問題
“高”房價是目前房地產存在的突出問題的表象。在一個成熟的擁有充分理性并且信息對等透明、交易雙方平等自愿不受干擾的市場,其形成的價格無所謂高低。目前的高房價直接引發或埋下諸多極具威力的隱患。
目前的高房價已經突破了合理水平。以通行的租售比指標來衡量。房屋租售比是什么?一般而言,“房屋租售比”=“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的月租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的房價”。一般而言,按照國際經驗,在一個房產運行情況良好的區域,應該可以在200—300個月內完全回收投資。有學者研究,在2015年北京上海兩地,需要至少500多個月才可以收回投資,而2016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價又遭遇了瘋狂的漲幅。以另一指標,北京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191元。北京市城區房價很難找到4萬以下的,即使緊鄰北京的燕郊等地的房價也已經突破2萬每平方米。
二、“高”房價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
第一,高房價極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成本,降低人們的生活品質。高房價首先體現在高地租上。以北京為例,城區一居室租金五六千是很平常的,而一個北京在編事業單位的科員的稅后月工資也僅僅5千元左右。造成北京市交通擁堵的原因之一就是超高的房價,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燕郊等地成為睡城,店鋪租金占據了店鋪經營成本中的很大比例。以通州為例,店鋪租金每日每平米十元是很低的標準,通州萬達廣場要達到15~20元每日每平方米。
第二,高房價也造成了對社會倫理文化的沖擊。代表例子就是高房價衍生出來的離婚潮。“假”離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規避政策限制,節約購房成本。高房價對于人們的價值觀也構成沖擊。以筆者為例,十多年的教育工作,個人收入不過幾十萬。本單位同事,入職恰逢單位分房,30余萬購入,幾年后,以近300萬賣出,然后辭職。辛苦一生買不到一套房或辛苦工作數十年不如炒一套房子。這對于人們的價值觀和事業觀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沖擊。
第三,高房價扭曲了經濟結構,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據媒體數據顯示,2015年以412家上市公司為準,兩市(上海和深圳)共有46家公司的全年凈利潤不足1 500萬元。2014年的年報數據也顯示,494家上市公司凈利潤不足1 500萬元,占全部2 818家上市公司的17.53%。農業是國之基本,實業是國之柱石。高房價引致的生產成本的上升很難在終端消費者那里獲得足額補償。價格上升,消費數量下降。成本上升幅度大于產品價格上升幅度必然壓縮利潤。當實業利潤降低和炒房收益巨大兩者沖突的時候,很多企業家選擇關掉企業去炒房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第四,高房價,尤其是持續高漲的房價給了政府和銀行乃至社會公眾一種“房價”幻覺。“土地財政”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績鴉片。銀行也以房貸為優質貸款,利潤重要來源而推波助瀾,社會公眾面對持續高漲的房價失去理性。
三、高房價的成因
只有找到中國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的原因才能夠對癥下藥解決這個頑疾。
首先要明確的就是房地產具有的雙重屬性中的消費屬性完全被投資屬性所掩蓋,否則無法解釋超高的租售比,無法解釋只要有可能人們就要購買超過其居住需求的住房。房地產徹底淪為投機標的是高房價的直接原因,以下是推高房價的其他因素。
第一,政府土地財政的強烈驅動力。中國大政府格局必然要求龐大的財政支持。姑且不論政府官員的尋租問題,單純從政績考核驅動來講,花錢尤其是耗費巨資打造形象工程也是官員的優先選擇。土地是政府掌控的最佳資源。目前的一個“隱雷”地方債務問題和土地財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財政資金無法滿足地方官員迅速提升政績的要求時,舉債就是一個必然。而擔保品往往就落在了政府能掌控的優質資源——土地上。為了維持這個格局,推高地價,高漲的房價是地方政府官員樂于見到的事情。通過比價效應,制造出來的“地王”會刺激房價進一步高漲。
第二,銀行提供撬高房價的杠桿。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披露,上半年個人住房貸款增加2.3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6月末增速達32.2%,月度增量屢創新高。京滬兩個城市今年上半年個人住房貸款總計增加了超過3 000億元。如果沒有銀行的參與,房價如此高漲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了股市等融資渠道,但是銀行依然是房地產市場各方最值得信賴的杠桿提供者。杠桿的產生伴隨了泡沫的風險,這個是常識。尤其是銀行為了利益,次級貸問題引爆了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當前,無論是房地產開放商還是最終購房者都充分利用銀行提供的資金來推動房價的上漲。而房價下跌,首先受傷的就是銀行,極端例子就是斷供。銀行以金融市場崩潰要挾政府,所以持續上漲的房價是銀行樂于見到也是極力促成的。銀行風控受到各種外部干擾,銀行敢于提供推高房價的杠桿,背后其實還是對于大政府的一種信任和詐欺。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單一。中國經濟結構需要調整是共識。但是,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打斷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4萬億投資不僅沒有優化經濟結構,反而強化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一旦遇到經濟出現問題,推高房價拉動經濟就成了一個熟悉的套路。上文也談到,炒房收益高企打擊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創新能力缺乏合適的土壤,企業家更多是把資金投向了房地產市場,加劇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
第四,供需雙方博弈力量失衡。任何泡沫的產生都離不開失去理性的賭徒抑或是被貪欲蒙蔽了理智而幻想自己總會有好運氣不會成為最后接盤者的買家。土地有其特殊屬性,在特定區域,土地是固定的。中國人投資渠道少,股市波動太大,理財中各種陷阱更多,人們目前更多是嘗到房產升值的甜頭,又沒有受到貶值的傷害,所以投資房產成為一個最優先選擇。同時,開發商為代表的賣房通過各種手段制造恐慌氛圍,消磨買方理性。
第五,政府管控手段和能力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政府的管控手段和能力不強是不能回避的問題,首先,缺乏預期從而政策制定缺乏提前量往往被市場牽著鼻子走。政策的滯后性極大削弱了管控效果。例如北京市政府東遷通州,只是到了通州房價已經爆炒之后才出現限購政策。其次,政策執行缺乏持續性。限購等政策在大中城市本應是需要持續執行的,但是往往地方政府受經濟環境影響時而放松時而收緊,導致政策失靈。再次,調控手段單一。目前調控手段更多依然是依靠行政命令,例如地方政府要求不出地王等。經濟行為最有效的管控,還是從經濟角度改變經濟成本收益。
四、對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建議
第一,必須切斷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地方政府的財政過度依賴房地產市場必然導致地方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所以,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有取有舍。中央政府應重新審視分稅制帶來的現實問題,而要從根子上切斷土地財政,首先要深入反腐斗爭,房地產領域是腐敗高發區域,就是因為這個領域尋租空間巨大。所以,通過有力的反腐斗爭可以抑制地方政府官員的個人謀利沖動。其次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對于大政府的取向要進行檢討,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只有簡政才能精兵,只有精兵——壓縮冗員才能夠降低社會稅負。
第二,堅定持續有效地貫徹調控政策。調控政策要有持續性,例如限購政策在大中城市必須要持續堅定的執行。否則斷斷續續的執行只會導致需求在短期限購空窗期爆發,反而會促使房價非理性上漲,限購的預期便不會達到。限購等政策是把房地產回歸商品而非投機標的有效手段,所以利用現有技術通過大數據全國一盤棋,可以有效地打擊房地產投機行為。
第三,切斷銀行的輸血鏈條。可以講,房價的暴漲背后的資金就來自于銀行的信貸。所以嚴查銀行信貸,提高銀行的風控水平,同時保證銀行的信貸業務不受地方政府的脅迫,并在適當時機通過上調首付比例來降低資金杠桿。特別需要注意的就是,嚴禁以房抵押二次貸,這相當在杠桿上面繼續加杠桿。
第四,要有勇氣破產一批房地產企業。要有勇氣讓一部分地區的房價降下來,這么做的目的是破除人們對于政府給予房地產市場背書的預期。一旦人們對于政府是最終保險人的角色認識不變,那么瘋狂炒作就不會休止。一旦人們對于政府需要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的預期不變,那么人們炒房的熱情就不會減退。
第五,要加大對于房地產租金稅收的征收力度和幅度。通過降低租金收入預期,從經濟角度抑制商業地產租金暴漲對于整個經濟的傷害。
第六,最終依然是要地區均衡發展才能根本解決大中城市房價暴漲的困局。分散式經濟布局比輻射線經濟布局要更健康更安全,所以要多中心發展模式而不是輻射線發展模式。缺乏接盤的炒作很快就會停止,所以經濟發展方式的順利轉型是解決房地產市場的最終法寶。
[責任編輯吳明宇]
F293.3
A
1673-291X(2016)25-0095-02
2016-08-16
崔志宏(1977-),男(滿族),北京人,講師,從事體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