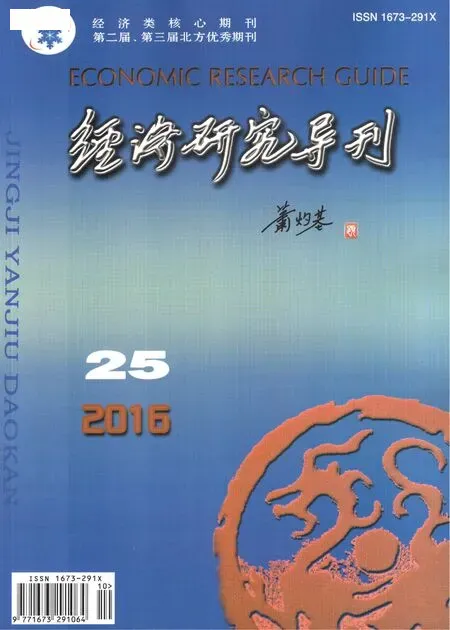上海市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P區(qū)為例
吳貞芳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上海 200061)
上海市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P區(qū)為例
吳貞芳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上海 200061)
在上海,無證照餐飲店一般是由外來務(wù)工人員、下崗職工等非正規(guī)就業(yè)者經(jīng)營的,在滿足廣大中下階層消費者飲食需求的同時也解決了這些就業(yè)者的生計問題。但監(jiān)管部門設(shè)置的餐飲準入制度對他們而言似乎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高墻”,導致這些餐飲店被迫成為“非法”經(jīng)營主體。運用訪談法和實地觀察法,對上海市P區(qū)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進行全方位考察,進而分析這些無證照餐飲店與房東、消費者、執(zhí)法部門和大眾媒介的互動關(guān)系,并揭示其背后的各種權(quán)力交互。
餐飲店無證照;生存狀態(tài);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圖;權(quán)力交互
20世紀80年代,與改革開放相伴而來的是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型和非公有制經(jīng)濟的產(chǎn)生,就業(yè)領(lǐng)域隨即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大批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知識青年返城和下崗再就業(yè)等一系列因素催生非正規(guī)就業(yè)群體的出現(xiàn),他們大多選擇從事像飲食業(yè)這樣低門檻的就業(yè)方式來解決生計問題。但隨著城市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開設(shè)餐飲店需要申辦各類證照,而這些餐飲店通常較小、價格低廉,由于很難達到這些相關(guān)的許可要求而被處于無證無照的尷尬局面。
本文以上海市P區(qū)為例研究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及其影響因素。P區(qū)下轄6個街道、3個鎮(zhèn),與中心城區(qū)及郊區(qū)都有接壤。原為老工業(yè)區(qū)的城區(qū)格局意味著區(qū)內(nèi)多“城中村”、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和老式小區(qū),人口密集且外來務(wù)工人員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員較多。P區(q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階層分布導致無證照餐飲店比例較高。
根據(jù)P區(qū)執(zhí)法部門對無證照餐飲店的摸底資料顯示,2012年P(guān)區(qū)共有無證照餐飲店1 141戶,2013年略有上升,為1 201戶。從無證照餐飲總體分布情況來看,兩年內(nèi)各街鎮(zhèn)無證照餐飲店比例相對穩(wěn)定,主要集中3個鄉(xiāng)鎮(zhèn),其中尤屬TP鎮(zhèn)數(shù)量最多,占總數(shù)量的40%。并且,每個街鎮(zhèn)中均有幾個路段會集中開設(shè)無證照餐飲店。從經(jīng)營群體構(gòu)成看,約有83.35%為外來人員,僅16.65%為本市戶籍人員,且這些無證照餐飲店多以夫妻共同經(jīng)營為主。從經(jīng)營狀態(tài)分析,這些無證照餐飲店的類別主要以小型飯店、小餐飲店形式居多,經(jīng)營時間在一年以下的有330戶,占總戶數(shù)的27.53%;一至三年的有421戶,占35.05%;經(jīng)營時間超過三年以上的有450戶,占37.42%。
一、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研究
在上海開辦一家餐飲店,合法資質(zhì)的取得意味著需要經(jīng)過多個部門(工商、食藥監(jiān)、環(huán)保、市容、消防等)審批和滿足限制性審批條件,主要涉及的就是房屋問題。規(guī)定表明,房屋無產(chǎn)權(quán)證明或獨立產(chǎn)權(quán)證明、擅自改變房屋性質(zhì)、場所屬違章搭建或臨時性建筑,以及影響周邊無法通過環(huán)保局審批的房屋均不適合作為餐飲經(jīng)營場所。所以,即便食品來源可靠、操作規(guī)范,沒有選對“房”也會被迫成為違法主體。
而從事無證照餐飲的經(jīng)營者的年齡普遍偏大,知識體系和技能偏低。他們從事餐飲經(jīng)營通常僅僅是為了生存,為了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條件,繁雜的申請手續(xù)和高門檻的準入條件使他們無意或不知情中違反了規(guī)范,有的經(jīng)營者雖然知情,也并非有意與政府的一些規(guī)范對抗,所以他們違反規(guī)范并非是自愿的。
正因為他們游離于正式法規(guī)之外所呈現(xiàn)出的經(jīng)營狀態(tài)不被政府所認可,例如:衛(wèi)生狀況普遍不佳;從業(yè)人員食品安全意識薄弱;所產(chǎn)生的油煙、噪音、排水等問題讓周邊居民苦不堪言等。同時,他們的存在也使那些正規(guī)持證經(jīng)營者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對他們造成壓力。因此,無證照餐飲店的經(jīng)營與目前城市管理等政府部門制定的規(guī)范體系格格不入,不具備合法的身份地位,是被現(xiàn)有制度或政策貼上“違法”標簽的經(jīng)營行為。
二、無證照餐飲店的社會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圖
筆者在調(diào)查期間發(fā)現(xiàn),無證照餐飲店的生存狀態(tài)會受到周邊群體的影響,這些影響會直接導致它的發(fā)展狀態(tài)。這些群體涉及到房東、消費者、執(zhí)法部門和大眾媒介,構(gòu)成了以無證照餐飲店為中心最基本的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
(一)無證照餐飲店資質(zhì)的獲取者——房東
無證照餐飲店在整個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中首先要與房東產(chǎn)生租賃關(guān)系,房屋問題也是這些餐飲店是否具有“合法”資質(zhì)的硬件條件。房東出借經(jīng)營場所,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而往往忽略了作為房東應(yīng)承擔的責任和義務(wù)。利益驅(qū)使又催生二房東群體的誕生和發(fā)展,多層的租賃關(guān)系無法有效地保障租賃者的合法權(quán)益。
(二)無證照餐飲店經(jīng)濟利益的關(guān)系者——消費者
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背景下,供求關(guān)系成為無證照餐飲店存在及維持的根本原因。潛在的巨大餐飲消費市場使非正式經(jīng)濟的產(chǎn)品交換具有良好的生存空間,無證照餐飲店作為正式經(jīng)濟空間的隱形消費市場存在,在追求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下促使這一隱形消費市場加速發(fā)展并呈現(xiàn)出來。它主要由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共同組成,通常這些無證照餐飲店的經(jīng)營更貼近大眾化,由于沒有正式制度化的費用支出(稅務(wù)、辦證費用等),在價格上更具優(yōu)勢和競爭力。在市場經(jīng)濟背景下,這種價格策略極大地迎合了普通市民的消費需求。
(三)無證照餐飲店的管理者——執(zhí)法部門
國家在立法過程中往往對利益主體多元化,訴求多樣化理解不足,在體制框架內(nèi)設(shè)置了較高的準入門檻,使無證照餐飲店被排除在合法身份之外。而面對這些餐飲店的經(jīng)營,政府也不愿意增加行政管理成本,他們更愿意將有限的資源力量用于那些屬于合法范圍內(nèi)的餐飲店上,所以這就增加了無證照餐飲店爆發(fā)飲食安全的風險率。另一方面,一個小小的餐飲店可以受到多個執(zhí)法部門的監(jiān)管,分段式的管理模式導致管理不閉合、執(zhí)法有爭議,部門之間的壁壘存在又導致部門間難以合作,無法形成協(xié)作治理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在執(zhí)法過程中面對無證照餐飲店,執(zhí)法部門也通常習慣用“運動式”的管理手段來解決問題,通過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加以控制,一般的處理方式就是處罰或取締。但從現(xiàn)實情況看,這兩種簡單、剛性的治理手段太過形式主義,未考慮到生活在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權(quán)益保障,常常會侵害到他們的生存權(quán)和經(jīng)營權(quán),有時還會產(chǎn)生不良的社會影響。
(四)無證照餐飲店的“雙刃劍”——大眾媒介
大眾媒體對無證照餐飲店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媒體受政府影響不時曝光一些無證照餐飲店的食品安全狀況,或有記者直接暗訪舉報其中的違法行為,使無證照餐飲店受到社會排斥,給公眾留有“壞”印象。但對其中一些弱勢群體的實際困難信息匱乏,使他們被邊緣化,喪失話語權(quán)。另一方面,網(wǎng)絡(luò)媒介也成為不少無證照餐飲店可以利用的營銷資源,幫助自己打開市場,快速而有效地帶來直接的經(jīng)濟收益。但這個過程也常受到政府部門的控制和打擊,如網(wǎng)絡(luò)平臺的銷售。其實,這些無證照餐飲群體中也有不少渴望發(fā)展、希望得到合法資質(zhì)的商家,但“資質(zhì)”問題始終成為它們無法逾越的“障礙”。
三、無證照餐飲店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背后的權(quán)力交互
從分析無證照餐飲店的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圖我們可以看出,其背后隱藏的政治權(quán)力、經(jīng)濟權(quán)力、社會權(quán)力和媒介權(quán)力共同塑造了無證照餐飲店的形態(tài)及其發(fā)展趨勢。
在交互關(guān)系中各種權(quán)力呈現(xiàn)出明顯的力量不均:(1)政治權(quán)力與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互動缺乏完善的法律規(guī)范,不但使政治權(quán)力的運行存在失控的危險,也影響到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正常發(fā)揮,制約經(jīng)濟效率和經(jīng)濟增長。如前文所述,無證照餐飲經(jīng)營被理解為是一種非正式經(jīng)濟。在我國建國初期存在著大量的非正規(guī)部門,但那時的制度體系卻不完備。之后國有化改革,經(jīng)濟規(guī)制和社會規(guī)制逐漸減少,非正規(guī)部門也隨之減少。到了20世紀80年代,經(jīng)濟技術(shù)快速發(fā)展,從事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數(shù)量增加,此時政府為了規(guī)范市場制定了多種法律條文加以約束,但制度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了在經(jīng)濟市場環(huán)境中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并迫使非正規(guī)部門在法律框架之外加以發(fā)展。所以與其說是無證照經(jīng)營者自身造成了違法行為,不如說是目前的制度體系將他們隔離在外,自我發(fā)展的過程中更暴露出許多問題,造成他們不被認可的局面。(2)政治權(quán)力與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互動缺乏成熟的民主機制,使政治權(quán)力在運行過程中凸顯專制。制度體系中博弈的結(jié)果取決于各個群體力量的大小,包括權(quán)力的掌控、輿論的控制、話語權(quán)的掌握等等,制度的制定也以某個群體的利益為出發(fā)點,博弈的結(jié)果自然也帶有這種利益傾斜。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期,市場經(jīng)濟的背景下利益需求多元化,客體多樣化,而政府在互動博弈中占絕對優(yōu)勢,在政策的制定上往往以自身及利益集團為主而損害到其他一部分群體的利益。無證照餐飲店目前的生存狀態(tài)正是印證了這種博弈的結(jié)果,且媒介自上而下的傳遞方式使它們喪失話語權(quán),使它們總以負面報道的形式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它們也無法向社會表達它們真正的生存需求,在經(jīng)營過程中的不易、困境、無奈和被迫。(3)社會權(quán)力未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權(quán)力的影響。我國對餐飲經(jīng)營的規(guī)制仍處在起步階段,對餐飲經(jīng)營的治理多依靠執(zhí)法部門的監(jiān)管,未充分發(fā)揮餐飲行業(yè)協(xié)會等社會組織對餐飲經(jīng)營的指導作用。政府管理社會化是無法抗拒的趨勢,相對政府的行政運行手段,社會組織的成本會低廉的多,與剛性的政治權(quán)力形成互補,而相對單純的市場調(diào)節(jié),又更能保證社會公益目標的實現(xiàn)。所以,充分發(fā)揮社會權(quán)力,轉(zhuǎn)變社會治理模式顯得極其重要。
綜上,在對待和處理無證照餐飲店這個問題上政治權(quán)力、經(jīng)濟權(quán)力、社會權(quán)力和媒介權(quán)力的發(fā)揮需要有一個合理適度的界線,它們的分化與整合有利于推動社會機制的介入和創(chuàng)新,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促進和諧,有利于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良性發(fā)展,并對推進我國實現(xiàn)服務(wù)型政府具有深遠意義。
[責任編輯周沖]
F719.3
A
1673-291X(2016)25-0162-02
2016-07-08
吳貞芳(1983-),女,上海人,在職研究生,從事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