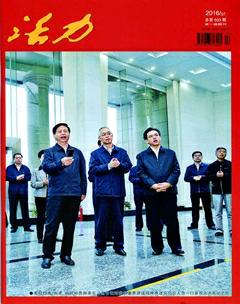史學工作者的愛國情懷
陳靜
今年一回顧,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在近代中法關系史的領域里浸潤了16年。無論是碩士論文《滇越鐵路的修建》還是博士論文《黃埔條約簽訂后法國在廣東的傳教活動》,其實都屬于中國近代史的范疇。每次做這段鴉片戰爭到民國的晚清史,總不禁產生一種感慨,就是一個孱弱的國家致使整個民族都是屈辱的,國家的統治機構從中央最高中樞到地方最末微的官員通通在來到自己國家的強者面前卑躬屈膝。史學工作者就是這樣在讀史和治史中,不自覺地產生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這樣由自身內部產生的民族情懷與外界強加的不同,它一旦形成基本不會消除。
史學工作者如何在讀史和治史過程中產生民族感情和愛國情懷,就以本人做博士論文先做個簡單的例字。博士論文剛擬定題目,一位指導老師就要求我先把立場明確起來,一開始自己還不以為然,覺得應該不偏不倚地用材料來說話。而不是帶著既定的眼光來論證。誰知一閱讀材料。不得不佩服他們這些數十年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教授們的眼光之毒辣,其實他們早已窺得其中的真相:晚清史就是中華民族的屈辱史。因為我一方面從中國官方的檔案材料中看到的是。清朝政府數次向西方強國退讓的協定和章程,無論是他們要求建教堂的土地,還是為了擴大教堂用地把周圍居民遷出兩條街以外。為了協助西方傳教士修建教堂進行采石而彈壓當地村民,為了保護外國人專門派出軍隊鎮壓本國民眾等等,無一不反映出一個卑躬屈膝的政府任西方強國隨意欺凌,無法反抗的真相,原因就是這些西方強國的堅船利炮早已令虛弱的清朝政府徹底屈服。而另一方面從西方人寫的著作和使用的事件當事人的原始信件中觀察到的是,西方強國在中國的耀武揚威、無所顧忌,以下兩個場景可以恰如其分地說明這種情況:一個場景是在中法雙方簽訂石室教堂用地儀式時發生的,在簽約儀式開始前法國駐廣州最高司令官(其實只是一位海軍上尉),在被英法聯軍俘虜的前兩廣總督葉名琛官宅的院子里策馬一圈,然后下馬把佩劍插在地上,向廣州主教行騎士禮。聲稱他剛跑過的這個范圍現在屬于這位廣州主教,根本沒看一眼垂手肅立在一旁的廣東地方軍政要員一眼。昂首進入簽約的房間。另一個場景是廣州主教乘坐的轎子與清朝官員的轎子相遇。洋大人視而不見繼續前行,揚長而去,而清朝官員則下轎退讓并垂首恭送洋大人離開。任何一個讀到這樣真實歷史資料的史學工作者一定都會在腦海里反映出“屈辱”兩個字,一個主權國家任外來列強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已經喪失了獨立主權。實際上。晚清整個時期直至近代中國,中國的海關、稅務、郵政等要害部門均被英國人、美國人等西方國家人員把持,這樣還能說這個國家擁有獨立主權?充其量就是擁有半個主權的半獨立國家,是仰西方列強鼻息的懦弱政府。通過這樣的讀史和治史,在我們史學工作者內心產生的情懷就是,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個民族即使人數再多。也只是一個弱小的民族,而一個大而弱的國家只能任人欺凌。為了讓這個國家和民族變得更加強大,作為其中一員的史學工作者應該做哪些事情呢?這就是我們史學工作者愛國情懷產生的過程。
下面我們看看史學工作者是如何用自身打上中華民族烙印的愛國情懷來洽史。并用來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權利。月前。我院邀請一位旅居海外多年的研究釣魚島問題的史學家講學,這位史學家的治史經歷讓我們看到了深藏在他心中的愛國情懷。這位史學家坦陳,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發生釣魚島事件時,他正在日本留學,看到這種狀況就敏銳地意識到中日兩國遲早會因為釣魚島主權歸屬發生沖突,那么到時中國政府用哪些證據來維護自己的主權,駁斥日本政府占據釣魚島的既定事實,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沒有任何組織委托,也沒有任何經費支持。他完全是出自自愿地盡可能多收集證明釣魚島屬于中國的相關資料,甚至包括日本政府和陸軍部的地圖。用日本的官方資料來證明釣魚島在甲午戰爭前并未歸人日本國版圖。由于當時日本政府并未重視釣魚島問題,這位史學家在離開日本時帶走幾大箱相關史料,資金完全依靠省吃儉用留學生獎金。然后是大洋彼岸潛心研究十數年。不顧這門學科是冷門。讓他在寂寞和孤獨中堅持下來的理由就是愛國情懷。今年,在中日兩國因為釣魚島主權問題發生爭執時,在中國政府需要釣魚島從歷史上就屬于中國的證據時,這位旅美多年的史學家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交上去,我們從他的語句中感受到的是欣慰,而不是獲得國家課題和釣魚島首席專家這樣的殊榮而產生的自喜,他欣慰于我們國家已經強大到著手維護以前無法觸及的遙遠的海權。據他所說,正是這種民族認同感,讓海外許多華人不計任何代價地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貢獻。至于這種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情結,一位旅德多年加入德國國籍的華人從內心發出感慨,這些年他們確確實實感到了,祖國的強大惠及到了每一個海外華人。這種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情懷是我們在國內感受不到的。
為這場報告會做講評的另一位專家,同樣用自己的治學經歷談了他們一批史學工作者的愛國情懷。這位專家是暨南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他率領的研究團隊剛中標國家重大課題,是關于南海諸島問題,同樣是為我國目前維護海洋權益所用。這位重大課題的首席專家,并沒有提任何與榮譽有關的話語,而是很平靜地告訴在場聽報告的人員,他們研究南海島嶼問題已經十幾年甚至經歷了不只一代史學工作者,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在場的青年學者,選擇研究課題有一個基本原則,也就是埋藏在每一位史學工作者心中的尺度,盡管他沒有點明,但在場每位人員都不言自明地理解到,這位首席專家指的尺度就是對國家和民族有用。史學工作者對民族和國家的感情不是暴風驟雨式的,而是堅定的、持久的、日積月累式的。他們把自己對民族和國家的感情融入日常的學習和工作中。并一直默默積累著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國家需要時,他們將會爆發出排山倒海式的力量,盡自己最大力量用自己所學為國家和民族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