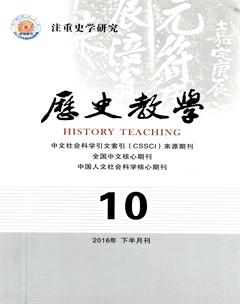五四新潮下的歷史教育
摘 要:受五四新潮的影響,在1922~1925年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年會上,歷史教學組的學者,針對當時中小學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若干改革歷史教育的議案。分析這些改革案,我們不難看出,中小學歷史教育在史學“科學化”新潮影響下,出現(xiàn)了“人的隱去”的新取向,以及“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的新追求。不過,五四新潮下的歷史教育對史學新取向不是激進地“全盤照搬”,而是多少保留了一些“傳統(tǒng)”的。
關鍵詞:五四新潮,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議案,歷史教育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6)20-0028-08
中華教育改進社是受五四新潮的影響而建立的一個規(guī)模較大、且具全國性影響的教育社團。1921年12月該社成立于上海,是由南北教育家聯(lián)合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志社、實際教育調查社等規(guī)模略小的教育團體合并組建的。該社“以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進行為宗旨”。①在成立大會上,南北方教育界人士推舉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黃炎培、汪精衛(wèi)、熊秉三、張伯苓、李湘辰、袁希濤等9人為董事會董事,孟祿、梁啟超、嚴修、張仲仁、李石曾5人為名譽董事,并決定設總事務所于京師。董事會聘陶行知為主任干事。該社還設立32個專門委員會,分別研究各級教育(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各類教育(如義務教育、職業(yè)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各科教育(如國語教育、歷史教育、地理教育)等。
晚清以來,新知識界在普及教育、培養(yǎng)新國民的旗號下紛紛組織教育社團,到五四前后達到了高潮。②若究其原因,似有幾個方面:其一,新文化運動沖擊了傳統(tǒng)舊教育,新式教育亟待研究和發(fā)展,而政府又無暇顧及于此;其二,各種新式學堂及留學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較強群體意識和趨新觀念的知識分子,而當時中國的政治特點,使得新式教育的推行與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育社團的群體力量才得以實現(xiàn);其三,清末以來,大量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加之歷來有文人結社的悠久傳統(tǒng),而政府對結會設社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政策。③在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五四前后教育界涌現(xiàn)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教育社團,中華教育改進社則是其中相當突出的一個。
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存在時間只有五年左右,一般認為北伐戰(zhàn)爭開始后,該組織就解散了。它存在時間雖短,然從1922年至1925年先后在濟南、北京、南京、太原舉行了四屆年會,每次年會討論的議案多達100件以上。這些決議案或呈報教育部采納,或函請地方、學校酌量施行。①每屆年會上,歷史教學組都提出許多改革議案,議題涉及很多方面,如歷史課程的側重點、史地課程的合理配置、歷史教科書編纂的改革,等等。
學界對中華教育改進社的研究比較薄弱,其中有關年會歷史教育議案的研究成果更為稀見,而且闡釋也尚顯不足。②鑒于此,本文擬以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歷史教育議案為研究對象,將之放于五四新潮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分析這些關涉中小學歷史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議案體現(xiàn)了何種新的取向,并由此揭示五四前后歷史教育的一些新面相,豐富我們對于這一時期歷史教育的認知。
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議案中,反映出一種在“科學化”思潮下“人的隱去”③的新取向。這種“與國際接軌”的現(xiàn)象至少在兩份議案中有較多的體現(xiàn)。其一,梁啟超提出了《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梁啟超猛烈抨擊“中國舊史以一姓興亡斷代為書”,主張編纂“普通史”。梁氏的“普通史”分為六部:(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會及經濟;(6)文化。也就是六部專門史。其中“年代”雖然必會涉及朝代興亡及帝王嬗替,但并不是教科書的敘述主體,“不過借作標識時間經過而已”,且篇幅不及全部內容的1/20。最可能牽涉到政治人物的“政治”一部,梁啟超卻認為:
對于一時君相之功業(yè)及罪惡皆從略,專記政制變遷之各大節(jié)目,令學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④
其余如“地理”“民族”“社會及經濟”“文化”等皆不以人為中心而注重敘述制度、群體,且“社會及經濟”“文化”兩個部分內容的篇幅占全部內容的一半,成為梁氏所謂“普通史”的主體部分。由此可見,梁啟超的“普通史”幾乎只有“群體”“民族”“制度”,而少見具體的“人”,特別是傳統(tǒng)的帝王將相、政治人物。從梁氏在議案后面所附6部192課的課題名稱來看,也無一課以人物來命題。
其二,何炳松提出的《編輯或講授歷史應以說明歷代社會狀況之進化案》。何炳松認為:“通史不應偏重政治,不以多列人名地名為貴。”在他看來,過去的歷史教科書“僅述大人與大事,則正如火山大洋不足以代表地理學,虎豹犀象不足以代表動物學”。他主張:“歷史之目的,在于使學生明白現(xiàn)狀之如何遞嬗而來。”⑤何氏雖然沒有如梁啟超那樣,擬出一份專題式“人的隱去”的歷史教科書綱目,他于20世紀30年代編著的初中或高中歷史教科書,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出版商降低商業(yè)風險、爭取最大利潤的羈絆,未能在體裁方面有較大的創(chuàng)新,但何氏強調歷史教學“應以說明歷代社會狀況之進化”的觀點,與梁啟超編纂“普通史”的思路亦有異曲同工之處。
這種關注“國民群體”“社會變遷”“學術派別”而相對隱去具體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的風氣,不僅在上述兩件議案中有所反映,在年會其他一些議案中亦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如1924年第三屆年會(南京年會)上,鄭沛霖提出《小學歷史宜專授近世史案》。在這份議案中,鄭沛霖認為:“小學為國民教育之基礎”,“故近世國內經濟狀況之變遷,交通事業(yè)之興革,民眾心理之急激變化,學術思想之革新進步,與夫現(xiàn)時本國在世界上所占之地位,均所當知”。⑥作者提到了“經濟狀況”“交通事業(yè)”“民眾心理”“學術進步”等,認為這些都是小學歷史課應該講授的內容,然恰恰沒有提及中外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本來,注重書寫人物是中國史書的傳統(tǒng)。中國古代撰修的“正史”大都是紀傳體,以展現(xiàn)人物為基本特色。即便傳統(tǒng)的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史書雖然分別側重記年和記事,然亦都離不開人物。其實不僅在中國,在西方也有重視書寫人物的史學傳統(tǒng)。如古典時代的史學杰作、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os)的《歷史》就被后世認為是“具有強烈的重人事而輕神靈的所謂‘古典人文主義傾向”。直到近代,隨著伏爾泰(Francois Marie Arouet)首倡總體史的研究,19世紀中后期要求改變歷史研究現(xiàn)狀的呼聲此起彼伏,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進一步把這種無所不包的總體史稱為“文明史”,提倡以聯(lián)系和整體的方法去觀察歷史。另一位19世紀的史家米希勒(Jules Michelet)更明確提出史家要重視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氣候、食物、生理和體質狀況以及民眾意識、習俗等在內的大眾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歷史。①這樣從19世紀開始西方史學出現(xiàn)了重要的研究轉向,即由傳統(tǒng)的凸顯人事的事件史向關注社會本質特征的制度史的轉移,成為歷史研究的新趨向。20世紀初年,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在美國史學界發(fā)起新史學運動,其目的是揭示基于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心理的等多種因素基礎上的歷史演進的總體意義。②更為重要的是,新史學意圖與其他學科建立密切關系,使史學成果具有“科學”價值。換言之,就是要推動史學“科學化”。魯濱遜不僅提出新史學的理論主張,而且還在美國廣收門徒進行傳授,由此在美國形成一個頗具聲勢的新史學流派,也影響到當時在美國留學的許多中國學生。因此五四前后中國史學界受其影響崇尚“科學化”新潮就勢所必然了。
在中國近代最早倡導史學“科學化”觀點的是梁啟超。許冠三在《新史學九十年》中指出:近代中國新史學“從新會梁氏朦朧的‘歷史科學和‘科學的歷史觀念起,新史學發(fā)展的主流始終在‘科學化,歷來的巨子,莫不以提高歷史學的‘科學素質為職志”。③誠然,“近代史學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科學化”。④史學“科學化”的訴求,一方面呈現(xiàn)追尋“純粹客觀性”,探究歷史真相,注重通過廣泛搜集資料到資料的詳細考證、再到史學“客觀性”堅持的特點,這既是史家傅斯年所說的所謂“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近代西方史學“科學傳統(tǒng)”的寫照,同時它也是受崇尚訂訛正謬、拾遺補缺的清代“乾嘉史學”影響的真實體現(xiàn);另一方面,史學的“科學化”又是史學研究范圍的重大變革,甚至可謂另起爐灶之更新。因為“以前史家所注意者,大抵不外非常之人,與非常之事。故其所記,偏于政治軍事”。“現(xiàn)今史研究之范圍則較此為尤廣。其所謂史,乃包括全部人類社會演變之過程。舉凡人類之所曾感受者,實行者,思想者,無往而不在史家研究范圍之中。”“現(xiàn)代科學最大之特點,即在其注重極平常之事實,研究極普通之現(xiàn)象;現(xiàn)代史學之趨勢,亦為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變。”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一二非常之人,一二非常之事,固或有推進之功,與阻障之罪,然其重要亦在其影響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歷史上之主人翁,應為平常之人,歷史之主要對象,應為日常生活之演變”。⑤
由此可見,“科學化”的史學由關注帝王將相轉向關注下層社會、普通民眾。在“科學化”思潮下史學中“人的隱去”其實并不是完全沒有人物,恰恰相反,“群體”即由許多人物組成,只是觀察的角度轉換了,由專注于“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偏重政治與軍事的舊史學轉變?yōu)橐詫n}研究為形式、凸顯“平常之人”“平常之事”,揭橥民眾活動與社會、文化演變的新史學。
史學“科學化”的內涵是與時俱進的。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以及夏曾佑、劉師培等人所主張的“科學化”以進化論為標志,注重新觀念的闡發(fā)。而五四前后史學“科學化”的路向發(fā)生很大變化。王晴佳《中國史學的科學化——專科化與跨學科》一文,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國史學界對史學“科學化”認識的轉變,指出:“這一時期,歷史學家逐漸從注意闡發(fā)新的歷史觀念,轉移到注重新的歷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就是“從重視史觀到重視史法(歷史方法)的轉變”。⑥王晴佳的研究頗見功力,讀之受益良多。不過其研究雖提及梁啟超、何炳松等學者,然基本未涉及歷史教育的層面。
1916年已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何炳松對歷史教育的影響不可忽視。1923年,他發(fā)表的《西洋史與他種科目的關系》一文,表達了他對于史著及歷史教育中有關“人”的看法。他認為:“向來歷史家統(tǒng)以文學的眼光去研究歷史”,歷史變成了很有趣的“人物傳奇”,他說:“以傳奇的眼光去研究一段好歷史,那歷史亦就壞了。”①此說表明他不贊成傳統(tǒng)的注重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與此同時,何炳松非常欣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史學教授約翰生·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小學中學中的歷史教學法》一書的觀點。他認為作者屬于魯濱遜所倡的新史學一派,而對于此派的論點,他是很贊成的。②1922年夏他開始翻譯這本書,并于1926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漢譯本,對中國近代歷史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反對歷史教育突出少數(shù)名人,而強調彰顯“社群”的意義。約翰生·亨利說:
差不多所有我們所承認的歷史著作,從希羅多德到現(xiàn)在,統(tǒng)是部分的傳記的。……他們用比較少數(shù)世界上所謂大人或名人來代表人類。君主、將軍、教皇、主教及其他教會里面同國家里面的官吏,繪畫家、雕刻家、建筑家同其他“偉業(yè)事業(yè)”的創(chuàng)造家,遇到公共大事的演說家,對于公共大問題的著作家,當然統(tǒng)是曾經描寫過。……近世所謂傳記,原來以描寫真正個人為目的,敘述他對于社群的功業(yè)或罪惡,以便明白他這個人的重要。③
他認為這種書寫方式頗需商榷,認為歷史應“以描寫社群為目的”,“說明社群的狀況同活動”。對于學校的歷史課程尤其是高年級的歷史課程,約翰生·亨利比較贊成以“制度”為線索來展開社群的歷史。“制度”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工業(yè)的、社會的幾個方面。政治制度的中心是政府,宗教制度的中心是教會,教育制度的中心是學校,工業(yè)制度的中心是職業(yè),社會制度的中心是家庭。他認為這五條線索構成一個整體,學校歷史課程應以此為思路進行改革。④由此可見,在約翰生·亨利所構想的學校歷史課程中,精英人物“隱身”了,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群體所訂的各種“制度”;原來以“個人”為中心的歷史不見了,而民族、國家、宗教、文化等較為抽象概念則成為學校歷史課程的新寵。約翰生·亨利的這些見解對何炳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通過何炳松的譯介,又直接影響到中華教育改進社歷史教學組會議上相關議案的形成。
另一位年會的重要人物徐則陵,似也應當關注。徐則陵當時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歷史科主任,⑤在1922年底成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歷史教學委員會中擔任副主任一職(正主任梁啟超名氣大,社會活動多,掛名而已),成為委員會實際上的負責人。在第一屆年會歷史教學組的幾次會議上,他被公推為會議主席,可見他在歷史教育界的地位。1921年,徐則陵在《史地學報》上發(fā)表《史之一種解釋》,指出史學是研究人類活動的,人類活動包括政治經濟活動、宗教活動、學術活動、美術活動四類。正因為他有與當時西方新史學比較接近的觀點,所以,不但在此時他發(fā)表的文章中能捕捉到西方新史學的印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將此觀點付諸實踐,滲透在他起草的新學制高中歷史課程綱要之中。如在1923年新學制《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學綱要》中,他將歷史知識分為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知識的、宗教的五類,基本上就是在《史之一種解釋》一文觀點的基礎上修改而來的。
不僅于此,徐則陵在《綱要》中設計的116課世界文化史綱目,從標題看只有社會變遷、學術演進、經濟發(fā)展、民族競爭等“群體性”“制度性”內容,而無任何有關個體的“人”的話題。在新學制高中歷史課程綱要頒布之前,徐則陵于1923年5月的《史地學報》上曾發(fā)表過一份《高級中學世界文化史學程綱要》。這份“綱要”與不久正式頒布的高中歷史課程綱要極為相似,大約是其初稿。學者何成剛認為,初稿只有外國文化史內容,而正式頒布的“綱要”增補了大量中國文化史內容,從而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史。⑥這種差異當然是存在的。不過依筆者看來,兩份“綱要”都深受西方史學“科學化”思潮的影響,偏重于“物化”的歷史,而缺少具體“人”的歷史。因此,從學術與教育取向這一根本特質來說,“綱要”的初稿與正式稿并無二致。
至于梁啟超后來改變了他之前的主張,在1926年指出:“近人以為人的歷史毫無益處,那又未免太過。”“若把幾千年來中外歷史上活動力最強的人抽去,歷史到底還是這樣與否,恐怕生問題了。”①因此,又主張要撰寫“人的專史”。不過,這種轉向在20年代似乎并不普遍,至少何炳松等人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如何炳松在1925年發(fā)表的《歷史教授法》文章中,雖然說到以“個人的傳記入手”也是歷史教學的一種途徑,然而作者其實并不欣賞這種路徑,他認為盡管以人物為中心敘述歷史,比較符合兒童的興趣,但是他強調“兒童讀了名士英雄的傳記以后”,“結果不一定如我們所期,而且有時真正模仿起來,非常危險。況且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人不一定是有名的”。何炳松贊成“從社會的全體入手”來展現(xiàn)歷史,認為這種注重“群體”的歷史教學法不但“現(xiàn)在還很風行”,而且“事實亦實在很重要”。他甚至說,即便以“個人的傳記入手”,也須“以一種事實或一種運動為中心”,把有關系的“人”附到這種“事實”或“運動”上去,而不是以“人”為中心。②可見,在何炳松的認識中,“科學”的歷史是不能以“人”為敘述中心的。應該說,這種見識在當時的學界是相當普遍的。
五四前后學界認同“人的隱去”的新史學取向者不在少數(shù),而這種學界的“共識”對教育界的影響,從當時有關小學歷史教育的某些觀點即可見一斑。如小學歷史教師高德泉認為,小學歷史教學關鍵是要敘述“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最精彩的故事”,“至于沒關緊要的‘皇帝家譜等等事實,可以一概不取”。③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王芝九說得更加清楚。他認為:
歷史材料,拿人物做單位呢?還是拿事情做單位呢?——在中國古代史書上,正史是表志紀傳體,其他雜史或為紀事本末體或為編年體,或為別種體裁。小學所用歷史教學的材料,適用那一種體裁,只要看教學的目的,并兼顧兒童的心理狀態(tài)。依歷史的目的說,歷史教學是使兒童知道生活的演進、社會的變遷和世界的趨勢;那么,教學的態(tài)度當然是重在研究;研究的范圍當然是全人類的事物,而且是各整個的事物。倘使只講一人的歷史,如何可以代表全人類呢?所以就歷史教學的目的上看,歷史教學的材料當然要以事情做單位。
并說這已經是“現(xiàn)在的趨勢”。當然他也認為小學低年級可以適當照顧兒童的心理,“不妨參酌以人為單位的方法”,④不過這顯然只是過渡,最終目的還是要讓學生了解“物化”的歷史。可見,他們都認為小學歷史教育的內容不應以具體的“人”為中心,而應重點關注社會變遷、制度演進等比較抽象的歷史內容。這種取向與清末小學堂章程所提的“舉古來圣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鄉(xiāng)賢名宦流寓諸名人之事跡”⑤以及民初小學校課程標準里規(guī)定的“授黃帝開國之功績”“歷代偉人之言行”⑥等教學目標已經相去甚遠了。
學術與教育不可能完全合拍。五四前后受史學“科學化”思潮影響,我國史學界提倡專題研究,注重文化的視角,關注群體、制度等“物化”的歷史,具體“人”的歷史似有“隱退”之勢,然而歷史教學實踐亦有其自身特點,新學制歷史課程綱要也并非剛性的教育法規(guī),而僅為一參考性、指導性文本,因此囿于師資、習慣等多種因素的制約,歷史教學難以真正做到“人的隱去”,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何炳松、陳衡哲等學者編纂的中外歷史教科書仍書寫了許多人物可為明證。不過歷史教育以具體的“人”特別是政治人物為中心的情形也明顯動搖并逐步被摒棄。
雖然晚清的史家已經開始注意撰修本朝歷史,并且編印本朝的史料,史學界治古史的學風已漸有改變,⑦然晚清以降直至五四前后,學界的治學取向似仍偏重于古史。據(jù)史家羅爾綱回憶,他當初上大學時對中國上古史感興趣,也作過一些探索,預備寫一部《春秋戰(zhàn)國民族史》。1931年初,正在胡適家?guī)兔Τ瓕懻砗高z著的羅爾綱,把自己寫成的部分上古史研究內容給胡適看,胡適看后認為羅爾綱用的史料有問題,并說近年的人喜歡用有問題的史料來研究中國上古史,那是不好的,建議羅爾綱改治中國近代史。①可見,30年代初的學風依舊好古,熱衷研究古代史是當時史學界的風氣,偏重古代研究是歷史研究的主流。
史家羅志田在某次接受訪談時指出:
中國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終不曾出現(xiàn)過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學者與史著,個人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尚未累積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斷遭到戰(zhàn)亂與各項變故的阻礙,許多早期的開創(chuàng)性學者如羅家倫、蔣廷黻等人,也都沒能長期堅守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棄學從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發(fā)展,便健全得多,也產生過像陳寅恪、陳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就的學者。②
當時學界普遍不重視近現(xiàn)代史,從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的敘述中大體能概括出兩個原因:一是學者普遍認為古代史是此后歷史的根源,不從源頭著手,支流的真相也不易厘清;二是中國向來有“歷史退化觀”的謬論,以為愈古的時代愈好,到了后世便愈不行。③此外,章太炎認為“近代史之資料雖多,然皆散漫不易搜集,古代史則參考書已成者較多”。④筆者認為還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原因,因近現(xiàn)代史的時間太近,因此相關研究極易受到學界的“學術歧視”。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從20世紀初開始學界就有歷史編纂及歷史教育“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的提倡。梁啟超是較早論述這個問題的。他在1902年的《新史學》中就將過去的歷史著作斥為“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他認為歷史要關注“今務”,“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他說:“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后,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xiàn)。”因此“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fā)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⑤盡管顧頡剛在20世紀20年代以古史考辨而成開風氣創(chuàng)學派的“學術諸侯”,⑥其后又“畢生致力于辨?zhèn)吻笳妗保八墓攀穼永蹣嫵烧f”,“奠定了中國史學現(xiàn)代化之基石”,⑦然顧頡剛本人也說過:
新史觀輸入以后,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后世的文明遠過于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于歷史的觀念。
又說:“史學本來以現(xiàn)代為重要。”⑧另一位史學界頗有地位的朱希祖,在1919年似尚未提倡“以現(xiàn)代為重”的觀點,然其關于整理國故的看法有助于淡化人們傳統(tǒng)的尊古心理。他說:
我們現(xiàn)在講學問,把古今書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學、社會學的方法來治學問。換一句話講,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治學問。⑨
那么,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么當時的學者一方面開始倡導“以現(xiàn)代為重”,至少將古今“平等看待”,另一方面學者又大都熱衷于古代研究呢?除了前述的原因外,似有更深的緣由。史家羅志田認為,受清季革命黨人否定傳統(tǒng)一派的思路及近代傳入的社會進化論影響,五四時期的學者欲將“現(xiàn)代”里的“傳統(tǒng)”送進博物院的傾向相當風行。他說:
當時的趨新士人多認為“現(xiàn)代”與“古代”根本不能兼容,故不允許妨礙吸收“新學理”的“傳統(tǒng)”在新時代里延續(xù),以利于中國人成為二十世紀的“文明人”。
而趨新士人“驅古”的方法就是研究古代,他引用顧頡剛的話說,通過研究古史將“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送進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然后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里延續(xù)下去”。⑩
這種關注近現(xiàn)代的思路在五四以后比較突出,也對五四新潮下的歷史教育產生較大影響。在1922年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的第一屆年會上,朱希祖的提案《中學宜先教地理后教歷史案》認為:“古人所謂藏往而知來,皆以現(xiàn)代為樞紐。既以現(xiàn)代為樞紐,則今日以前之現(xiàn)代史尤為重要。”他批評當時中學歷史教學詳古略今的傳統(tǒng)習慣做法,指出:
吾國現(xiàn)在各中學校歷史教員,不知時間分配之精義,往往詳于上古以至近古,至近世現(xiàn)代史或因時間已無,棄置不講,此真所謂輕重倒置,不識史學究竟目的者也。
因此他建議在教學時間分配上,“上古中古史占二分之一,近世現(xiàn)代史占二分之一”。①此時章太炎的演講也支持“以現(xiàn)代為重”。他在1924年7月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南京年會上作了《勸治史學及史學利病》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列舉了近年史學研究的五大弊端,其中就有“詳古代而簡近代”一條,認為:“近代史非詳于古代不可”,因為“近于吾人生活時之歷史,實與未來歷史有密切關系也”。②章氏的觀點反映了當時學界的一種新的看法,而且以章氏在學界的地位,也有助于歷史教育界認同這樣的新取向。鄭沛霖就認識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國內大勢一變,汽船通航大西洋以后,世界大勢一變。故小學歷史教科書于鴉片戰(zhàn)爭以后之史事,應特別注意”。③事實上,當鄭沛霖在年會上提出《小學歷史宜專授近世史案》以后,很快即贏得與會者的共鳴,后來除了將題目中的“專授”修改為“注重”外,議案在會上獲得通過,并以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名義致函全國各縣教育局通知各校“酌量施行”。兩年后,徐映川還在文章中表示,很贊成“小學史材宜注重近代史的提議和理由”。④可見其產生的社會影響。
受“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新取向的影響,新學制歷史課程綱要的內容也發(fā)生較大的變化。事實上,清末頒布的《奏定中學堂章程》(1904年)即已提出外國史課程須“詳于近代而略于遠年”,對本國史課程則還沒有提出“詳近略古”的要求。但是清末的《奏定中學堂章程》和民初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標準》(1912年)對于本國史課程都已經特別提到“中國百年以內之大事”或“近百年來中外之關系”。可見,《章程》和《標準》的制定者已經開始意識到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不過,“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的價值取向清晰地在中小學歷史教育中反映出來,應該還是五四以后的事。在20年代新學制歷史課程中這種變化就比較明顯。如《小學歷史課程綱要》有關“畢業(yè)最低限度的標準”,在初級水平標準中強調“能知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大概”,在高級水平標準中突出“略知中外歷史有影響于現(xiàn)代文化、政治、社會狀況的各事項”。⑤《初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將“了解現(xiàn)代各項問題的真相”作為重要的教學目的之一。《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學綱要》也強調課程以“現(xiàn)代文化問題為主旨”,“以領會現(xiàn)代為歸宿”,“目光須注射現(xiàn)代”,“近世文化史教材,約須占全部教材三分之二”。⑥可見,“略古詳今”是新學制小學、初中、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的共同傾向。而這種傾向與五四前后士人“破壞舊社會”“反傳統(tǒng)”的努力以及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廣泛傳播顯然是密切關聯(lián)的。當時中小學歷史教育反映學界“關注現(xiàn)代”新取向的意義在于,它將五四學界“反傳統(tǒng)”“推陳出新”的學術取向,推廣到學術圈外,通過中小學歷史教育,促使“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新觀念的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以現(xiàn)代為重”畢竟只是一種史學研究的新趨向,遠非民國時期史學研究的主流。不僅“舊史家”大都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史研究,即便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郭沫若、范文瀾等也多側重古代文史的研究,雖部分學者偶也撰寫一些有關近代問題的論述,然并非其主攻方向。⑦真正實現(xiàn)史學研究“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大約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1958年3月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厚今薄古”,并由此引發(fā)一場新的“史學革命”,導致輕視歷史尤其是古代史的錯誤傾向。⑧當然,1958年的“厚今薄古”有政治色彩,恕不贅言。不過,五四以后從史學趨向上說,確已開啟關注近現(xiàn)代問題的研究之門大概也不容否認。
還須注意的是,教育與學術不同,尤其是中小學教育自有其內在規(guī)律,不可能與學術完全相提并論。事實上,五四以后學界“以現(xiàn)代為重”“略古詳今”的研究新取向是建立在“專題研究”基礎上的。這是五四前后注重“專題”“為學問而學問”學風的反映。對于中學歷史教育,梁啟超雖曾力倡“以縱斷史代橫斷史”,也就是要以地理、民族、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專題史代替近代以來形成的將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世等階段的通史,并且擬了192課專題式的本國史課本目錄,然而梁氏終其一生也沒有能夠編出這樣一部高難度的中學本國史教科書來。①推行新學制改革以后,盡管商務印書館做了嘗試,1923年出版了傅運森編寫的專題式的《新學制歷史教科書(初級中學用)》,并請胡適、朱經農等名人作為校訂人,其書分“歷史以前的狀況”“人類生活狀況的變遷”“人類信仰的變遷”“人群組織的變遷”“人類思想的變遷”“人群的斗爭與連合”“中華民國”等幾個專題敘述,然由于與初中生的學習心理與能力脫節(jié),出版后不但招致一些非議,而且出版社大都也不再出版專題史教科書。新學制初中歷史課程綱要所列課題,近世史的比例只占全部內容的四分之一,且仍將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幾段;高中歷史課程綱要中屬于近百年來的歷史僅占五分之一,且雖未劃分歷史階段,然時段性仍然較強。可見,五四新潮下的歷史教育對史學新取向的反應并不是激進的“全盤照搬”,而是多少保留了一些“傳統(tǒng)”的。
史家羅志田在《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一書中認為,對于北伐前的民國來說,五四運動是一個分水嶺,大致將此前和此后的時代潮流作了區(qū)隔,并認為“五四”后知識界的傾向是“知有國家更要知有個人和世界”。不過從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歷史教育改革議案來看,20年代初期人們的“群體”“國家”意識似乎仍相當有強勁,換言之“人的隱去”和“群體”的凸顯仍舊為歷史教育的主基調之一。另一方面,在具體設計新學制歷史課程的過程中也展現(xiàn)出“新潮”與“傳統(tǒng)”之間的某種調適關系。當然“向西方學習”,服膺、傳播西方新史學理論與方法是近代中國士人的共同取向,但是這種新史學革命可能并非完全“在傳統(tǒng)之外變”,②至少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的有關歷史教育的改革議案及其實踐中就能清晰觀察到“傳統(tǒng)”的力量以及“新”與“舊”的調和。
【作者簡介】朱煜,揚州大學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與教育研究、歷史教育學。
【責任編輯:楊蓮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