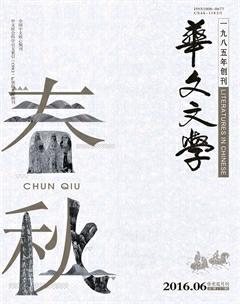論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
曾令存
摘 要: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與寫作已走過半個多世紀。顧彬關于1949年后中國文學(即當代文學)的敘述,一方面難于走出海外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界普遍存在的通過中國文學來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社會學思維怪圈,另一方面,他對當代文學“經典”的認證及其所作的“習慣性標準”(語言駕馭力、形象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與現代政治學意義的詮釋,又對我們考察海外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具有啟發意義。《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是一部“問題文學史”。這個“問題”,既是指其文學史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是指作為一種言說方式的文學史敘述模式。
關鍵詞:海外漢學;當代文學“經典”;現代政治學;文學史敘述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6)6-0024-08
一、海外漢學的文化身份與文學史立場
討論海外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海外漢學”,以及由此引伸出來的“多重文化背景”、西方價值觀念等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不過在有關海外(境外)的文學史家的介紹中,除了夏志清(1921-2013),對于像司馬長風(1920-1980)和林曼叔①等,我們并沒有特別展開這個問題。這里牽涉到如何理解“海外漢學家”內涵的問題。在質疑與批評大陸意識形態、主張“反共就是民主”②方面,不少海外漢學的態度與立場并無明顯的不同,區別只在于程度的輕重和表達的隱顯。但對海外漢學來說,更具標識性的,還是其文化背景與價值判斷,以及研究中國問題征用的理論資源、使用的語言等。夏志清、司馬長風和林曼叔都出生于中國本土并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教育。但與后面兩者不同,夏志清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后,在以后半個多世紀的人生里,基本在美國工作、生活,用英文研究與寫作,其思想政治立場、文化價值觀念,特別是文學研究理論體系等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去中國化”。換句話說,在夏志清,美國(西方)的政治、文化對其文學研究的影響程度已遠遠超過了中國傳統文化。這與司馬長風和林曼叔有很大的區別。在香港,除西方殖民文化外,對港人價值觀念與人生態度及日常生活影響比較大的,除了對大陸若即若離的政治立場,中國文化中的大眾——市民文化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林曼叔雖然有過短暫的法國留學教育經歷,但從本質上看,仍不足以構成其“海外漢學家”的身份,“是道地的香港文學評論家”(古遠清)。因此用“海外漢學家”來描述司馬長風和林曼叔的文化身份,顯得并不充分。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評述他們的文學史寫作過程中沒有過多考慮“多重文化背景”的原因。
但顧彬的情況顯然與上面三位文學史家不同,是個典型的“海外漢學家”。而作為一個漢學家,顧彬與“中國”的關系頗為復雜,主要表現在如下三方面:一是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起步比較早。若從1967年接觸李白開始算起,顧彬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已近半個世紀。1974、1975年,顧彬借到中國和日本學習之機,開始接觸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二是作為一個德國漢學家,顧彬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特別是最近十多年來,顧彬在中國非常活躍,包括受聘在許多高校講學、參加相關的文學活動,在中國內地文藝刊物發表研究文章等。三是顧彬早年求學生涯中對宗教神學的研究,也使得他的精神思想資源有別于其他海外漢學家。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前言”中,顧彬曾坦言他在嘗試借文學這一模型去寫一部“20世紀思想史”。若論文學的宗教表達,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顯然要弱于五四新文學。然而在將宗教作為考量中國文學的思想深度與“世界性”的一個籌碼方面,顧彬卻比上面三個文學史家中最熱衷于文學創作的“宗教含量”的夏志清還要執著,以至于給人一種當代文學研究的“泛宗教神學”之錯覺。如何評價這一現象,我們在后面還會作進一步的討論。但這種情形不能說與顧彬宗教神學的研習背景毫無關系。
因此,若論海外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多重文化背景”,顧彬作為個案無疑更具有代表性。與其他文學史家比較,顧彬似乎并不習慣系統地闡述自己的文學史觀念與立場,而更喜歡將自己這種復雜多重的文化身份和文學史立場化解在具體的文學史書寫過程中。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斷斷續續的表述中梳理出顧彬未必成體系的文學觀念。比如顧彬說他和他的前輩們在文學史書寫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與選擇”。他認為文學史寫作不是簡單的“報道”,而是“分析”:“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為什么它會以現在的形態存在,以及在中國文學史內外區分類似的其他對象?”③在文學史寫作的意識形態立場上,顧彬也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偏見,但同時又坦言自己對20世紀作家作品的“偏好與拒絕”都僅代表他個人。“如果它們更像是偏見而非判斷的話,肯定也要歸咎于中國在20世紀所處的那種復雜的政治形勢。”在此前提下,顧彬強調他本人評價中國文學的依據主要是“語言駕馭力、形象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這三種“習慣性標準”。④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顧彬用“國家、個人和地域”三個關鍵詞來描述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即中國當代文學)。這三個關鍵詞所指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內涵,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還是歷史主體的。顧彬指出,由于國民黨退往臺灣、東西方冷戰等政治原因,導致了1949年后中國文學的分化和國際化,同時,對1949-1979年中國大陸文學評價的一變再變,都使得曾經被文學史家們視為邊緣的臺港澳文學沒有理由再受到忽視。因此,討論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我們不應該再局限于大陸本土。顧彬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敘述,首先“從邊緣看中國文學:臺灣、香港和澳門”開始,并重點介紹了臺灣五六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懷鄉文學”(顧彬稱之為“機場文學”)、“現代主義文學”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賴和、白先勇、林海音、陳映真、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王文興等。這種“從邊緣看中國文學”的文學視角,旨在擴展人們考察中國大陸文學的“邊緣”視閾,更為我們評價一變再變的1949-1979年中國大陸文學提供另一個背景。對于1949年后的中國大陸文學,顧彬以1979年為界分為兩個階段進行考察:在第一階段(1949-1979),顧彬重點分析“對個人的聲音越來越形成壓迫”的“公眾意見”;⑤在“隨著開放政策而展開”的第二階段(1979—),則“詳盡地挖掘”逐漸取代“公眾意見”的地位并在世紀末成為“主導聲音”的“個人聲音”。⑥這第二階段又以1989年為界線,分為“人道主義的文學”和“商業化的世紀末文學”。
應該說,顧彬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期,本質上還是一種政治化的標準。但與始于大陸1950年代那種狹隘的政治化文學史分期觀念不同,“時間”在顧彬這里更重要的所指,卻是“現代”思想文化與藝術審美層面上的,甚至還是“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這也是顧彬分析和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起點與平臺。比如顧彬認為1949-1979年這一時期,中國的文藝美學和西方大眾文化的訴求差不多(“后者要求取消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差別”)。因此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像德國那樣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學,把這一時期中國文學作為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素材的研究是有問題的。他認為必須從“現代性”的高度來看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因為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開始就是一個現代國家,只是這個“現代”有別于西方的“現代”(不僅利于國家,更得利于個體獨立人格的獲得)。顧彬指出,1949年后的中國需要一種具有“整體感”的“集約性(totalitaristisch)的現代”,以建設一種新的整體秩序,而不是一個包含著國家與個體的成分的“曖昧含混(ambivalent)的現代”。個體的解放必須讓位于民族國家,“‘現代本身的含混內涵讓位于清晰的思想觀念”。顧彬認為在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中,“文本”和“作者”這一對概念必須統一起來,以前作家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已不再存在。“如今,作品內容就是世界觀,世界觀就是要和國家政治路線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路線的改變才能導致對世界觀評價的改變——或者過時或者超前。這種概念的結果是,再沒有人嘗試不同的視角,再也不存在陰暗的心靈——如果有,那就站在了敵人一邊。”⑦在這種視角下,顧彬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成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理論,中國的現代性也由政治領域擴展為一種“美學上的宗教”;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這些概念的組合看似未免有些古怪,“但是據說可以用來克服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中相抵牾的負面成分,永不停息的叛逆者可以借以發揮革命想象力,在一個不斷推翻自己的社會秩序中把革命趨勢推向前進。”⑧顧彬認為這一時期的作品構成了自有的美學體系,它既有助于“認識毛主義的內在性質”⑨,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197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
基于這樣一種文學立場,顧彬對1949年后中國文藝界不斷發動的批判運動試圖給予“更深層次的理解”。顧彬認為,由于反對的力量過于強大,儒家學說在1949年后并沒有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同時,似乎也沒有其他的意識形態或者宗教可以勝任,唯有共產主義在長時間內提供了某種平臺。盡管共產主義宣稱是純粹的世俗性質,卻只有在超越性的基礎上才可能解決主權和道統的問題,因此必須對傳統學說——其中也包括基督教學說——進行世俗化改造。”⑩顧彬的這種理解,雖然看起來有些過度宗教化,但他試圖從宗教哲學、政治學的層面理解文藝批判運動本質,這比簡單、狹隘地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進行解釋,也許更能夠給人啟發。
二、當代文學“經典”的序列及其認證
顧彬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敘述與評價,在文學史的結構方式和文學創作的評價標準方面,都與大陸和臺、港的文學史家有很大的不同。這可能與他海外漢學的文化身份、文學觀念與立場有關。比如大多數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都比較重視文藝運動和文藝思潮,包括林曼叔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但在顧彬的文學史敘述中,如果不是因為與“文學史的轉折點或者某些人的生平”有關,一般都很少提及,顧彬認為“對文藝運動的關注很容易使敘述偏離文學發展本身”。{11}換言之,顧彬的文學史更關注文學創作。而對構成文學史主體的作家作品的評判標準,顧彬也與其他的當代文學史家不同。比如盡管“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但顧彬還是比較警惕把1949-1979年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作為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素材,“把文學貶低或者抬高為社會學材料”{12}。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前言”中,顧彬強調自己評價中國文學的依據(“習慣性標準”)主要有三點:語言駕馭力、形象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在這種評價機制中,當代文學的“經典”——在這里也許用“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概念更合適——在其文學史敘述中被進行了重新認證與詮釋。暫且不論這種“經典”認證與詮釋是否權威、具有說服力,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顧彬的這種文學史觀念與寫作立場直接導致當代文學版圖的重繪,以及這一重繪的當代文學圖景透露給我們的信息與思考。考慮到對1979年以后中國文學評價的時間距離還不夠充分等因素,我們在這里不妨以1949-1979年為考察的時間區段,看看顧彬是怎樣通過對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認證與詮釋分解自己的當代文學史觀的。
與其他當代文學史著作不同,大概是受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戰爭意識”的研究成果的啟發,{13}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用“文學的軍事化”來形容1949-1979年的中國文學狀態,同時用“需要體現國家意志,需要塑造‘普通人代表黨和人民的聲音”的“戰爭美學”來概括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品質,并闡釋了這種美學的核心觀點。{14}其實這種概括和表述并不能完全自圓其說。如認為這一時期“文藝的方案來源于軍隊,而軍隊敵我兩軍對壘爭奪‘新社會的根本思維影響了政治以及文化”{15},這種情況顯然不是事實的全部。不過就其文學史敘述而言,更有意義的還是有關展示這一時期文學風貌作家作品的選擇與詮釋。這對我們考察海外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有重要意義。
根據時間的推移,同時結合作品表現的主題,顧彬選取了1949-1979年間不同時期的創作情況進行考評:敘事文學(土地改革、戰爭、歷史題材)、百花齊放時期文學、歷史劇和民族性文學、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其中在文學史正文中重點分析的作家作品和主要提到的作家或作品統計如下(以在文學史中出現的先后為序):
敘事文學:土地改革小說——重點分析的作家作品:趙樹理《三里灣》(1955)《“鍛煉鍛煉”》(1958)、周立波《山鄉巨變》(1957)、張愛玲《秧歌》(1954);同時提到作家:李準《不準走那條路》(1953)、柳青、王汶石;戰爭小說——重點分析的作家作品:茹志鵑《百合花》(1958);同時提到作家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戰役”》(1954);歷史主題作品——宗璞《紅豆》(1957)、老舍《茶館》(1957);
“百花”時期文學:重點分析的作家作品: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956)《青春萬歲》(1956)、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1956)、毛澤東舊體詩詞(《水調歌頭·游泳》,1956)、李準《李雙雙小傳》(小說,1959;電影,1962);同時提到作家作品: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1956);
歷史劇:吳晗《海瑞罷官》(1961)、郭沫若《蔡文姬》(1959)《曹操》(1959)、曹禺《膽劍篇》(1961)、田漢《關漢卿》(1960);
民族性:《阿詩瑪》(1954)、老舍《正紅旗下》(1961-1962)
文革時期文學:楊朔《西江月》(1963)、浩然《艷陽天》(1964-1966)《金光大道》(1972-)、豐子愷《緣緣堂隨筆》(1971-1973)、郭路生《相信未來》(1968)《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1968)、北島《波動》(1974)《回答》(1973)《宣告》(1980);同時提到作家作品:鄧拓雜文、傅雷家書、賀敬之、劉白羽、革命樣板戲、張抗抗、賈平凹、將子龍、多多。
為了更全面了解顧彬對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取舍,我們再將其在文學史正文注釋中提到的其他作家或作品按先后出現順序簡單統計如下:梅志《在高墻內:胡風和文化大革命》,《沈從文全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18-26卷),胡風《時間開始了》(1949),柳青《創業史》(1960),草明《原動力》(1949),王汶石《風雪之夜》(1956)《春節前后》(1956),老舍《龍須溝》(1950),袁靜、孔厥《新英雄兒女傳》(1949),曲波《林海雪原》(1957)、《智取威武山》(京劇,1971),吳強《紅日》(1957),羅廣斌、楊益言《紅巖》(1962),楊沫《青春之歌》(1958),《重放的鮮花》(1979),秦兆陽《農村散記》(1957),姚雪垠《李自成》(1963),鄧拓《燕山夜話》(1963),鄧拓、廖沫沙、吳晗《三家村札記》(1961-1964),孔捷生。
從上面的整理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就這一時期(1949-1979)的中國文學創作文學而言,顧彬涉及的面其實還是很有限度的。對于這種情況,也許我們只能從他評價中國文學的三個“習慣性標準”(語言駕馭力、形象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來理解。顧彬認為“1949年后大多數作家的語言貧乏格外引人注意”{16}。但從我們接下來將要展開的關于作者對這些作家作品內涵詮釋、評價的情況看,似乎又并不完全如此,也就是說顧彬并非簡單地從作家主體與文學本體角度來解讀這些作家作品,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還是主要的。我們由此可以疑問,這些作家作品能夠真正代表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嗎?如果不能,那么作為一個文學史家,顧彬對這些作家作品的把握與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說他通過這些“經典”的認證重繪的當代文學版圖是有些殘缺、失衡的。這種殘缺與失衡,作為關于這一時期中國文學的文學史敘述,在如下兩方面可能更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對這一時期當代文學創作的文類的處理。首先是作為這一時期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詩歌。在1949年后的文學史敘述中,顧彬除了重點提及毛澤東舊體詩詞和文革時期食指、北島的詩歌以外,其他詩人詩作基本忽略不計,像郭小川甚至連名字都不提,賀敬之也僅是在評述食指早期詩作的價值體系時通過注釋簡單引介其《放聲歌唱》。“從邊緣看中國文學”,將對象置放于百年的歷史視閾,1950-70年代大陸詩歌創作的乏善可陳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并不能夠作為將大陸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進行簡約化處理的理由。這樣的文學史敘述的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其次是小說。如果并非簡單地從作家主體與文學本體角度來表現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史,如果想借助文學更深入地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變化,1950年代中國農村土地革命的內涵,就沒有理由撂下《創業史》。類似情形還有關于1960年代初的短篇歷史小說創作。除了文類處理的問題,再就是文學史敘述的權重問題。直接地說,作為一部敘述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文學史著作,用近7個頁碼(第300-305頁、309-310頁)的篇幅來討論一個1949年后中國文學的詩人及其創作,顯然是失度的。這與其說文學史可以有自己的權力,倒不如說文學史寫作應該如何更好地遏制“權力”,“擱置評價”,以一種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知識學立場和方法來面對歷史。文學史寫作與文學評論的根本區別在于,面對繁蕪的文學現象,文學史家更應有一種歷史的識見,尤其是面對時間距離太靠近的“當代”文學。“放縱”自己的“正見”,有時可能恰恰是對歷史的“偏見”。
王瑤曾經談到寫文學史與編“作品選讀”不一樣,后者可根據某一種標準或者某類讀者的需要,因此沒有入選的不見得就不好。但文學史不同,講與不講一個作家(作品),“無論繁略都意味著評價”;文學史認為這個作家是杰出的、偉大的,“都有和其他作家的聯系比較問題”,這與文學批評就某個作家作品進行分析的不同的。{17}
當然,面對當代文學史的書寫,情況可能要更為復雜一些,這正如顧彬自己所說:“當代不允許特別的距離存在,因此一個最終評價常常難以做出。”{18}因此,顧彬對當代文學“經典”的重新“認證”是否能夠成立,仍是一個問題。
三、現代政治學與“習慣性標準”的作品詮釋
與當代文學“經典”認證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關于“經典”的詮釋。在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已走過半個世紀的新世紀初,顧彬的文學史寫作有繼承,也有超越。比如與夏志清一樣,顧彬也比較注意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考量中國當代文學,注重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學格局中的位置。特別是對新時期文學的評述,從“傷痕——廢墟文學”{19}的比較到高行健、莫言對西方現代戲劇與小說的模仿與借鑒,我們幾乎隨處都可以感受到顧彬在評析中國新時期文學過程中的西方文學維度。又如關于作家作品解析的宗教視角。他對一些文學現象的分析常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以浩然和他的作品現象為例。對浩然文革時期圖解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金光大道》中的人物只要引用毛澤東的話,字體即換成粗體字的做法,顧彬認為也許是借鑒了《圣經》,因為經書中耶穌和保羅的重要話語耶穌通過字體以示突出。另外顧彬還認為浩然小說標題中的“道”和“光”也具有某些《圣經》的色彩,“符合認知過程的敘事結構”和“‘尋找的敘述技巧”。{20}在類似宗教狂熱的文革語境中,顧彬的宗教角度闡釋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而對這種狂熱的文革文學的緣起,顧彬也不乏宗教視角:“神學和哲學認為,聽和說構成了世界的基礎,雖說這種看法在中國只是有限成立,但我們仍可以想象,如果作家不再是人民的喉舌,將必然造成災難性的局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個黨派只想從臣民口中聽到自己的聲音,那它就是通過以自己的觀點代替所有人的觀點重復自身。人們在別人身上看到的不是別人,而是自我塑造的自身形象。于是,他者成為自身的延伸。”{21}
不過在作家作品評析的“政治化”這一點上,顧彬雖然有所“警惕”,但終究還是“力不從心”,難于走出海外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界普遍存在的通過中國文學來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社會學思維怪圈。顧彬與夏志清、司馬長風和林曼叔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其提出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三個“習慣性標準”(語言運用、形象塑造、作家獨立思想),二是具有宗教神學性質的現代政治學價值體系。下面我們據此來看看與其他海外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者比較,顧彬對當代文學作家作品評析的“共識”與“異見”。
先來看看“共識”。有意思的是,在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寫作中,海外學者這些“共識”往往容易招來大陸同行的異議,質疑與批評。這其實與想象中后者的“黨性原則”與立場并沒有什么關系,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些海外學者并沒有真正讀入“現代的中國”,常常懷抱著太多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政治偏見,或者是純主觀揣測的研究立場。顧彬在這一點上似乎也宿命難逃。比如顧彬指出與現代文學比較,當代文學關于關土改題材的創作思路已經發生了變化,“小說不再以作家親自進行的社會調查為基礎,而是黨的路線”,{22}并舉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23}為例;認為1950年代的戰爭小說常以傳播“沒有戰爭就沒有新中國的成立”為己任,{24}歷史小說的任務是“按照黨的觀點敘述現代歷史”,是“世界觀又是教育材料”,講述“革命是如何在黨的領導下發生的?”是歷史小說的主題,{25}將歷史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卸職進行“無縫對讀”,{26}認為“傷痕文學”是一種“說客文學”,“一方面為自己說話,另一方面為黨說話,企圖藉此既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又不受特別的政治壓力”,{27}等等。不過相比較于其他海外文學史家,顧彬的情況還是要復雜一些,即對所選擇作品的分析并不都是強詞奪理和牽強附會。這也許與其政治學理論的現代性思想和解讀方法,以及對作家“個體精神的穿透力”的關注有關。比如顧彬認為雖然《山鄉巨變》中的村長“完全是圖解黨的概念,但是作者多處成功描繪了人、鄉村和風光。在這些描寫中,傳統的敘述代替了意識形態”。顧彬指出周立波“花了250頁的篇幅,描寫湖南一個落后鄉村的農民哄搶自己的財產,躲避上交合作社,只花了15頁的篇幅大致描寫了一下合作化運動獲得成功”,以證明“當時的政策并不受人歡迎”。{28}他肯定《“鍛煉鍛煉”》,認為趙樹理也沒像其他作家那樣,“以土改的政治文件為范本來展開階級斗爭情節,而是通過生動的人物形象描寫矛盾”,指出小說“介于堅持黨性和直言批評之間”。“如果顛覆性地閱讀小說,趙樹理或者小說敘述者就是在批評干部為了出成績而利用廣大群眾、欺騙部分群眾。”因此,小說的價值除了“自然流暢的語言”,“就只有體現在提出問題方面”。{29}顧彬盛贊張愛玲的《秧歌》是此類題材(土改)中“唯一值得嚴肅對待的作品”,可以成為“傳世之作”。{30}不過顧彬認為我們不應該把《秧歌》看做是“反共作品”的結論簡單化,指出小說更深刻的意義還在于,作者對于譚金根一家三口在朝鮮戰爭(即土地改革和合作社)期間以饑餓為中心的人間戲劇描寫結局的“戲劇性反轉”:與1949年以前同類題材(農民因饑餓反抗)的創作比較,同是“大團圓”式的喜劇結局,后者包藏的卻是悲劇。“秧歌”的功能在這里已經發生了轉換,具有強烈的反諷意味:“過去的事情將要改變,過去的東西將被視為垃圾。”{31}
類似這種另類但不失啟發性的詮釋在書中還不少。比如顧彬認為《李雙雙小傳》其實是丁玲《三八節有感》所討論主題的繼續:男女分工、婦女解放、男權主義問題等等。不過由此延伸認為小說符合毛澤東“打倒權威”(包括在兩性關系上)的觀點也許是一種過度闡釋,差強人意,以及認為小說尋找的“中國本色”性質的“民間”(“既指小說的行動主體,也指其中的思想觀念”),是李準與毛澤東(舊體詩詞創作,顧彬認為樹立了一種“體現中國傳統學說的美學范例”,在形式上“披上中式的外衣”,“同時服從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32})的“共同之處”:“兩人都滿足了時代提出的理論要求,即以中國傳統和民間文化為基礎進行文藝創作。”{33}又如,顧彬以食指《相信未來》為例,認為其詩歌在寫作風格詩人雖然受賀敬之的影響,但又與賀敬之有本質的不同:在食指詩中,對政治體制的歌頌已被在那個時代很容易成為犧牲品、無人支持的“愛”、對生命的愛所替代,詩中所表達的對未來的“疑慮”——“昨天才被暖化的雪水/而今已結成新的冰凌”,這種價值體系不僅不同于賀敬之的,也不同于文革流行的。另外,食指的詩在形式上雖然也受賀敬之影響,但注意通過重復和變換手法化解賀敬之抒情詩中的“空洞的激情”。{34}他認為舒婷早期詩歌的特別之處在于那種不僅以女人為受難者的關于人的苦難意識;與北島對年輕一代“略有保留的支持”不同,舒婷對自己這一代寄予很大希望;但顧彬指出,舒婷的詩并沒有嚴格體現朦朧詩的特征:“她的懷疑并不徹底,她的反抗也不危及體制,她的現代性容易理解,她揭露社會現實的需求并不激烈,她通過對個人的關懷來體現自我和人民之間命運與共的同一關系。”{35}
顧彬的當代文學作品解讀雖然沒有擺脫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家的政治化立場,但其以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的現代性意識,使他的作品解讀視界高出于其他文學史家。這種理論意識與其關于作品語言運用、形象塑造和作家個體精神穿透力的評價標準結合,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關于1949年后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活力與張力。從效果上看,顧彬對當代文學“經典”的認證與詮釋,形式與內容并沒有絕然分開,在關注作品內容與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內在深層關系的同時,顧彬并沒有放棄對這些作品形式的考量,即便是對周立波、趙樹理、李準、茹志鵑、老舍、食指、舒婷、王蒙、高曉聲等這些與主流意識形態貼近的作家。而像張愛玲、北島、楊煉、高行健、莫言等,顧彬關注的程度似乎更高,要求更高。也更注意挖掘其價值。他肯定《秧歌》語言簡潔,“近乎報告體,仿佛不含任何觀點”,但表達作者好惡的“象征性的場景以敘述者的口吻一再出現”;{36}認為《百合花》的寫作技巧要高于《紅豆》;贊賞老舍《正紅旗下》“細膩的反語,以及由細微處觸摸歷史大動脈的手筆”,認為正是這些構成了老舍的“高超敘述技巧”;{37}認同北島小說與詩歌的創作就是要“突破語言的牢籠”,打破“毛體”,特別是詩歌創作并列手法(蒙太奇)的運用;肯定翟永明《女人》詩歌語言的問題意識;推崇楊煉對詩歌語言的改造,感覺“就好像開創了一派詩風”。{38}關于高行健、韓少功、阿城、莫言這些介于“尋根”與“先鋒”之間的作家,顧彬在關注他們創作內容的同時,似乎更看重他們的語言表達與形式創新,包括對西方文學大師敘述技巧的借鑒與轉化……
也是在從語言運用到作家個體精神穿透力的考量標準中,顧彬看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當下”與“未來”——“不容樂觀”的未來,指出在“將文學標準和商業成績成功地結合在一起”方面,王朔遠比余秋雨《文化苦旅》要“好得多”。顧彬認為即便是在商業時代,王朔仍然是一個政治性作家;在敘述技巧方面王朔并非無可取之處,但這些都不足于改變王朔是當代“嚴肅文學的掘墓人”。在顧彬看來,在王朔那里已“那里失去了對于奠基性前輩的尊敬,不管是在政治還是文化領域。緊隨其后的是‘惡心的勝利進軍。自此而后,‘下半身主宰了中國文學舞臺,市場就是其同謀。”{39}
但是,顧彬認為,看似“不容樂觀”的中國文學,希望還是存在,“在那些強調對于語言的責任感并朝此方向去行動的少數詩人那里。”{40}在這里,語言再次顯現在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希望的寄托中。
四、充滿質疑與不確定性的文學史敘述
文學史的系統性與知識性特點對文學史編纂者的語言應用其實是一種潛在的制約。文學史家應該有自己的獨立品格,如文學史觀念、對作家作品的理解等,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不同,文學史語言更趨近于客觀與理性,避免過度主觀情緒化。文學史的內容展開應該是一種陳述,史家的疑問完全可以通過思想的過濾隱藏在冷靜的陳述之中。但恰恰在這方面,作為一種敘述風格與敘述模式,顧彬當代文學史的語言運用引人關注。在這里,陳述依然是一種基本的敘述風格,盡管書中也不乏一般文學史少有的那種斬釘截鐵性的表述,這從其大量使用的感嘆號中即可感受到。就文學史語言而論,顧彬的當代文學史書寫更引人關注和感興趣的,還有隱含著敘述者困惑的疑問句,以及敘述過程中對“或者”、“也許”、“抑或”、“如果”、“姑且”等模糊、假設性詞語及相關句式的使用。對于這種充滿質疑和不確定性的文學史敘述,我們當然可以從研究的一般常識和規律出發給予解釋,因為沒有質疑和批判,就不可能有超越和創新。我們還可以從敘述者自身的思想者角色意識予以解釋。顧彬在“前言”中就曾表達過“借文學這個模型去寫一部20世紀思想史”。但作為文學史,作為一種文學史敘述模式,如何評價顧彬這種沒有經過內化的敘述?{41}問題的解答,也許只有回到具體的“當代”與“文學”的語境中來。而如下兩方面的原因尤為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政治因素。這既表現為對當代中國政治對文學的影響產生的隱晦難于把握,同時也表現為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對相關作家作品等文學現象的意識形態解讀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二是時間因素。即“當代”的時間距離問題。用我們前面引用的顧彬話來說就是:“當代不允許特別的距離存在,因此一個最終評價常常難以做出。”這種“顧彬式的‘猶豫不決”,即在當代文學史寫作過程中對一些問題的多義性與不確定性把握的矛盾與困惑,使得顧彬的文學史敘述在客觀效果上,具有一種緊張感與陌生化效果。也使得文學史在敘述與閱讀之間形成一種潛在的對話關系。
下面我們不妨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1949年后中國文學的敘述中節錄出比較有代表性的若干片段,“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片段一:關于茹志鵑的《百合花》。作者在對小說情節與人物性格進行分析后提出:作為描寫“死亡與愛情”的作品,“這里究竟誰愛上了誰?”“新媳婦為什么要看上通訊員?”“或者這個故事講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愛情,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42}
片段二:關于北島的《回答》。顧彬指出:“讀者讀完這首詩首先提出的問題自然是,詩中究竟誰問誰答?更重要的問題是,問的究竟是什么?是第二段中通過兩個問句要求開放之后的更大開放嗎?我們暫只能得出以下判斷:詩中發言者是以文革中所有受害者的身份進行回答,最后甚至是在對全人類喊話。”{43}
片段三:在介紹“人道主義的文學(1979-1989)”
的時候,顧彬疑問:在1979年后的中國文學中,“‘人這個容易引起政治敏感的字為什么會獲得如此的重要性?”{44}
片段四:關于北島的《宣告》。與把《回答》的寫作時間向后改動不同,北島把寫于1980年的《宣告》的時間往前推移到文革期間。按照顧彬的說法,這首詩讀起來像是遇羅克遇難前的宣告。顧彬的問題是,詩人為什么要在寫作日期修改上面“做文章”呢?顧彬試圖根據自己掌握的有限資料予以探究,但仍不敢確定結論是否有效。在顧彬看來,這些推測并不能作為“解讀北島的可靠資源”。{45}
片段五:在談到王安憶1980年代中期的“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與女性文學的問題時,顧彬指出因為王安憶“始終不厭其煩地從自傳角度解讀自己的作品”,使得對她的作品進行正確評價變得很艱難。“有些評論甚至指名道姓地列舉某人是王安憶作品中的某情人原型。”顧彬不能理解的是:“難道大家真的很想知道這些嗎?”對于不少人說張賢亮是《錦繡谷之戀》中的情人原型的情況,顧彬認為這種說法反倒令人生疑:像張賢亮這樣對女性懷有荒唐想象的男作家難道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46}
片段六:在評述新時期“改革文學”代表作家高曉聲和他的《李順大造屋》時,顧彬指出小說敘事者曖昧的態度把讀者引入一個兩難的窘境。“帶著這幾句非政治的結語,主人公告別了讀者。那么敘述者呢?了解了主人公所有事情的他,是站在主人公這邊,還是站在帶來了偉大承諾的改革者這邊?”在經過一番辨析后,作者指出:“在這兩種觀點之間作一個最后裁決,也許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因為說和寫有時需要模棱兩可,以便能夠表達一種不同意見。”{47}
片段七:在“展望:20世紀末中國文學的商業化”中,顧彬提問:“越得我們接近20世紀的末尾,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什么是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所特有的,什么不是;什么是要緊的,什么又不是。”{48}
從這種意義上,說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49年后的中國文學》是一部“問題文學史”,未嘗不可。這個“問題”,當然不僅是指其文學史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還是指作為一種言說方式的文學史敘述模式。
① 林曼叔(1941-),廣東海豐人,1962年旅居香港,1978年赴法國深造,長期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現為香港《文學評論》主編。著有《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 大陸部分)》、《魯迅論稿》等。
② [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頁。如下所引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此版本。
③ [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序”。
④ [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前言”。
⑤顧彬并沒有對“公眾意見”內涵進行闡釋。但從其文學史語境看,“公眾”背后的主體應該是國家、政府,“公眾意見”則是代表國家(政府)意志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
⑥⑦⑧⑨⑩{11}{12}{15}{16}{18}{20}{21}{22}{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 [德]顧彬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第263頁;第254頁;第282頁;第255頁;第256頁;第315頁;第255頁;第272頁;第26頁;第325頁;第294頁;第294頁;第267頁;第270頁;第272頁;第287頁;第311頁;第267頁;第268、269頁;第268、269頁;第268、269頁;第282頁;第285頁;第297頁;第313頁;第269頁;第290頁;第334頁;第365-366頁;第366頁;第272頁;第301頁;第307頁;第305頁;第322頁;第328頁;第351頁。
{13} 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陳思和的《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該文曾收入陳思和《雞鳴風雨》,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14} 顧彬解釋這種“戰爭文學”的美學核心觀點有四點:(1)文學和戰爭的任務一致;(2)必須進行史無前例的革命;(3)文學水平的標準是戰士即人民群眾(大眾文化);(4)文藝工作者之所以來著大眾是基于戰爭經驗(業余藝術家)。[德]顧彬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第263頁。
{17} 王瑤《關于現代文學研究的隨想》,《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頁。
{19} “廢墟文學”是顧彬為評價新時期“傷痕文學”從相關研究資料中援引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由德國伯爾的《廢墟文學自白》提出。參考《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第285頁。
{23} 顧彬(抑或是翻譯者)似乎太“粗心”了,把小說題目錯寫成《不能走那條路》。
{41} 顧彬文學史敘述的這種質疑和不確定性,類似于洪子誠《我們為何猶豫不決?》(《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洪子誠這里談到的“猶豫不決”,并不簡單局限于當代文學的評價方式、價值判斷等學科的范圍,同時還關涉知識分子的思想立場和對當下社會現實等問題的回應。有關闡述可參考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部分的內容。另外,在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冷靜、理性的敘述語言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其強烈的問題意識。
(責任編輯: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