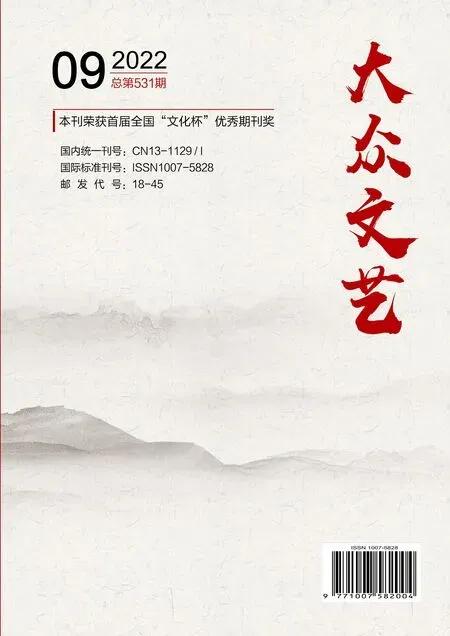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質物本心”
——本人陶藝創作的三個階段
張 春 (湖北美術學院 430060)
“質物本心”
——本人陶藝創作的三個階段
張 春 (湖北美術學院 430060)
“質物”是物質的本源,“本心”是我創作的初心。本文主要圍繞“物質”之本源,“我心”之初衷為話題展開自己十年陶瓷創作之路中對現代陶藝創作的理解。也希望通過對自我創作的梳理,總結并歸納出自我創作的方法論,以此繼續探尋未來陶藝創作之路的可能性。
物 現代陶藝;創作方法論
20世紀80年代,現代陶藝在中國剛剛萌芽,之后曾有一段相當長的高速發展時期,而在近幾年學院背景下的現代陶藝創作開始出現不同的發展方向,一部分創作者開始走向手工藝化,從原本的先鋒性慢慢蛻變成大眾更能接受的審美傾向;另一方面的創作者越來越注重個人與時代性的表達,用陶瓷創作變成其中但不唯一的表達方式。
面對歷史和當下的陶瓷藝術發展現狀,回顧本人十年的陶瓷創作經驗,發現自身對個人意識的處理與實驗性的創作一直貫穿在我的創作之中。本文也是希望通過對自我創作的總結與歸納,尋找到個人陶藝創作的語言與規律,并以此探討未來創作的可能性。
總的來講,我的創作思路有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器皿去功能化,追求形式語言的偶發性。其作品以手工成型為主,追求與自然協作。代表作品《皮囊壺》系列等。
第二階段,從對歷史文本的熱衷,如魏晉書法和明式家具的審美體驗,到人與自我生活空間之間的關注,在矛盾中追求和諧。代表作品《瓷書》系列等。
第三階段,把人與物的關系進行拓展,回歸到“物”的本質,將個人體悟提煉并強調作品體現的觀念性。手法上開始試驗泥土的“可復印性”。代表作品《自述》《以死印生》等。

圖一 皮囊壺1

圖二 皮囊壺2
文中所指的“物”大體上可歸納為“自然之物”“歷史文本之物”“藝術思維之物”暗合我創作中體現的偶發性、和諧性與觀念性之特性。
一
《皮囊壺1》系列如圖一,創作于2010年,這是我就讀中國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時期的早期作品。在這件作品中,“壺“的功能被關注到最小,其形態也被置換成純粹的雕塑語言。當創作這件“物”(“自然之物”)時,可以說我已經接受了來自中國美術學院最優質的陶瓷材料訓練,這個階段我非常關注泥巴本身形式語言的產生的多種可能性,利用黑陶“致柔致硬”的特性,有意將偶發狀態下產生的質感與記憶一一保留:泥土在濕潤狀態下柔軟且極賦可塑性,而撕裂之后類似疤痕的質感又不禁讓人聯想起人類身體被傷害后的記憶,但這種記憶的被喚醒是潛在的,更多的是泥巴本身帶來的,而非意識的充分發揮。

圖三 瓷書
同系列的《皮囊壺2》如圖二,在空間形態的處理上,從積蓄膨脹的外形轉化為內斂的收縮狀態,我利用鋼筋將其架空、懸掛,這改變了傳統壺的放置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件作品與其最初的形態來源——“蒙古皮囊壺”馳騁沙場的氣質更為吻合,某種程度也賦予了這個器物一定的動物性與原始性。
在這個系列中,泥土的偶發效果是我刻意表現的,在看似宛若天成的自然肌理背后其實是我對泥性的有意經營。這個階段,我和泥巴的關系是若即若離的,一方面放任泥土在造型過程中產生的自然質感,另一方面又緊緊控制這種質感的限度與范圍。在這個系列里,泥巴是自然、柔軟的,而我的情緒與意識呈現的是一種含蓄,內縮的狀態,這種狀態更多的是泥巴直接帶給我的感受,我的意識其實是伴隨泥巴的周折而周折的。
也就是說這個階段的創作是材料先制作,意識后產生的過程。泥土的偶發是順和自然的發展而展開的,是呈現泥土自然屬性的最好的體現。
而我這階段的作品似乎更符合和自然合作的概念,這里的“物”是比較單純的“自然植物”
二
《瓷書》系列如圖三作品是我對“物”(“歷史文本之物”)的語言的另一種嘗試。這是對魏晉書法用筆和明式家具的審美有感而作。在氣度上,我試圖尋找書法的運筆走勢,而在細節的推敲上,又將在明式家具上所感受到的雅致審美、高格調體驗移植入作品之中。
《瓷書》系列作品是我將瓷與木的結合首次嘗試。瓷與木結合在材料上是一種冒險,這是硬與軟的沖撞,冷與暖的交織。但我試圖營造出一種視覺上的和諧。在這種和諧中,“保護與抗爭”“承載與依附”的悖論情緒一直伴隨我創作到最后。

圖四 自述

圖五 以死印生
對矛盾的事物進行聯系,我在第一階段的創作之前就十分感興趣。中國古典美學里提到,對常規事物的“反常”理解(即稱之為“反常合道”)在表面上是對現事物的扭曲,但卻能形成藝術中的新奇效果,但“反常”又必須“合道”,雖意表之外卻在情理之中,即生活常理合乎藝術之道。此處的矛盾最后都將化為和諧之力量。
因為有矛盾因素的存在,所以在手法和視覺上我盡可能處理的單純,和諧:銅紅釉和米黃色柏木在色彩上互補,猶如層層青巒。詩意纏綿的瓷和冷靜平闊的木形成對比,整個作品體現出一種平和收斂又包容互斥的能量。
而這種冷靜表達的背后,支持我的作品完成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對和諧的表達,雖然和諧的同時存在著矛盾與反對,材料的反對,色彩的反對,但我還是試圖在反對中尋找和諧,尋找其可以共存的元素。
三
在《皮囊壺》《瓷書》系列作品中,我非常拒絕生澀的表達“觀念”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用接近手工藝的處理手法來創作作這些作品。在《瓷書》之后我又很長一段時間沉寂與思考:如果我的《瓷書》繼續做下去,文本是否可以繼續往前發展,或者瓷書的未來會不會變成只是有簡單意義的抽象雕塑?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需要我回到材料的本質來考慮。這種本質不僅僅是對材料本身特點的探尋,也是對背后的文化意義的探尋。
而所謂的文化意義應該是對生活、對文化、對社會的一種個人體悟。《自述》《以死印生》等系列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產生的,一種來自個人化、觀念化的“物”(“藝術思維之物”)的面貌將日漸清晰。
與在《瓷書》系列中瓷與木結合所傳達的是“和諧”不同,從《自述》《以死印生》開始,我重新思考了瓷與木的關系——泥土的可復印性——泥土的物理特性之一。復制是為了還原與記憶。出于偶然的生活體驗,我對老舊的木制家具產生興趣,使得我的關注點從歷史文本中轉移至尋常生活,我想,這恰恰是藝術的本源之地。
在《自述》如圖四這件作品中,我將老家具所有突出的邊角,用泥土包裹,每塊泥土都形成內方外圓的兩個形態:內形是家具的結構與紋路,外形是包裹的軟體形態。隨著泥土干燥、開裂、瓦解,最后我將脫落下來的瓷泥坯置入高溫窯爐將之瓷化。在展示時,瓷片被工整的安置在展廳,形成零件集合的場域。這些白色或黑色的瓷片,看上去似乎是物體的皮屑,又有建筑或者工業零件的錯感,同時又有很強的書寫感。好像一篇生活、環境、亦或是本人“自述”的一種物化方式。
《自述》系列的開始使得我重新考慮我的兩種創作材料:木與瓷。不同于《瓷書》中比較簡單的將兩個材料進行“加法”,《自述》更多的是考慮“減法”,木與瓷的聯系更像是一種概念上與空間上的關聯。
與此同時,樹木的新芽,樹皮的脫落,再一次使我體會到了自然的生死合一。我重新思考:木的本來,木與瓷再次結合的可能性。樹皮剝離了樹木,剝離了時間、剝離了生命,成為了時間與生命的碎片。《以死印生》系列如圖五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產生的,我認為我所做的就是將這些碎片以一種原始的方式儲存。
我將撿來的或大或小幾十塊樹皮一層層地涂上瓷泥漿,累似漆器里脫胎的手法,只是我木頭部分我做了保留。最后將之置入窯爐中高溫燒制。此時,泥漿化為瓷質而樹皮則化為草木灰釉,最終達到瓷(泥漿)與木(樹皮)的完全合一。
在我看來,樹皮是樹死亡的痕跡,正如死皮是人類細胞死亡的證據,記錄樹皮剝離的狀態也是在記錄這個生命曾經活著的記憶碎片。記錄這樣的死也是在回憶這樣曾經的生。在創作《以死印生》這件作品,與其說這是創作,不如說這更像是一種對轉瞬即逝的祭奠。也許,更難能可貴的,這是“我做為我”對外界事物的全新認知,也是“我”重新發現“我的初心”的一種方式。
而此時對于陶瓷這種材料我有了和之前《皮囊壺》不一樣的認識。最初的《皮囊壺》系列是對陶瓷材料最直接的反映,陶瓷在制作過程中的偶發性與空間感是吸引我創作的最大動力。《瓷書》系列中體現的理性中的反作用力是體現和諧的材質之美的最大體現,《自述》開始我慢慢體會陶瓷作為創作材料的的社會層面的意義,第三階段的《以死印生》是我對人與自然作為生命較深層面的理解。
四
自從2005年第一次接觸陶瓷,無論是自然偶發的啟示還是歷史文本的引導,最終到藝術思維的體悟,給我的最大影響的是這些思維過程給予豐富的感官,心理體驗。我個人認為文中的三個階段即:自然之物,歷史文本之物,藝術思維之物內在還是一個遞進體悟的過程。但無論怎么樣每個階段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經歷,而藝術思維的快樂給我感情、認知、生命所帶來的微妙變化和碰撞是當下的,我認為對陶瓷材料進行創作,是一個越來越走向思維解放的過程,也是一個在藝術挑戰、人生態度上越來越勇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