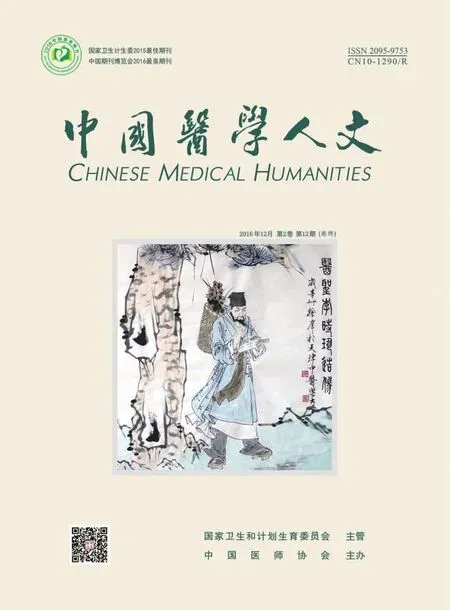聆聽疾病背后的聲音
文/劉夢苑
聆聽疾病背后的聲音
文/劉夢苑

“患者悲嘆醫生不能傾聽他們的聲音,對他們的痛苦漠不關心……他們也許在技術上得到足夠的治療,但在面對疾病的后果和恐懼時卻被拋棄……”麗塔?卡倫在《敘事醫學:尊重疾病的故事》的開篇對現代醫學做出了如是評價。的確,現代醫學的高度發達令人矚目,但“科學與理性”的背后深藏著“冷漠與麻木”。醫生更多地尋求如何提供最先進的醫療技術服務,而忽視了聆聽病人對疾病的傾訴,缺乏對病人情感的關注。病人在忍受疾病折磨時,感受不到治療中的理解與安撫,著實令人唏噓。
麗塔?卡倫用她豐富的臨床經驗和廣博的人文關懷為我們解開了這個疑慮。這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內科學教授,用她那詩意的語言向我們展現敘事醫學的力量,讓患者從自己的講述中發現軀殼下“自我”的哭訴,讓醫者在聆聽中感受那個孤獨靈魂的啜泣,醫生和患者的交流超越了醫學、生物學的領域,跨越了時空的阻隔,達到的是心靈上的相生與共情。
醫學的敘事特征
麗塔在書中這樣評價,“醫學其實是個敘事性很強的領域。”獨特性、時間性、主體間性、因果/偶然性和倫理性,構成了醫學的五種敘事特征。我想,這也大概就是敘事醫學之所以能填補醫患之間的鴻溝、讓醫患雙方得以共情的原因吧。如同本書的題目所言,疾病是故事,是發生在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身上的故事,不可復制,也難以比擬,這便是疾病的獨特性。之于時間性,疾病是時間積淀的產物,將生命的腳步加快并接近遠方的終點,而醫學企圖將時光放慢、停滯,甚或渴望歲月逆流,“醫學是一場跟時間的較量”。之于主體間性,就像小說的讀者與它的作者所形成的微妙契約一般,醫者與患者之間也有著這樣的約定,它不是那一紙病歷、一張化驗單,更不是一條收費憑據,而是兩個原本陌生的心靈間真誠的約定。一個人講述,另一個人聆聽,講述者在講述中重釋自我,聆聽者在聆聽中走近他者,聆聽疾病背后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講,醫學與敘事一直就是不謀而合的。
然而,當醫學告別了曾經的神靈主義、自然哲學的醫學模式,當哈維的血液循環學說、魏爾嘯的細胞病理學等等劃時代的研究成果問世,醫學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人們開始一味地強調醫學的科學性——可復制性和普遍性:皮膚科醫生接診每日來訪的病人就像翻閱一本儲存了皮膚科疾病的圖冊,外科大夫操作精巧的手術如同在流水線上修繕零件。我們太過追求醫學之上的共性,醫療活動便成為了在一個個肉體上的重復、重復、再重復。
如今,人們漸漸發現唯數據馬首是瞻,視證據為金科玉律,誕生的不過是“為醫療衛生中的科學因素耗盡心血而無暇顧及疼痛、苦難和死亡等人類情感”的一代代專家,醫患的鴻溝未被彌合,醫患的距離甚至愈來愈遠。當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醫學的缺憾,還原醫學敘事屬性的敘事醫學便應運而生。
2001年是文學與醫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的內科醫生、文學學者麗塔?卡倫(R.Charon)提出了“敘事醫學”這一新的名詞。敘事醫學是指具有“敘事能力”的醫學實踐,而敘事能力是一種吸收、解釋、回應故事和其他人類困境的能力,其核心是共情與反思。正是因為醫學本身的敘事屬性,敘事醫學才得以彌補現代醫學的缺憾,成為醫學發展的美好愿景。
講述生命的故事
麗塔?卡倫在書中提到,“敘事不只是一種文學形式,它還是一種現象學和認知學的自我體驗模式”。敘事般地訴說病情、回首往事,患者開始留意藏在自己身體中的秘密,這個秘密不為人知,甚至連居住在軀殼下的“自我”都并未知曉。敘事給了患者這樣的機會,正如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所說的那樣,“正是通過敘事,我們才得以創造和重塑自我。”而在診療的過程中,患者并不是唯一的講述者,醫生在聆聽,也在講述。當醫生“用第三只耳朵”聆聽疾病的故事,用敘事技巧分辨出故事的隱喻、意象與影射,再用深厚的醫學經驗加以梳理、以獨特的文學手段將生命的故事再現,醫生是在書寫患者的“傳記”,卻也是在書寫自己,更是在書寫生命于疾病和死亡面前的故事,這便是共情。
敘事給了患者一次走近自己的機會
如果說“疾病加劇了認識自我的過程”,那么敘事就是讓這種對自我的認識、探索得以展現的方式。書中的一個病例很生動地描繪了敘事如何增進了軀殼下的“自我”對身體的感知。一位向來以“我身體很好”而自豪的農產品卡車司機,一直強調自己因腿疾而停止工作。然而,敘事的過程讓患者不斷回憶起夜間氣短、胸悶出汗的細節,一點一滴地透露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跡象。甚至,那個被他的“自我”置若罔聞多年的“枕三個枕頭”的習慣,也在不經意間訴說著“端坐呼吸”的秘密。敘事醫學的歷程很類似自傳文學中“自傳性分隔”的過程,通過回憶與敘事,“自我”獲得了一次與身體的短暫分隔,以敘述者的視角對自己故事中的“主人公”深入剖析,并最終走近身體,了解自己身體的秘密。
疾病敘事的過程不僅是在給醫生講述,更是一個和自己靈魂溝通的過程。在當今,除了病原學明確的傳染性疾病以外,疾病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那個致病心結和矛盾沖突,這一點很符合精神動力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描述,這種被壓抑的“潛意識”就像一雙無形的手扼住生命的喉嚨,在內心積聚、爆發而構成疾病,但是這個深受其害的患者恐怕卻并未意識到它的存在。在精神分析治療中,心理醫師會使用自由聯想的方法讓病人回憶從童年起始的遭遇中的一切經歷,想到什么便暢所欲言,從而發現病人壓抑在潛意識里的致病情結。
我想,在這里,敘事醫學與精神分析療法殊途同歸。敘事醫學也是讓病人在看似漫無目的的思索中講述疾病背后的故事,而從中走近自我,發現埋藏在身體深處的疾病之根。就像書中寫到的那樣,89歲身患多種疾病并伴有長期焦慮的非洲女性通過回憶與敘事,才發現是源于12歲的性侵,盡管吐露心聲已無法逆轉高血壓、乳腺癌在身體上留下的傷痕,但打開了心靈的枷鎖,焦慮也隨之蕩然無存。而敘事醫學更為高明之處在于,它將傳統的生物學治療與心理治療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講述疾病的歷程,也是發現身體上的傷痕與心靈上硬痂的過程。
敘事給予醫生一種講述生命贊歌的途徑
在臨床敘事中,患者并非唯一的講述者,醫生在聆聽,卻也在講述。當了解到患者的生存境遇,還原了疾病的社會生活史、傳播史,當聆聽了患者的感人故事,感受其信仰與觀念之后,醫生的敘事撰寫便是一個關注、反思與再現的過程。醫生運用自己獨有的醫學與文化底蘊,將那有血有肉卻又不免邏輯混亂的素材,整理成一曲動人的生命贊歌而將故事重現。王一方教授曾這樣評價,“敘事內容再現敘事者的疾苦觀、生死觀、醫療觀,是敘事者信念、思想、意圖所建構的另一種真實。”
我想,醫生得天獨厚地擁有與病人零距離接觸的位置,可以記錄下疾病的侵蝕、演進以及生命一次又一次相應的掙扎與抗擊,這對于患者本人、患者群體、醫生乃至整個社會都是莫大的精神財富。因為,“疾病是一扇幫助認識自我的門”,疾病雖然使生活黯然失色,卻讓患者思考那些不曾思考過的問題,讓他們開始考量生命的價值,思索生命的終點意味著什么。身體健康的人視命運與身體為理所當然,唯有經歷病痛的折磨后,才能真正體會健康的價值、生命的可貴,才會思索生與死的意義。宗教學者約翰?赫爾因中年視網膜病變而失明,才意識到“肉體完整才是一個人自我之所在”的真諦。史鐵生經歷殘疾、腎衰等一次次折磨才有了“唯愛愿于人間翱飛飄繚,歷千古而不死”的生死感悟。但是,不是每個患者都是約翰?赫爾、史鐵生,并不是每位經歷病痛的人都有著這樣清晰的人生理解與感觸,那種疾病背后的聲音更多是一種朦朧的、若隱若現的存在,等待醫生的耐心傾聽、敏銳捕捉,并用敘事的手段將故事再現,將微弱的生命之音放大為震撼的生命贊歌。
聆聽疾病背后的故事
醫學敘事特征中的“主體間性”決定了臨床敘事中必然包含兩個主體:一個人講述,一個人聆聽。這種敘事本性告訴我們:醫學實踐本來就是需要一名合格的聆聽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代醫學模式化的診療方式使患者的傾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斷,“你不用說了,我會問的,你回答我的問題就行。”這樣近似冷酷的回答想必每位罹患過疾病的人都有所耳聞。我們這些醫學生自進入臨床見習之日起,就被一套標準化流程反復、反復而變得“訓練有素”。一本本醫學寶典教會我們以所謂“專業”的方式問診,并以主訴、現病史、既往史、社會史、家族史、器官系統回顧、查體等一系列機械化的套路完成病歷撰寫。毋庸置疑,我們聆聽了,并且的確是認真聆聽了,只可惜我們企圖抓住那些與醫學密切相關的細節之后,卻忽略了一些也許更為重要的東西。阿瑟?克萊曼曾主張:“將疾病與疾痛區分開來,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醫生的世界,一個是病人的世界;一個是被觀察、記錄的世界,一個是被體驗、敘述的世界;一個是尋找病因與病理指標的客觀世界,一個是訴說心理與社會性痛苦經歷的主觀世界”。對當下的臨床路徑而言,這樣的比喻恐怕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然而,疾病是有故事的,它展現的絕不僅僅是“頭暈、胸悶、喘不上氣”這幾個簡單的癥狀性描述,它隱含著患者的認識、情感、意志,甚或是患者的人格特征與社會價值取向。患者并不是唯一的講述者,和他一起講述的還有他所處的文化。
敘事醫學卻教給了醫生怎樣做一個合格的聽者。細讀、反思性寫作的過程,更是教會了醫生總結如何聆聽,如何走近患者的心靈、與他們共情。書中麗塔在對敘事能力的描述中將敘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關注、再現和歸屬。在我看來,關注的過程即體現在醫生對患者的聆聽過程,也是醫療工作的起始。當綠色的簾子下,一位飽受煎熬的陌生人與我們相遇,傾聽過程隨之開始。“關注的涵義是清空自己”,聆聽也是如此,把自己的思想清空,成為“意義產生的容器”。這個容器接納病人的疾病故事,捕捉故事中的心靈密碼與隱喻,感知患者的靈魂深處,締結情感和精神的共同體。
當然,我想,麗塔將醫生比作“容器”,并不是說醫生就是一個接受患者龐雜的訴說的器皿,也不是說醫生可以拋棄自己多年的臨床知識與醫學儲備。相反,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容器”,她不是被動的接納,而是通過承擔見證,主動地將患者疾病背后的故事、體驗甚或是難言之隱吸引出來。她是“容器”,她會包容所有龐雜的癥狀、與之相伴的情感、乃至其背后的醫療觀、人生觀。
然而,聆聽的過程并未就此止步。這個所謂的“容器”會以她敏銳的洞察與深厚的儲備,對容納的信息進行加工,她并沒有卸載任何信息,只是以一種專業的方式將它們攪拌、提煉,讓它們獲得專業的解讀。
聆聽疾病背后的故事,意味著全面、自然地吸收、接納與理解,在靈魂深處與患者相遇,與他們共情。而富有專業知識的聆聽并不局限于此,因為經過醫生這個“容器”的加工之后,患者本人也許會更加清楚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困境,自己的苦難是從何而起。在這個比喻下,現代醫學更像是一個濾器,她缺少“容”的過程,而是過早地對信息進行了過濾,只可惜那些被無情濾掉地信息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尾聲
聆聽和講述,是敘事醫學中關鍵的組成成分,也是醫療實踐中醫患溝通的關鍵。當然,這兩個過程并非截然分開,也并非是單向的聽與講的關系。患者在講述,他在講述疾病背后的故事,醫生在聆聽,她在聆聽那個痛苦軀殼下的聲音。但同時,醫生也是講者,她將自己聽見的聲音,與自己的知識、情感融為一體,以訴說、記錄抑或平行病歷的方式將這個聲音重現、放大,讓自己聽見、讓患者聽見、讓整個社會聽見。在聆聽和講述的過程中,醫患的角色在調換,這樣的過程仿佛正向的循環,聆聽方可更好地講述,講述才能更好地聆聽。敘事醫學帶來的不僅是融洽的醫患關系、改善的治療效果,更是打通軀體與心靈的阻隔,重建人性的悲憫與救贖。
當然,有人會說,在當今醫療體制之下,醫患供需嚴重失衡,醫生應付于日常工作,即便全力以赴尚且感到有所不足,又怎能耐下心來去聆聽、品味、再現那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呢?是的,我想當今中國的醫療環境也許暫時還不是敘事醫學的沃土,敘事醫學的碩果尚且不能在如今的中國立馬扎根、發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拋棄、拒絕這樣的理念、信仰和追求。在本書麗塔的描述中,我們知道,即便是在醫療體制發達的美國,也依然沒有擺脫冷漠麻木的臨床路徑:“只有病,沒有人;只有技術,沒有關愛;只有證據,沒有故事;只有救助,沒有拯救”。因而,即便我們克服了醫療制度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做到將醫患關系轉入正軌,唯有“技術前行、科學至上”的理念恐怕孕育的還是一個只會看病不會懂人的機器。我們的社會需要的不僅是柳葉刀、聽診器,更是需要一個有著人性的悲憫與溫情的活生生的聽者,技術僅僅是工具。
感謝麗塔給了我這樣一次洗禮靈魂的機會。作為即將邁入臨床實習的醫學生,敘事醫學給了我一個嶄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醫生這個職業,醫生是工程師、科學家,是藝術家,更是牧師、是靈魂的救贖者。敘事醫學告訴我們,在褪去了醫學的自然科學外殼之后,醫學與文學、哲學、藝術殊途同歸,因為醫學的靈魂終究是屬于人文的沃土之上。敘事讓醫學得以重返人文,在平靜的聆聽和娓娓的講述中,獲得心靈上的相生與共情,展現人性的溫存與美麗。
/北京大學醫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