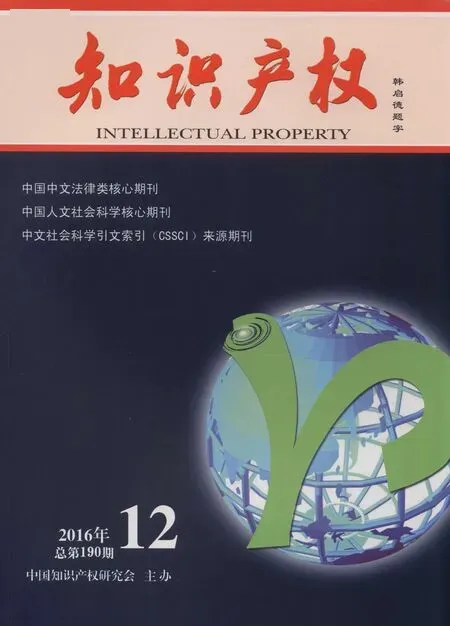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司法定價之惑
馬海生
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司法定價之惑
馬海生
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是FRAND原則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影響專利許可費計算的因素比較復雜。專利價值評估理論雖然有不同的評估方法對專利價值進行定量評估,但尚沒有公認的有效方法,評估結果也多不被認可。專利標準化增強了專利價值、專利許可費計算的復雜性,因此法院難以作出符合FRAND原則的專利許可費認定。單許可費爭議在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訴性。反壟斷之訴、強制許可均不會導致由法院裁定專利許可費。法院“以最低費率為準”裁定許可費有可能不符合FRAND原則,也有可能損害專利權人的正當利益。
標準必要專利 許可費 司法定價
一、引 言
自從產業界為解決專利標準化后可能出現的專利權人濫用技術標準為其帶來的強勢地位問題,提出了公平、合理、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FRAND)專利許可的基本原則,其內涵的模糊性就具備了“迷人的困惑”。因其模糊,且符合人類本能的正義理念,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原則迅速得到了產業界和理論界的認可,例如幾十家標準化組織早早就接受了該原則a調查統計分析,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鑒于對FRAND模糊性的質疑,有些標準化組織已經修改了其專利政策,開始具體化FRAND的內涵。可參閱:http://patentlyo.com/ patent/2015/02/amends-patent-policy.html.,理論上也未見有人明確反對該原則。這種模糊性對FRAND原則在產業界的推廣功莫大焉,因而對于指導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實踐間接起到了作用。因其模糊,對于什么是FRAND許可沒有任何明確的解釋,又妨礙了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在標準專利許可中功用的發揮,甚者已經導致了幾場訴訟糾紛及反壟斷執法案的發生。
在所有的爭議當中,價格是核心問題、終極問題。除非蓄意拒絕許可(技術實施方也有可能蓄意拒絕接受專利許可),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人與實施方的各種談判條件最終都會歸結為:“多少錢”。
因此,相關學術理論、有關糾紛案件,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的數額都是探討的焦點問題之一。它的重要性還體現在立法上。《專利法第四次修訂征求意見稿》第82條規定,參與國家標準制定的專利權人與標準的實施者不能達成專利許可使用費協議的,由地方人民政府專利行政部門裁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b該司法解釋實際具有立法的性質。第24條規定,推薦性國家、行業或者地方標準明示所涉必要專利的信息,經專利權人、被訴侵權人充分協商,仍無法就該專利的實施許可條件達成一致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確定。從該司法解釋給出的考量“許可條件”的因素c綜合考慮專利的創新程度及其在標準中的作用、標準所屬的技術領域、標準的性質、標準實施的范圍和相關的許可條件等因素。看,許可費無疑是“許可條件”的核心。
從結果角度考察,由司法認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最終是要給出一個確定的許可費(率)數額,并推定這就是對當事人雙方而言公平的、合理的、無歧視的許可費數額。
本文提出的疑問是,由法院或者行政部門d即使裁決由專利行政部門做出,其性質也是準司法行為,而不是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行為。故本文討論中統一以司法認定標準必要專利性許可費行為為研究對象。裁定的許可費(率),真的是公平的、合理的、無歧視的許可費(率)?
二、標準必要專利性許可費影響因素的復雜性
(一)專利許可費影響因素的復雜性
專利許可費就是專利實施方愿意為專利技術實施行為所支付的且專利權人愿意接受的對價,也近似于e之所以是“近似于”,是因為從文義理解,專利的價值應該是專利權的全部價值,亦即轉讓的價值。但在專利許可中,被許可人眾多(至少不確定),即使是獨占許可或排他許可,被許可人也不享有專利權。因而專利許可的許可費,邏輯上的數額應該是少于專利轉讓的數額——專利權的全部價值。本文所謂“近似于”是從方法論角度言說,不是指兩者的價值數額近似。研究中也發現,在專利價值評估中,名曰評估“專利價值”,實際上會考慮專利許可狀況。可見,也未嚴格在語義上區分專利價值與專利許可價值。可能是因為二者的高度相關性,或者在實際許可中評估專利價值時,不言而明的是評估本許可的價值。基于前述方法論上的共通性,本文對于專利許可費確定的影響因素與專利價值確定的影響因素作同一考慮。是雙方為標的專利定價。影響普通專利許可的許可費或者是專利價值的因素,通常對于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的確定也有影響。
確定專利許可費所需要考慮的因素,亦是影響專利價值的因素,在司法實踐及專利價值評估理論中,都得到了總結。
1.司法實踐中總結的影響專利許可費的因素——美國的經驗
直接因許可費爭議產生的司法訴訟案例極少f經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刊登的案由為“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糾紛”的判決案件,皆是因為合同履行引發,未發現因當事人雙方不能達成許可費數額而起的爭訟。,法院處理的涉及專利價值的案件多是侵權案件引發的損害賠償計算問題。在我國專利法中,“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是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法定第三順位計算方式。但是,實踐中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數額多是以法院酌定的方式確定,尚難以從判例中總結出我國法院確定專利許可使用費的方式。
《美國專利法》第284條規定:法院應判給原告足以補償所受侵害的賠償金,其不得少于合理的許可費。在美國,合理許可費方法(reasonable royalty)是專利侵權訴訟中計算損害賠償的最主要方式。g在美國的地方法院中,從1990年到2004年,超過60%的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是基于合理使用費方法計算得出的,另外,15.1%的專利損害賠償計算同時使用合理使用費方法和所失利潤方法;而從2002年到2009年,約有80%的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案件使用了合理使用費方法,相比1990年到2004年的75%有所上升。阮開欣:《解讀美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計算中的合理許可費方法》,載《中國發明與專利》2012年第7期,第64頁。是故,美國法院判例總結出了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確定侵權賠償數額時假定當事人進行許可談判所確定合理的專利許可使用費的方法,可供我們借鑒。
在美國判例中,影響最大的專利許可費計算判例是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案hGeorgia-Pacif 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166 U.S.P.Q. (BNA) 235(S.D.N.Y. 1970).。該案總結了15項在假定談判中應考慮的因素,分別為:(1)專利權人對涉案專利曾收取的許可費數額;(2)被許可人為使用與涉案專利具有可比較性的其他專利所支付的許可費;(3)許可的性質和范圍;(4)專利權人通過拒絕許可他人來維持專利壟斷或者為許可設置特殊的條件來保護這種壟斷的既定政策和營銷安排;(5)許可人與被許可人之間的商業關系;(6)銷售專利產品對被許可人的其他產品的促銷效果,該發明對許可人在銷售其他未受專利保護產品時的幫助效果;(7)涉案專利的有效期和許可期限;(8)生產專利產品的現行獲利能力、其商業上的成功、當前的市場普及率;(9)涉案專利相對于類似的舊模式或設備的作用和優勢;(10)涉案專利技術的性質;(11)有關侵權人使用涉案專利的程度,以及可證實的使用價值的證據;(12)使用涉案專利技術或相類似技術在特定行業或類似行業中慣用的產品售價或利潤上占有的比重;(13)涉案專利實現的利潤;(14)具有資格的專家的證言;(15)如果許可人與被許可人理性、自愿地協商,在侵權發生之時可能達成的許可費。
上述15項因素比較詳盡,然而其適用必然面臨如下問題:
第一,各因素影響因子的不確定性。適用15項因素判斷許可費數額,在不同的個案中,15項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甚至,在不同案件中,有些因素不存在,例如(1)、(2)、(4)、(6)、(11)、(13)、(14)諸項就未必在每個案件中都存在。在不同的案件中,考慮哪些因素,不考慮哪些因素,因素之間的比例關系如何都不可能一致。即使在一個案件中,15項因素各自的影響因子調整后,許可費認定的結果也會不同。在個案中應如何確定15項因素的影響因子,也是一個極難的問題。考慮的因素越多,越難以解決上述問題,越可能違反“奧卡姆剃刀原理”i即“簡單有效原理”,“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可操作性及操作效果越值得擔憂。
第二,可比性問題。第(1)項因素是以專利權人對涉案專利曾收取的專利許可費對比本次許可,這是一種縱向(時間上)的對比。第(2)項是以被許可人為其他專利所支付的許可費,這是一種橫向(專利間)的對比。對比的前提是比較的對象具有可比性。但專利的性質恰恰給可比性帶來挑戰。技術方案能夠獲得專利權的前提是具有新穎性、創造性,與現有技術比較具有非顯而易見性的區別特征。這就給涉案專利與其他技術間的可比性判斷帶來困難。技術之間當然可能具有可替代性,但可比性與可替代性是不同的性質。可替代性并不僅僅考慮技術間的相似性,價格(成本)本身就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原因因素。許可費確定中的技術可比性,價格卻是結果因素。技術方案獲得專利權以后,法律賦予的獨占權因素對可比性也有影響,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間,專利保護范圍、保護強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會對同一專利技術的實施結果產生影響。即使在一國內部,專利保護結果隨著保護期的變化也會不同。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項專利技術的許可,被許可人不同,許可的市場、產品、實施量、預期也會不同,這些都會影響許可費。尋求這些前提條件皆基本一致的比較對象很困難。忽略掉某些“次要”因素,可以擴大可比對象的范圍,但忽略某些因素的科學性又值得懷疑。
第三,定性而不定量。在個案中法官需要回答當事人:應付多少許可費/賠償金。15項因素中的絕大多數只能是從“定性”的角度,給出確定許可費數額的參考。每個因素運用到個案之中,各能夠產生多少許可費數額或比率?各因素加權之后,又能產生多少許可費數額或比率?顯然,15項因素無法從“定量”的角度幫助法官確定具體案件的許可費(率)。從“定性”到“定量”的跳躍是如何產生的,15項因素本身難以給出答案。
2.專利價值評估理論存在的問題
在會計學、管理學領域,形成了系統的專利價值評估理論。重點包括專利價值影響因素、專利價值評估方法。
(1)專利價值影響因素方面的問題
根據專利價值評估理論學者的研究,專利價值影響因素包括技術因素、法律因素和經濟因素。技術因素包括先進性、行業發展趨勢、使用范圍、配套技術依存度、可替代性、成熟度;法律因素包括穩定性、不可規避性,專利侵權可判斷性、有效期、多國申請、專利許可狀況、依賴性;經濟因素包括市場應用情況、市場前景規模、市場占有率、競爭情況、政策適應性。j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管理司、中國技術交易所編:《專利價值分析指標體系操作手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
前面在分析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案的15項因素時指出的缺陷,上述因素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此外,專利價值評估理論構建評估體系,會為每個因素的影響力賦值,才能進行下一步的評估。例如,一篇研究文獻對其總結的專利價值評估指標賦值如下表:

專利價值評估指標表k王珊珊、王宏起、李力:《技術標準聯盟的專利價值評估體系與專利篩選規則》,載《科技與管理》2015年第1期,第2頁。
每個因素的賦值只可能來自于經驗和研究者對于某項(些)因素的偏好。這種賦值是否準確是一個既難以證實也難以證偽的問題,因為缺乏可比性,即使從事后看按照這個評估體系確定的專利價值高了或低了或恰如其分,也無法知道是某項或全部的影響因素賦值準確導致,還是各項因素賦值有的偏離有準確但在整體上達到了最終的評估數值。因此,賦值會影響最終專利價值評估值,但難以說賦值是科學的。對于不同的專利、不同的市場、不同的許可條件,是否都應按照同一標準賦值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如果Georgia-Pacif 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案確定的15項因素也按這種方式賦值,前述問題也會存在。
(2)專利價值評估方法方面的問題
在專利價值評估理論和實踐中,評估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法、收益現值法、市場比較法、實物期權法等。
成本法主要基于專利技術的成本來確定專利價值。自創專利資產成本一般由研發成本、專利申請及維持費用以及交易成本構成。外購專利資產成本常使用重置成本法。在評估資產時按重置成本估價標準,以被評估資產的現行重置成本減去資產的損耗或貶值等因素,從而確定被評估資產價格。l程文婷:《專利資產的價值評估》,載《電子知識產權》2011年第8期,第76頁。成本法計算簡單,數據來源相對可靠,然而,專利的價值并不能由其成本直接決定。成本法沒有考慮專利技術所帶來的預期收益,故往往會低估專利的價值,而且無形損耗測算復雜,難以準確計算。m楊思思、戴磊:《專利價值評估方法研究概述》,載《電子知識產權》2016年第9期,第79頁。
收益現值法是指通過估算被評估資產的未來預期收益并折算成現值,借以確定被評估資產價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n同注釋l,第78頁。收益現值法雖然更能全面考量影響專利價值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買賣雙方的市場預期和價值判斷,然而,預期收益額的預測難度較大,受較強的主觀判斷和未來收益不可預見因素的影響。o許華斌、成全:《專利價值評估研究現狀及趨勢分析》,載《現代情報》2014年第9期,第78頁。
現行市價法是指按市場現行價格作為價格標準,據以確定資產價格的一種資產評估方法。p同注釋l,第79頁。現行市價法仍然存在“可比性”的問題。研究者還指出了其他困難:市場波動較大,某些產業,尤其是諸如電子、通訊等技術更新換代速度較快的產業,專利技術的價值易受市場環境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出較大差異;專利交易數量不足,我國技術交易市場不成熟,在某些特定領域完成技術交易的專利數量不多,難以尋找足夠數量的參照專利;交易信息難獲取,技術交易往往涉及交易雙方的商業秘密,技術交易的細節通常不予公開,難以獲得準確的交易金額。q同注釋m,第80頁。
實物期權法是將現代金融領域中的金融期權定價理論應用于實物投資決策的分析方法和技術。企業可以取得一個權利,在未來以一定價格取得或出售一項實物資產或投資計劃,所以實物資產的投資可以應用類似評估一般期權的方式來進行評估。同時又因為其標的物為實物資產,故將此性質的期權稱為實物期權。學者把這種分析方法引入了專利價值評估領域,運用金融理論模型來為專利技術定價。例如有學者給出了如下模型r韓士專:《許可實施狀態下的專利價值評估方法》,載《中國發明與專利》2008年第11期,第89頁。:

其中,V是生產專利產品的投資費用;Fi是投資者準備生產專利產品之前每年的費用;P為投資者生產專利產品所產生總現金流的現值;θ為相應的標準差;μ為現金流的折現率;γ為無風險利率;T年為投資者購買專利權到具體實施專利權、生產專利產品的時間年限;q為專利實施許可費率。
對于該模型而言,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若專利實施許可費率正是雙方爭議待解決的問題,則無法預先確定,進而無法求出專利價值。對實物期權法,有研究者認為,其缺陷是需要使用復雜數學公式,不確定性難以估算。s同注釋o,第78頁。同時,該方法對專利的法律屬性和技術屬性考慮不足,如法律狀態的穩定性、專利保護范圍大小、技術先進性高低、技術成熟程度、技術可替代程度等,導致評估結果出現一定誤差。t同注釋m,第81頁。
有研究總結指出,現有專利價值評估方法的現狀和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不同機構和組織提出的評估方法眾多;目前沒有能夠得到公認效果的評估方法;經濟體判斷專利價值時機構或個人的主觀影響大,評估方法的結論采信度小;專利價值評估沒有行業或國家的規范和標準;專利評估方法的類型仍停留在一種或幾種理論的結合上,方法體系本身沒有突破;價值計算的參數以靜態預測得出為主;計算依據的參考因素高度概括,數量少,無法實現與專利價值多種影響因素的擬合;計算方法定型后更新困難,計算方法沒有自適應特性,無法快速處理變化的海量數據,不能適應專利誕生到發展期間外部環境中新影響因素的出現和變化需要。該研究給出的調研結果更令人尷尬。在2015年的專利信息年會上進行的專門調研中,隨機選取參會的10家專利代理公司(其中含1家臺灣地區公司,9家大陸公司)進行提問。對于“您公司的專利價值評估是否能夠得到其他同行的認同?”的問題,回答均為“不能”。其中臺灣地區一家參展代表明確表示,作為臺灣地區最早開始研究和提供專利價值評估的智權公司之一,現在很少收到專利價值評估方面的業務,原因是自己苦心研究的價值計算方法得不到外界用戶的認可。u吳全偉、伏曉艷、李嬌、趙義強:《專利價值評估體系的探析及展望》,載《中國發明與專利》2016年第3期,第124頁。
從專利價值評估理論自身的研究成果看,每一種主流的專利價值評估方法都有內在缺陷,專利價值評估結果難以獲得實務界認可。這種情況是符合情理的。因為專利價值評估是對未來的預期,受復雜、不可控因素影響,未來是不確定的。面對這種情況,即使將能夠“定量”分析的評估工具運用到司法實踐中,也很難得出真正符合FRAND原則,對于雙方當事人而言許可費(率)是公平的、合理的,且對第三人也是無歧視的效果。進一步反思,如果連定量分析都無法實現,只能靠定性分析裁決出的許可費又如何保障其符合FRAND原則?
(二)專利標準化增加的復雜性
困難并沒有結束。除了具有普通專利的價值確定面臨的問題外,專利標準化后,還會給標準必要專利價值的認定帶來額外的問題。
1.如何別除標準帶給專利的價值增值
關于標準必要專利的價值,學者普遍接受兩個假定:第一,標準會給專利權人帶來更高的市場優勢地位,增強專利權人在專利許可談判時的議價能力。這相當于增加了專利技術的價值。第二,標準化是公益性活動,專利權人只應收取專利法所保障的與其創新貢獻對應的技術許可費,不能額外收取因標準化產生的增值收益。甚至有標準化組織因為標準的公益性考慮而要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放棄收取專利許可費。v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雖然前兩個假定在邏輯上尚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明,但作為主流觀點,本文亦暫也接受并作為本文論證的基礎。
依前兩個假定,除非要求專利權人放棄收取許可費(這很難實現),準確裁定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費,勢必要能分辨出三個數值:沒有標準化時專利的價值及其許可費、標準化帶來的專利價值增值量、標準化以后專利的價值及其許可費。當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實施者談判時,實施者便可以判斷專利權人的要價是否包含了標準化帶來的價值增值量,進而判斷專利權人的要價是否公平、合理。法院面對爭訟時的判斷也是如此。
但是,筆者在專利價值評估理論研究成果中,尚未檢索出能作前述數值評估、數值別除的方法。w當然,筆者非專利價值評估理論研究人員,查閱的資料難免存在遺漏。甚至還存在與其相反的理念。例如有研究總結企業技術標準聯盟技術定價問題是關系到技術標準聯盟運作成敗的關鍵因素的理由時,認為企業首先可以通過聯盟的影響力促使自身聯盟的標準成為事實標準,從而能夠節省大量的時間,迅速占領市場;其次還可以通過聯盟使對手成為朋友,同時消除潛在競爭對手的標準對自己的威脅;還可以通過聯盟輸出自己的技術,增加自己在標準制定中的談判籌碼。x曾德明、朱丹、彭盾:《技術標準聯盟成員專利許可定價研究》,載《軟科學》2007年第3期,第14頁。當然,從現實角度講,本文也認可該研究的總結。這恰好說明,企業加入技術標準聯盟是為了利用標準帶來更高的收益。在實務操作中,如何能區分合理地利用技術標準帶來增益與不合理地利用技術標準帶來增益?如何能切割出這種既是行使專利權,也是標準化行動的一部分的企業行為,進而實現對標準化給專利價值增值的認定和別除?目前看,還需要深入研究,甚至也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但若不做這種別除,在邏輯上又如何得出基于前述兩假定的公平、合理的許可費數額?
2.專利費累積(Roy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alty Stackingg)問題
專利費累積是標準必要專利討論中的焦點問題之一,學術界已有相當多的探討。y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在此不對如何解決專利費累積展開討論,而是分析專利費累積與專利標準化之間的關系。
(1)專利標準化不是專利費累積的主要原因
專利費累積問題突出表現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領域,因為這些領域存在大量的專利權。為何這些領域專利權數目龐大,原因可能有:第一,這些領域屬于技術創新熱點,新技術層出不窮;第二,層累性質的“微創新”很多,而這些“微創新”在產業上又具備相當的應用價值,要申請專利保護;第三,產品屬于技術密集型產品,單位產品里包含的技術數量非常大;第四,企業為了“自保”,被迫申請大量專利(即使不會實施)用以應對可能的大規模專利訴訟,并形成了惡性循環。
專利累積局面形成后,即使每一個專利權人只索取很小數額(或比率)的許可費,許可費總額都可能會很可觀,甚至會吞掉低利潤率企業的全部利潤。
但是,以上專利累積的原因都與專利標準化沒有關系,即,專利標準化并沒有造成專利累積,只是在專利累積的局面形成后,專利標準化加強了專利權人的議價能力,使部分實施者喪失尋求實施替代技術的可能性。故可以說,專利標準化只是加強了專利費累積的后果,并不是專利費累積的主要原因。
如果專利標準化不是專利費累積的主要原因,在確定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能夠獲取的合理使用費時,還需要考慮專利費累積因素嗎?在多大程度上考慮才能說是公平、合理的呢?
(2)個案中裁定專利許可費數額難以考慮專利費累積問題
雪崩的時候,每一片雪花都有作用,但每一片雪花又都無足輕重。專利費累積是由數量龐大的專利導致的,單一件專利的影響并不大。但個案的FRAND許可費爭議,可能是針對若干專利,也可能是單一專利。
要借助于“個案”解決“整體”問題,只有兩條路徑:第一,殺雞儆猴,通過個案裁定較低的許可費數額警告全部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如不自行解決許可費累積問題(通常是降低許可費率),一旦走到司法階段,權利人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從功利角度考慮,這條路徑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對當事的專利權人而言,肯定不是受到了公平、合理的待遇。第二,分析出涉案專利(專利包)對整個專利費累積所起的作用,然后按比例原則,適當降低專利許可費。這種方式可謂公平,但難有可操作性。不論是法院,還是當事企業,都難以確定造成專利費累積的專利有哪些,未來還會出現哪些,更不要說分割清楚各標準必要專利所起的作用了。
即使離開個案從整體上看,司法實務操作也難以區分出上述四種原因導致的專利費累積與專利標準化加強的專利費累積。如果不能作出區分,以不能獲取標準產生的額外利益為名,犧牲專利權人的部分利益,克服并非主要由標準化所產生的后果,即要求專利權人接受更低的許可費,對專利權人而言該許可費難言公平、合理。畢竟,公平、合理是對專利權人和實施者雙方的要求,也是給予雙方而不是一方的待遇。
三、專利許可費的可訴性問題
(一)單許可費爭議不構成合同之訴
本文認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具有一定條件下的強制締約義務的觀點。在具有市場支配地位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行使專利權的行為也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z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關于強制締約義務,另可參閱祝建軍:《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率糾紛具有可訴性》,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4期,第8頁。@7 羅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漢斯?G?萊塞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8 參閱王利明:《統一合同法制定中的若干疑難問題探討》,載《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違背強制締約義務或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利益或信賴利益受到損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訴。此時,可以認為FRAND承諾具有可訴性。
但是,當當事人的爭議點僅在于許可費(率)的時候,許可費(率)爭議是否具有可訴性?本文認為沒有,理由如下:
1.合同尚未成立,不存在違約事由
除強制締約義務和締約過失責任外,因合同事務引起訴訟,都基于當事人間合同已成立,訴訟是針對合同的履行(一方或雙方違約)而不是可否締結合同。
以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及學理為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是否成立存在爭議,人民法院能夠確定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標的和數量的,一般應當認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對合同欠缺的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內容,當事人達不成協議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第125條等有關規定予以確定。學理上通常認為,前述規定并不破壞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一致”原則,它只是在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導致合同已成立的情況下,就其他不明確的問題達成補充協議或無法達成補充協議時的救濟,這實際上已經屬于合同履行問題。《合同法》第61條、第62條位列《合同法》第四章“合同的履行”部分進一步印證了該判斷。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單方做出FRAND承諾,通常只意味著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愿意以善意的態度與同樣秉持善意原則的潛在實施者協商許可條件并最終達成意思表示的一致——許可合同。難以認為一做出FRAND承諾,就立即與所有潛在實施者達成了意思表示的一致,除非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做出的FRAND承諾內容明確具體,包含了立刻授予潛在實施者專利許可實施權的意思。如果說有“意思表示一致”,也只能認定專利權人與潛在實施者在“善意協商”上達成一致,但這種一致不能視為合同成立。
從合同成立的過程看,要約和承諾形成合同。要約是希望與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的內容應當是具體確定的,且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要約人即受該意思表示約束。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僅僅做出FRAND承諾,許可合同的內容基本沒有涉及,難以認定構成要約。
2.單許可費爭議的可訴性與契約自由原則相沖突
在合同中,最基本的一項原則就是“契約自由”。正如海因?科茨所講,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7合同自由之所以備受推崇,是因為人們堅信它本身意味著正義或公正,自由意志將導向公正。@8
契約自由包含四個方面的含義:(1)締約自由,即當事人雙方有權自主決定是否與他人締結合同, 法律不應當限制當事人訂約或不訂約的權利。(2)選擇合同相對人自由,即當事人決定與何人訂立合同的自由。(3)確定合同內容自由,這是合同自由原則的核心之所在。確定合同內容自由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當事人選擇合同類型的自由,即締約人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確定與他人訂立何種類型合同,而不受他人的干涉;二是選擇合同條款的自由,締約者可以自由選擇合同的標的、價款、履行方式、交付的時間和地點、違約責任的承擔等事項。(4)締約方式自由,即當事人有權自由選擇意思表示的方式。@9蘇號朋:《論契約自由興起的歷史背景及其價值》,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5期,第90頁。
在不具備強制締約義務的情況下,契約自由意味著專利權人可以根據其希望的契約內容確定可與之締結契約之人。如果當事人之間單純就許可費(率)達不成一致就可以起訴請法院確定許可費(率),無疑是一舉剝奪了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一切情況下的締約自由、選擇相對人自由、確定合同內容自由和締約方式自由,與契約自由原則沖突嚴重。
契約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契約自由是市場交易秩序的基礎,無特別事由(這種特別事由通常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而破壞契約自由原則,無疑是對正當市場經濟秩序的威脅。
3.合同無效之訴不能產生司法裁定許可費之結果
合同法也的確為排除技術標準必要專利許可中的不公平提供了依據。如《合同法》第329條規定:“非法壟斷技術、妨礙技術進步或者侵害他人技術成果的技術合同無效。”第334條規定:“技術轉讓合同可以約定讓與人與受讓人實施專利或者使用技術秘密的范圍,但不得限制技術競爭和技術發展。”第335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技術進出口合同或者專利、專利申請合同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樣,國務院1985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列》在《合同法》實施后仍然得以適用。根據該條例第9條的規定:技術引進合同的供方不得強使受方接受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未經審批機關特殊批準,合同不得含有某些限制性條款。#0#0 不得含有的限制性條款包括:(1)要求受方接受與技術引進無關的附帶條件,包括購買不需要的技術、技術服務、材料、設備或者產品;(2)限制受方自由選擇從不同來源購買材料、零部件或者設備;(3)限制受方發展和改進所引進的技術;(4)限制受方從其他來源獲得類似技術或者與之競爭的同類技術;(5)雙方交換改進技術的條件不對等;(6)限制受方利用改進的技術生產產品的數量、品種或者銷售價格;(7)不合理地限制受方的銷售渠道或者出口市場;(8)禁止受方在合同期滿后,繼續使用引進的技術;(9)要求受方為不使用的或者失效的專利技術支付報酬或者承擔其他義務。#1 華為訴IDC公司案[(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7號、(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5號],一審判決的主審法官發表的文章雖然表達了認為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對標準實施者以及潛在的實施者負有以符合FRAND條件許可的義務,該義務與供水、供電、供氣等壟斷企業所擔負強制締約義務相似的觀點(參見:祝建軍、陳文全:《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率糾紛具有可訴性》,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4期,第8頁。),但在一審判決書中,并未直接表達出這種類比思路,而是以IDC公司在中國負有以FRAND條件向華為公司許可的義務,但IDC的要約不符合FRAND原則,華為如果不尋求司法救濟,就只能被迫接受IDC公司單方面所提出的條件作為論證理由,得出法院有權力裁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結論。終審判決又是以類比強制許可的思路,得出雙方可以自行協商確定使用費或者費率,協商不成,則可以請求相關機構裁決的結論,進而得出華為有權利申請法院裁定的結論(不是強制許可,必不會是行政機關裁定)。因此該案終審也沒有適用強制締約義務理論。#2 《反壟斷法》第50條: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如果出現法定的合同無效情形,不能協商解決的,一方當事人可以訴請法院判決。判決的結果一是合同無效,一是可能存在因合同無效導致的他方返還義務或賠償義務。
但是,這種訴訟不可能產生法院裁定許可費(率)之結果。裁定許可費(率)實質上是法院強制在當事人之間建立了許可實施合同關系,與合同無效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反。在法律性質上,裁定的專利許可費(率)也根本不能解釋為一方對另一方的違約賠償。
4.締約過失責任不產生司法裁定許可費之結果
在締約過程中,一方主體可能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給相對方造成了信賴利益損失或其它損失。這種損害行為導致的結果是賠償對方損失,并不能導致雙方締結合同。因此,一方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也不能產生司法裁定許可費(率)之結果。
綜上,在合同法上,法院違背一方當事人意愿,裁定專利許可費(率),強制在當事人之間建立許可實施合同關系只能基于一個法律事由——一方當事人具有強制締約義務。目前尚未發生法院認定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具有強制締約義務,并進而在當事人不能協商確定許可費(率)的情況下由司法裁定許可費(率)的案件。#1#0 不得含有的限制性條款包括:(1)要求受方接受與技術引進無關的附帶條件,包括購買不需要的技術、技術服務、材料、設備或者產品;(2)限制受方自由選擇從不同來源購買材料、零部件或者設備;(3)限制受方發展和改進所引進的技術;(4)限制受方從其他來源獲得類似技術或者與之競爭的同類技術;(5)雙方交換改進技術的條件不對等;(6)限制受方利用改進的技術生產產品的數量、品種或者銷售價格;(7)不合理地限制受方的銷售渠道或者出口市場;(8)禁止受方在合同期滿后,繼續使用引進的技術;(9)要求受方為不使用的或者失效的專利技術支付報酬或者承擔其他義務。#1 華為訴IDC公司案[(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7號、(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5號],一審判決的主審法官發表的文章雖然表達了認為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對標準實施者以及潛在的實施者負有以符合FRAND條件許可的義務,該義務與供水、供電、供氣等壟斷企業所擔負強制締約義務相似的觀點(參見:祝建軍、陳文全:《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率糾紛具有可訴性》,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4期,第8頁。),但在一審判決書中,并未直接表達出這種類比思路,而是以IDC公司在中國負有以FRAND條件向華為公司許可的義務,但IDC的要約不符合FRAND原則,華為如果不尋求司法救濟,就只能被迫接受IDC公司單方面所提出的條件作為論證理由,得出法院有權力裁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結論。終審判決又是以類比強制許可的思路,得出雙方可以自行協商確定使用費或者費率,協商不成,則可以請求相關機構裁決的結論,進而得出華為有權利申請法院裁定的結論(不是強制許可,必不會是行政機關裁定)。因此該案終審也沒有適用強制締約義務理論。#2 《反壟斷法》第50條: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二)反壟斷之訴不產生司法裁定許可費之結果
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可能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其行使專利權的行為有可能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根據《反壟斷法》第50條#2#0 不得含有的限制性條款包括:(1)要求受方接受與技術引進無關的附帶條件,包括購買不需要的技術、技術服務、材料、設備或者產品;(2)限制受方自由選擇從不同來源購買材料、零部件或者設備;(3)限制受方發展和改進所引進的技術;(4)限制受方從其他來源獲得類似技術或者與之競爭的同類技術;(5)雙方交換改進技術的條件不對等;(6)限制受方利用改進的技術生產產品的數量、品種或者銷售價格;(7)不合理地限制受方的銷售渠道或者出口市場;(8)禁止受方在合同期滿后,繼續使用引進的技術;(9)要求受方為不使用的或者失效的專利技術支付報酬或者承擔其他義務。#1 華為訴IDC公司案[(2011)深中法知民初字第857號、(2013)粵高法民三終字第305號],一審判決的主審法官發表的文章雖然表達了認為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對標準實施者以及潛在的實施者負有以符合FRAND條件許可的義務,該義務與供水、供電、供氣等壟斷企業所擔負強制締約義務相似的觀點(參見:祝建軍、陳文全:《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率糾紛具有可訴性》,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4期,第8頁。),但在一審判決書中,并未直接表達出這種類比思路,而是以IDC公司在中國負有以FRAND條件向華為公司許可的義務,但IDC的要約不符合FRAND原則,華為如果不尋求司法救濟,就只能被迫接受IDC公司單方面所提出的條件作為論證理由,得出法院有權力裁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結論。終審判決又是以類比強制許可的思路,得出雙方可以自行協商確定使用費或者費率,協商不成,則可以請求相關機構裁決的結論,進而得出華為有權利申請法院裁定的結論(不是強制許可,必不會是行政機關裁定)。因此該案終審也沒有適用強制締約義務理論。#2 《反壟斷法》第50條: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3#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被告實施壟斷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的,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查明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4 如注釋#1,華為訴IDC公司案,判決許可費(率)的論證思路也不是反壟斷法的思路。#5 這種類比若僅在學理上探討,尚具有學術意義。其實學術上,倒不如將FRAND承諾歸為默示許可更合適。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可以解釋為允許默示許可的存在。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的司法實踐中也有適用“默示許可”的案例。用默示許可理論解釋技術標準必要專利專利權人的許可授權問題,在我國法律上也不存在障礙。 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的規定,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承擔的民事法律后果有二:停止侵害、賠償損失。賠償損失自然不能導出司法裁定專利許可費(率)之結果。停止侵害,從語義理解,應該是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停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對于不按FRAND條件許可他人實施專利的行為(假定有該行為就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而言,結論應該是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按照FRAND原則授予他人專利許可實施權。
如果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開始以FRAND原則授予他人專利許可實施權,可以認為是承擔了停止侵權的法律責任。如果其仍然不能以FRAND原則授予他人專利許可實施權,則應當承擔拒不履行司法判決的責任。
不過,如何判斷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是否開始以FRAND原則許可他人實施其專利,可不可以法院在判決中確定一個合理的許可費(率)或范圍,以此作為標準讓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執行?單從文義看,尚不能得出清晰的結論。考慮到專利權人的法定獨占權地位,保護專利權人的利益是專利法的首要直接目標,本文認為不宜直接得出法院可以據反壟斷法判決一個使用費(率)的結論。如果有此需要,應采用司法解釋的方式進一步予以明確。目前我國也尚沒有以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為由判決使用費(率)的判例。#4#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被告實施壟斷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的,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查明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4 如注釋#1,華為訴IDC公司案,判決許可費(率)的論證思路也不是反壟斷法的思路。#5 這種類比若僅在學理上探討,尚具有學術意義。其實學術上,倒不如將FRAND承諾歸為默示許可更合適。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可以解釋為允許默示許可的存在。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的司法實踐中也有適用“默示許可”的案例。用默示許可理論解釋技術標準必要專利專利權人的許可授權問題,在我國法律上也不存在障礙。 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三)強制許可不產生司法裁定許可費之結果
華為訴IDC案終審判決將標準必要專利的FRAND承諾類比于專利強制許可,進而得出法院可以裁定專利許可費(率)的結論。
強制許可是國家知識產權局出于特定法定事由需要行使行政權力允許實施者直接實施他人專利的行政措施。學理上把強制許可按事由概括為不實施的強制許可、反壟斷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的強制許可、從屬專利的強制許可。標準必要專利的FRAND承諾與專利強制許可在擬解決的法律問題、發生機制、法律關系、法律后果方面均性質不同,沒有可比性。#5#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被告實施壟斷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失的,根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查明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告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4 如注釋#1,華為訴IDC公司案,判決許可費(率)的論證思路也不是反壟斷法的思路。#5 這種類比若僅在學理上探討,尚具有學術意義。其實學術上,倒不如將FRAND承諾歸為默示許可更合適。我國專利法的規定可以解釋為允許默示許可的存在。在我國專利侵權訴訟的司法實踐中也有適用“默示許可”的案例。用默示許可理論解釋技術標準必要專利專利權人的許可授權問題,在我國法律上也不存在障礙。 可參閱馬海生著:《專利許可的原則: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就強制許可而言,如果標準必要專利技術的實施者認為專利權人有壟斷行為,且具備了專利法上反壟斷的強制許可的條件,可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尋求強制許可,在不能商定許可費(率)的情況下,由國家知識產權局裁定許可費(率)。這種裁定不會發生在司法程序當中,除非因為強制許可而發生行政訴訟。但這種行政訴訟附帶的強制許可許可費(率)爭議的性質,與通過民事訴訟尋求法院裁定專利許可費(率)不同。
四、司法定價的導向性問題
司法是“被動”的,法院裁定專利費(率)有賴于當事人雙方的舉證。出于利己的動機,專利權人傾向于舉示能證明其索要的專利費(率)符合FRAND原則的證據。實施者傾向于舉示能證明專利權人索要的專利費(率)不符合FRAND原則的證據。此類證據通常會與既往的專利費(率)的數額有關,故有的證據顯示專利權人以往索要的專利費(率)高或至少與該案索要的許可費(率)大致持平,有的證據顯示,專利權人以往索要的專利費(率)遠小于該案索要的許可費(率)。
假定雙方舉證都較為充分,且證據的證明力大致相當,對相反的證據,法官如何采信就具有很強的導向意義。
是否滿足公平、合理、無歧視條件并不是僅僅限于根據案件當事人之間的報價進行判斷,而是具有很強的相對性。考察既往的專利許可費(率)情況、橫向同業者的專利許可費(率)情況,才能更好地判斷專利權人的要價是否公平、合理,尤其是是否存在對該案中實施者的歧視。當然,這需要既往的專利許可案例、同業者的專利許可案例信息可得,且有可比性。#6#6 這恰恰有很大困難。參見本文第一部分。#7 此處不考慮專利權人主張的專利是否屬于標準必要專利等情況。#8 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費(率)客觀上是否存在都不無疑問。
如果既往或橫向案例證明既有更高、又有更低的許可費(率),或者如果在案證據只顯示既往或橫向的許可費(率)更高,該案裁判結果一般會是認定專利權人的許可費(率)要價沒有違反FRAND原則#7#6 這恰恰有很大困難。參見本文第一部分。#7 此處不考慮專利權人主張的專利是否屬于標準必要專利等情況。#8 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費(率)客觀上是否存在都不無疑問。。但如果在案證據只顯示既往或橫向的許可費(率)更低,是否就必然得出專利權人的許可費(率)要價違反了FRAND原則的結論?
專利許可費談判中,當事人考慮的因素可能很多,例如類似于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案中總結的那些,但也可能很少,例如雙方的專利技術互補性很強,專利權利比較清晰,不用很多考慮就可以決策。甚至雙方的專利數量都太多,無法一一分析比較,只能簡單地“以數量定費用”。專利費的計算方式有多種,如一次性付費、入門費加提成、純提成方式等。對于專利權人而言,如果他預期實施者未來的實施規模不會很大甚至經營會有不小的潛在風險時,會傾向于采用一次性支付許可費的方式。相反,如果他預期實施者未來在市場上會比較成功,則會傾向于采用提成方式。對于雙方都存在并且無法避免的風險是:雙方是對未來的預估,未來總是不確定的。
以華為訴IDC案為例,在案證據顯示,IDC公司2007年與蘋果公司簽訂了期限為7年的許可合同,并采用一次性付費的方式,許可費折算下來,許可費率是0.0187%。而IDC公司向華為報價的許可費率高于此近百倍(據此算即是2%左右)。IDC給予三星公司的許可費率大約是0.19%(之前IDC贏得了對三星的訴訟)。許多媒體報道的ICT領域的許可案例,費率從終端設備售價的0.8%至百分之十幾不等。單看數值比,IDC報價在不同的企業間差異極其巨大。法院也正是參照IDC對蘋果收取的專利許可費率判決IDC只能按不超過0.019%的許可費率向華為收取專利許可費。但若我們假定,IDC公司在2007年與蘋果簽訂的專利許可合同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誤判。要知道,2007年蘋果公司剛剛推出第一款IPHONE手機,當時正是功能機“大佬”諾基亞如日中天之際。如果IDC證明是自己的市場誤判,法院是否仍應將對蘋果收取的許可費率作為參照基準值得考慮。假定這個案情,是為了提出,法院是否應傾向于按照既有或橫向的最低許可費(率)作為參照基準判斷專利權人是否遵循FRAND原則,并作為裁定本案許可費(率)的依據。
“以最低費率為準”的導向,對于個案中的實施者是有利的。在專利許可市場上,實施者很多時候也是專利權人,因此在整體效果上,有可能達到降低全市場專利成本的結果。這種結果是良性的。
但在同時,邏輯上我們不能得出結論——最低費率就是合理費率。如果費率低到傷害專利權人的正當利益——通過專利技術(創新)就應獲得的市場報酬,就違背了FRAND原則,FRAND原則只是抑制標準專利權人不當利用專利標準化帶來的市場優勢,不是限制乃至剝奪專利權人的創新利益。同時也損害了專利法鼓勵創新的宗旨。
因此,“以最低費率為準”的導向,其結果是未知的,全在于對客觀上存在的公平、合理費率的發現。以最低費率作為客觀上公平、合理費率是不恰當的。這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揭示的困境,法院在有限證據、有限信息、有限認知能力、有限審理時間的約束條件下,能發現客觀上公平、合理、無歧視的費率#8#6 這恰恰有很大困難。參見本文第一部分。#7 此處不考慮專利權人主張的專利是否屬于標準必要專利等情況。#8 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費(率)客觀上是否存在都不無疑問。?
結 語
本文研究的結論,不是標準必要專利實施者沒有訴權,亦不是法院對于FRAND糾紛完全沒有管轄權,只是證明法院難以有能力裁定一個公平的、合理的、無歧視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法院審理涉FRAND許可費(率)糾紛案件的目的不應在此。
那么,一個公平的、合理的、無歧視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誰說了算?一句戲謔的話也許就是真理:誰權力大誰說了算。
Th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licensing fee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FRAND; it is also the focus of the parties' disput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alculation of patent licensing fees are complicated. Although the patent valuation theory has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patent value, but there is no recognized effective method,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not recognized. Patent standardization strengthens the complexity of assessing the value of patents and patent licensing fees. Therefore, the court is diff cult to determine the patent license fees in line with FRAND. The dispute of license fee does no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suing in the Contract Law. Antitrust lawsuits and compulsory license will not lead to a court ruling on patent licensing fees. The court determines the license fee "at the lowest rate" may not meet FRAND, and may also damage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atente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licensing fee; judicial pricing
馬海生,法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