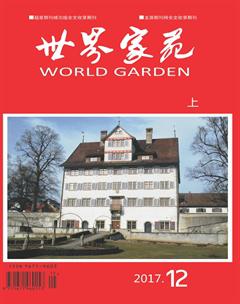博伊斯和他的社會雕塑
趙選寧
摘要:約瑟夫·博伊斯是德國激浪派,偶發藝術,行為藝術家以及雕塑家,裝置藝術家,圖形藝術家,藝術理論家和教育家。他的大量作品都基于人文主義,社會哲學和人類學的概念,并最終形成了他的社會雕塑的想法,為此他聲稱在塑造社會和政治方面具有創造性和參與性的作用。他的職業生涯的特點是公開辯論,涉及廣泛的主題,包括政治,環境,社會和長期的社會文化趨勢。他被認為是20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
關鍵詞:約瑟夫·博伊斯;激浪派;社會雕塑;創造性;參與性
1.故事的開始
隨著1944年3月16日的一聲巨響,博伊斯的飛機在在烏克蘭境內茲納緬卡市附近的克里米亞前線(Crimean Front)墜毀,隨后的故事我們都已熟知:他被游牧的韃靼部落救起,身上被包裹了毛毯和動物的脂肪以抵御嚴寒。雖然已無法證實這段陳述是否真實,毋庸置疑的是,毛毯和油脂成就了博伊斯日后最重要的藝術作品,這也使我們可以更加直觀的理解他有關社會雕塑(Social Sculpture)的想法。
但首先我要否定毛毯與油脂的各種象征意義,1983年博伊斯在德國Club 2的訪談節目上表示:“如果藝術背后的理論才是藝術本身的話,那我大可不必做能被感覺器官所接收的藝術品,寫一些有邏輯的話就可以了。”這句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入口,博伊斯認為藝術的目標并不是為理性服務的,它不應該被理性的解釋,比如問“這代表什么?”“這是什么意思?”相反的人們應該用感官充分的去感受,去滲透。
以《脂肪椅子(Fat Chair,1964)》為例,筆者在2017年參觀英國利茲藝術博物館(Leeds Art Gallery)的“藝術房間(Artist Room)”時,看到椅子上的脂肪已經融化至坍塌,而且相比于這件藝術品的首次展出時的情景,脂肪和椅子之間加上了一支溫度計,于是觀者明白,脂肪就是要化的。此時我們需要聯想某個場景來更直觀的體會:鏡頭鎖定這件作品,加速1964到2017年至半分鐘。我們會看到展館內人流來往,脂肪不斷溶化,其間的聯系變得顯而易見,人們在發出熱量,脂肪也在發出熱量。由此觀者無需去思考脂肪的象征意義是什么,要做的是感受自己發出能量時與周圍的聯系,這種聯系超越簡單的因果關系,它產生一種“諧振”(Resonate),消解了主客體的關系。在這里我們想到了希臘神話里的酒神狄俄倪索斯,以及尼采對醉的狀態的進一步闡述:作為醉的現實,這一現實同樣不重視個人的因素,甚至蓄意毀掉個人,用一種神秘的統一感解脫個人。我們細微的品味這一“神秘的統一感”,在每次身體上的運動,甚至是一呼一吸中,與融化的脂肪產生著共鳴。這種關系亦存在在他的作品《如何向死兔子講解繪畫(How to Explain Pictures to a Dead Hare,1965)》中,兔子化身為博伊斯的體外器官,他們通過一系列行為緊密相連,共同感受外部世界。通過人類對動植物的支配甚至殺戮行為,人類自己建立了屬于自己的主體性,博伊斯則通過這件藝術作品塑造了關于愛的“諧振”關系,思考人類與其他物種和物質的關系。
《毛氈大衣(Felt Suit,1970)》是一件兩件套的西裝,其中包括灰色毛氈制作的大衣和褲子,博伊斯在同年制作了100件相同的作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中。他表示作品可以用任何方式展出,然而在筆者所看到的博物館里,它們無一例外都被高高的掛在墻上,以防被參觀游客所觸碰。然而這種展覽方式并不符合藝術家的本意,這件作品使用簡單的標題來強調所使用的材料,他將脂肪與溫暖感覺的產生聯系在一起,在1979年,他表示有興趣制作表現進行的過程的雕塑,而非固定狀態的雕塑,回到毛氈大衣,我們便可以想象到最好的展覽效果自然是要將大衣穿在每個人的身上,讓肌膚切實感受到溫暖感。由此,這種變化性質衍生出了有關社會雕塑的設想,我們如何塑造自己和周圍的世界?
2.人人都是藝術家
博伊斯曾說人人都是藝術家,他之后也補充道,并不是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畫師,雕塑家或者建筑師,而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未來的社會設計師”。在雕塑社會形態這一抽象的概念,我們需要一系列具體措施和意識形態來發出能量——創造性(Creativity)的能量。
在7000棵橡樹(7000 Oak Trees,1982)正體現了生活中的創造性行為,這件作品在德國卡塞爾舉行的國際藝術博覽會Doumenta 7上開幕,內容是種植七千棵橡樹,每一塊都配有四英尺高的玄武巖柱,整個行為歷時5年。在種植的行為中,每個創造力的個體都貢獻出能量去參與創造,這本身就像一個理想的烏托邦式的民主模式,參與者在經歷能量輸出后會看到最后的結果,樹木的生長以及雕塑的形成的過程。這個作品具有獨特的視角和對藝術的深刻影響,在種植行為中呼喚起人們的創造力,當然站在參與者的角度思考,儲存使用創造力的感覺也是至關重要的。
博伊斯對雕塑的概念拓寬了藝術的邊界,相比杜尚,藝術變得更加日常更具功能性,同時也更難于捕捉。接下來我們要嘗試討論社會雕塑,話語與身份的關聯。受語言哲學家J.L.奧斯汀的影響,美國后結構主義學者,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關于性別操演(Perfonnativity)的新角度,在性別研究中,她否認存在一個先驗的主體,那么我們所認識到的“我”其實是在服從于一系列性別規范的重復行為的過程中遇見的。這些重復的行為大多遵循話語已經固定的社會觀念,例如:男人要有男子漢氣概,女人要有女人味兒。所以在巴特勒看來性別是一種持續的操演行為。這種持續行為與博伊斯的雕塑觀念十分契合,我們把語言看作是一種雕塑的工具,由于對話具有時間的屬性,就好像雕塑的過程,所以我們得到了由語言構建的雕塑,它承載著信息和情感,與博伊斯的社會雕塑不同的是,語言雕塑具備更多理性,觀點和立場,社會雕塑則訴諸身體與感覺器官。試體會一種感受,當使用不熟悉的第二語言和外國人交流時,人們會體會到自身無法被理解的束縛感,我們用語言提供給他者的雕塑無法被感知,猶如本體被囚禁。這種分離感也存在與爭吵中,爭吵大多意味著感性與理性同時與他人的碰撞,所以在這種情況中人們更傾向于讓事情變得合理,好像兩個人表示出愿意一同描繪這個抽象的語言雕塑的愿景,但也因此忽略了身體上的感覺。我在此引用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的兩個論述:
6.52.我們感受到盡管所有有關科學的問題都被回答了,生活本身的問題還根本沒有被觸及到。當然當所有的問題都被解答完,這恰恰就是答案。
3.對于不可說的,我們應當保持沉默。
當然有趣的是博伊斯沒有選擇沉默,相反的還是積極的通過演講或者辯論在說,他并沒有對語言和理性抱有過高的幻想,而是另辟蹊徑尋找身體上的更多可能。對博伊斯而言,對我們而言,身體與大腦,感性與理性,感覺與語言,它們中間存在著太多的未知空間,而這些空間我們可以通過藝術去感知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