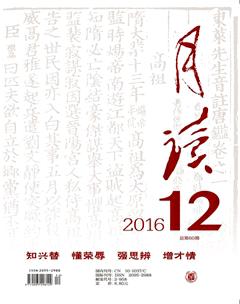鄭和:七下西洋一巨人
說起歷史上的大航海家,我們往往想到的是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這些在西方大航海時代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名字,尤其是1492年率領(lǐng)西班牙船隊遠航,并抵達了美洲的哥倫布,更是為人所熟知。其實,早于哥倫布出航八十多年,中國就出現(xiàn)了一位率領(lǐng)船隊劈波斬浪的大航海家。他,就是鄭和。
一、鄭和七次下西洋
鄭和,原姓馬,明洪武四年(1371)生于當時尚被元朝殘余勢力控制的云南。洪武十三年(1381),明朝平定云南,鄭和被俘虜至南京,成為宦官,配屬于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王府。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次年,燕王朱棣發(fā)動“靖難之役”,在戰(zhàn)爭中,年輕力壯的鄭和追隨朱棣作戰(zhàn),數(shù)次立功,逐漸成為一位“有智略,知兵習戰(zhàn)”的將領(lǐng)。朱棣登基稱帝后,鄭和因軍功被賜姓“鄭”,并升任內(nèi)官監(jiān)太監(jiān),擔任了內(nèi)廷(宦官)體系中的重要職務(wù)。因他小名“三保”,故民間習稱“三保太監(jiān)”,后來又訛寫為“三寶太監(jiān)”。
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六月,鄭和奉命率領(lǐng)一支船隊“通使西洋”。這個使團以鄭和為正使,另一宦官王景弘任副使,團隊成員既有宦官和文武官員,也有醫(yī)士、買辦、通事(翻譯)等技術(shù)人才,還有明軍將士兩萬余人。整個團隊乘坐當時稱為“寶船”的大小海船六十余艘,船只排水量多在千噸以上。就當時來說,這個規(guī)模的船隊是歷代罕見的,
鄭和一行從蘇州的劉家港(今江蘇蘇州太倉市瀏河鎮(zhèn))乘船出航,抵達福建后稍加休整,便揚帆西去,抵達了占城(古國名,在今越南南部)。自明朝建立以來,占城多次朝貢,鄭和以占城為遠航的首站,是非常謹慎的做法。
據(jù)《明史·鄭和傳》記載,鄭和抵達占城后,“以次遍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鄭和出航所到的國家大多在今印度洋海域,明朝時將這一帶海域稱為“西洋”,故民間有“三保太監(jiān)下西洋”的說法。船隊所到各國多對使團持友好態(tài)度,除接受明朝的詔書、禮物并回贈禮品外,還往往遣使者隨船到明朝訪問。永樂五年(1407)九月,鄭和的船隊回到國內(nèi),向明成祖匯報了出使經(jīng)歷,獻上各國的禮物,各國來華使臣也隨鄭和朝見了明成祖。
鄭和船隊航行的成功,以及各國紛紛遣使來華的盛大場面,使明成祖對航海出使有了很大的信心。在成祖的余生中,鄭和又于永樂六年(1408)、十年(1412)、十四年(1416)、十九年(1421)、二十二年(1424)分別率船隊出使,往返時間短者一年,長者兩年有余,這樣的長時間航海,在當時也是很少見的。
永樂二十二年,明成祖命鄭和出使舊港(今印尼的巨港),歸來時成祖已經(jīng)去世,其子朱高熾繼位,是為明仁宗。仁宗對其父北擊蒙古、南拓西洋的事業(yè)不感興趣,但對鄭和依然信任,故命鄭和“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仁宗去世后,繼位的明宣宗朱瞻基追慕成祖的事業(yè),于宣德五年(1430)歲末命鄭和再次統(tǒng)率船隊前往西洋各國。此時,鄭和已經(jīng)是一位花甲老人。從永樂三年到宣德五年,鄭和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了航海事業(yè),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
這次出航前,也許是因為預(yù)感余生無幾,鄭和在劉家港留下了《通番事跡記》碑刻,到福建后,又在長樂立有《天妃靈應(yīng)之記》碑,分別記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況。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九日,鄭和的船隊從福建起錨出海,周歷忽魯謨斯(今伊朗的霍爾木茲)等十七國,于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自忽魯謨斯返航。同年六月二十一日駛返劉家港。然而,鄭和并沒能看到祖國的土地,他于歸國途中在古里(今印度的科澤科德)病逝,享年六十三歲。船隊回國后,明宣宗得知鄭和去世的消息,下詔賜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達對鄭和功績的肯定和紀念。
二、“鄭和下西洋”的性質(zhì)與意義
鄭和七下西洋,前后歷經(jīng)二十余年,所為何來?從明代開始,就有對鄭和動機的探討。一種觀點認為,“靖難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蹤告終,成祖對這個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鄭和去海外搜尋。另一種觀點認為,成祖抱有“天朝上國”的理想,派遣鄭和遠航,是為了向南洋各國耀武揚威,逼迫他們來朝貢。《明史·鄭和傳》說:“成祖疑惠帝(即建文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就是對上述兩種說法的綜合。近代以來,針對這個問題,還有人提出過包抄帖木兒帝國、掃蕩張士誠舊部、解決“靖難之役”后士兵閑散無事問題等多種說法。
其實,早在宋元時期,我國與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各國的貿(mào)易就非常活躍,也不時有官方的通使往來。至明成祖時期,社會經(jīng)濟已經(jīng)從元末的戰(zhàn)亂中恢復(fù)過來,具備發(fā)展海上交通、開展海道貿(mào)易的基礎(chǔ)。鄭和每次航海歸來,總會帶回大量香料、染料、寶石、皮革等異國特產(chǎn),這些特產(chǎn)有的是所謂“貢物”,但主要還是貿(mào)易所得。當時,鄭和的船隊在滿剌加(今馬來西亞的馬六甲)“立排柵如城垣……內(nèi)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去各國船只回到此處取齊,打整番貨,裝載船內(nèi),等候南風正順,于五月中旬開洋回還”。我們從船隊的“番貨”需要專門整理分裝,已見當時貿(mào)易規(guī)模之一斑。不僅如此,鄭和船隊的翻譯人員馬歡在回國后,著有《瀛涯勝覽》一書,記載了他隨船隊所到的二十國的情況,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各地特產(chǎn)和貿(mào)易情況,如他記占城“其買賣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銀,中國青磁盤碗等品,纻絲、綾絹、燒珠等物,甚愛之,則將淡金換易”,記爪哇“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磁器并麝香、銷金纻絲、燒珠之類,則用銅錢買易”,等等。這是只有親歷貿(mào)易活動、深知其中三昧的人才能寫出的實錄。可見,鄭和的航海活動具有很強的海上貿(mào)易色彩。
此外,鄭和的航海活動也給國內(nèi)帶來了大量的白銀。根據(jù)史料記載,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一兩黃金可以折換四兩白銀,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兩黃金可換五兩白銀,金銀比價變動很小。然而,等到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歸來的永樂十一年(1413),一兩黃金已經(jīng)可以兌換七兩五錢白銀,而且不久后就變成了一兩黃金兌換十兩白銀,這顯然是國外白銀經(jīng)由海上貿(mào)易大量流入明朝國庫的結(jié)果。因此,明中期官員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對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航海活動評價說:“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
當然,鄭和的七次出海遠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孫宣宗的意旨“通使西洋”的,這就決定了鄭和下西洋不會是單純的海上貿(mào)易活動。第一次出航,周歷十余國,所到之處,鄭和都宣讀了明成祖的詔書,船隊回國時有各國使者隨船來訪,外交色彩很濃厚。此后的航海活動,也間有送使者回國或赴某國公干的,謂之外交活動,應(yīng)無大錯。在舊港,鄭和還打擊過當?shù)氐暮1I,為維護貿(mào)易秩序和國家尊嚴做出了貢獻,這又是一種軍事行動了。
所以說,鄭和下西洋,既是遵從明朝皇帝意志對東南亞、南亞和西亞進行訪問的外交活動,也是官方經(jīng)營海上貿(mào)易的一個縮影。鄭和憑借其杰出的個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國內(nèi)的豐富貿(mào)易資源為背景,在外交和貿(mào)易兩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來華的各國領(lǐng)導(dǎo)者中,事跡尤其顯著的,有渤泥國(古國,在今加里曼丹島)的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和蘇祿國(古國,在今菲律賓蘇祿群島)的東王巴都葛叭哈剌。這兩位國王都是在明成祖永樂年間率家屬和大臣泛海來華的,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熱情接待,卻不幸在中國因病去世。成祖對兩位國王的后事非常重視,不僅派遣官員致祭,而且命有關(guān)部門為其營護喪事、建造墓塋,對去世國王的家人也給予了妥善的安排。兩位國王的墓地現(xiàn)在仍受到良好的保護,是中國明朝與東南亞各國友誼的歷史見證,而締結(jié)這份友誼的使
者,則應(yīng)當首推鄭和。正因如此,《明史·鄭和傳》對鄭和的外交活動作出了很高的評價:“(鄭)和經(jīng)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自和后,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jiān)下西洋,為明初盛事云。”鄭和確實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
三、鄭和下西洋的啟示
雖然在鄭和去世后,明朝逐漸停止了大規(guī)模的官方航海活動,但“三保太監(jiān)下西洋”的故事長期在民間流傳。到了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1598),甚至有以鄭和航海活動為故事原型的《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刊刻出版。據(jù)作者自序,他撰寫該書的目的,在于以鄭和下西洋的故事來鼓舞時人抵抗倭寇的決心。鄭和在明朝人心中的地位之高,可見一斑。時至今日,距鄭和七次遠航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六個世紀,我們還能從中獲得哪些教益呢?
首先,鄭和的航海活動告訴我們,我國與亞非各國的友好關(guān)系,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鄭和每一次出海遠航,所到國家少者數(shù)國,多者十余國,一向秉承睦鄰友好的原則。我們以他最后一次航行為例。宣德六年底,鄭和率船隊離開福建,前往東南亞,經(jīng)占城、爪哇、舊港、滿剌加到達蘇門答剌(在今蘇門答臘島)。在這里,鄭和船隊分成了幾支分隊。鄭和本人率一支船隊,經(jīng)錫蘭山(今斯里蘭卡)、古里,航行至忽魯謨斯。其他幾支船隊,有一支經(jīng)溜山(今馬爾代夫)直航非洲東岸,訪問木骨都束(今索馬里的摩加迪沙)、不剌哇(今索馬里的布拉瓦)、竹步(在今索馬里朱巴河口一帶),另一支船隊在太監(jiān)洪保的率領(lǐng)下直航古里,訪問了阿拉伯海海域的多個城市。洪保到達古里時,古里正派船去麥加,于是洪保就派出以隨隊通事為首的七人小隊,隨古里的船只到麥加訪問。這一次航行,鄭和船隊先后訪問了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東非的十九國,不僅帶回了諸多珍奇貨物,還有力地擴大了明朝的國際影響。據(jù)《明史·宣宗紀》記載,在鄭和船隊歸國的宣德八年,有十九個國家和地區(qū)派遣使者訪問了明朝,其中有十五國屬于鄭和船隊航海所及之處,有些使者可能就是隨鄭和船隊前來明朝訪問的。這些古國有的現(xiàn)在還存在,有的已經(jīng)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但中國人民和亞非各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則毋庸置疑。
其次,鄭和的航海活動告訴我們,在國際交往中,友好往來是主流,但也要捍衛(wèi)國家自身權(quán)益。在通使西洋的船隊中,有供使團人員乘坐的“坐船”,有運輸糧秣物資的“糧船”“馬船”,也有載運將士、打擊海盜的“戰(zhàn)船”。船隊航行時,以戰(zhàn)船置于外圍,保護內(nèi)側(cè)的非軍事性船只。即便如此,鄭和船隊的航行也不總是一帆風順的。第三次下西洋時,鄭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今斯里蘭卡的錫蘭山寺布施,并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以紀行(此碑現(xiàn)存于科倫坡博物館),同時訪問了錫蘭山國。錫蘭山國的國王亞烈苦柰兒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義,把鄭和引誘到都城內(nèi),向他逼索財物,又發(fā)兵攻打鄭和的船隊。鄭和敏銳地看破了錫蘭山國主力在外、國內(nèi)空虛的狀況,率領(lǐng)所部官軍“中心開花”,出其不意地占領(lǐng)了錫蘭山國的都城,生擒亞烈苦柰兒及其妻子和官屬。前去攻擊鄭和船隊的錫蘭山國軍隊聽說都城被攻克,急忙回兵救援,船隊上的明朝官軍乘勢出擊,又大破敵軍。值得稱道的是,鄭和俘獲錫蘭山國君臣之后,并未在當?shù)卮箝_殺戒,而是將亞烈苦柰兒等人帶回明朝國內(nèi),交由朝廷處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沒有殺亞烈苦柰兒,而是下旨給予衣食,同時命禮部從錫蘭山國的國人中選擇賢者代之為王。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既捍衛(wèi)了國家的正當權(quán)益,為進一步開辟航路做了充分準備,又始終占據(jù)道義上的制高點。明成祖和鄭和能以恩威并施、輕重得宜的手段處理國際問題,證明他們是成熟的政治家。
第三,鄭和的航海活動告訴我們,一時的優(yōu)勢不是永久的優(yōu)勢,故步自封、安于現(xiàn)狀就會落后挨打。鄭和所乘坐的寶船究竟有多大,現(xiàn)代研究者最樂觀的看法是,大型寶船能達到排水量兩千五百噸的規(guī)模(這幾乎是木帆船的極限);即使是保守的觀點,也認為大型寶船的排水量在八百噸左右。而在流行于14世紀歐洲的柯克帆船中,大者排水量也不過五六百噸。15世紀產(chǎn)生的卡拉克帆船中偶見千噸級的大船,但百噸至數(shù)百噸的中小型船只仍是主流。所以說,即使與同時期的歐洲海上強國相比,明朝的造船技術(shù)也是很先進的。論遠洋航行能力,鄭和船隊最遠到達過東非,同時期在海上探險中走得最遠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還在探索西非的加那利群島、馬德拉群島、亞速爾群島等地,水平迥不相侔。我們完全可以說,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中國擁有同時期最為強大的遠洋船隊。然而,隨著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動,歐洲慢慢趕了上來。鄭和第七次航海結(jié)束的次年(1434),葡萄牙人突破了歐洲傳統(tǒng)觀念中的“世界邊緣”——博哈多爾角;1435年,葡萄牙船隊再接再厲,航行到了北回歸線以南地區(qū)。此后,受到激勵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不斷派出探險船隊,先后抵達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諸多地區(qū),并進行殖民和貿(mào)易活動。與此同時,適應(yīng)探險、作戰(zhàn)等各種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歐洲誕生。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出現(xiàn)了專門傳授航海知識的學校,加速了航海隊伍的建設(shè)。進入16世紀以后,葡萄牙人來到我們的家門口,與明朝發(fā)生了沖突,當時的葡萄牙戰(zhàn)船“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人眾,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fā),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這給當時航速慢、裝備差的明朝水師造成了很大困擾。此事發(fā)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距鄭和艦隊第七次航行歸國尚不到百年。這期間,我國戰(zhàn)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在抗風浪、船只規(guī)模等方面有所退化,這不能不說是明朝政府不重視遠洋探索,艦隊建設(shè)缺乏發(fā)展動力的結(jié)果。
鄭和的時代雖然過去了,但在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在東南亞,“三寶太監(jiān)下西洋”的故事仍膾炙人口;印尼爪哇省的首府三寶壟市,據(jù)當?shù)厝苏f,是因鄭和下西洋時在當?shù)氐前抖妹?005年4月25日,經(jīng)國務(wù)院批準,將鄭和首次出航的公歷7月11日定為中國“航海日”。同年7月11日,我國舉行了“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大會”。鄭和在航海活動中展現(xiàn)出的巨大勇氣和探索精神,以及中國與亞非各國之間的傳統(tǒng)友誼,會在當代得到更好的繼承和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