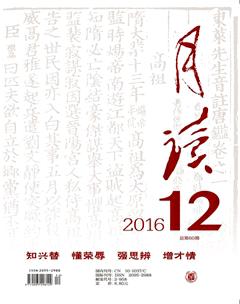北朝第一名士的人生悲喜劇(下)
張國剛
三、輔佐魏太武帝成就霸業
423年,拓跋嗣去世,太武帝拓跋燾登基。北魏進入大規模統一時期。崔浩是拓跋燾最重要的謀臣之一。滅赫連夏,破柔然,滅北涼,最終完成北方的統一,崔浩謀劃決策,運籌帷幄,往往引占星術佐助自己的論證,深得太武帝信任。
第一大仗是滅赫連夏,赫連夏又稱胡夏。
赫連勃勃,本姓劉,是匈奴貴族劉北辰之子。以統萬城(今陜西榆林靖邊縣)為都城,建立夏國。劉裕退兵后,曾攻入長安。425年,夏世祖赫連勃勃(381—425)死,其子赫連昌(?—434)即位。胡夏政權成為北魏選擇的打擊目標。“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
此時,北魏與北方游牧民族政權柔然的戰事并未了結,大將長孫嵩(358—437)等擔心,如果夏國堅城固守,以逸待勞,柔然大檀可汗(?—429)聞之,乘虛入寇,將十分危險。崔浩又搬出星象說事:“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己而行a,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于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拓跋燾完全采納了崔浩的意見,遣司空奚斤(369—448)等兩路人馬分別襲擊蒲阪(今陜西永濟)和陜城(今河南三門峽西),赫連昌企圖聯絡柔然負隅頑抗,仍然不敵北魏的進攻。427年七月,魏太武帝拓跋燾率軍力戰,攻入統萬城,消滅了夏國。a
第二大仗是破滅柔然。
柔然,北魏蔑稱之為蠕蠕,或謂東胡之苗裔,或稱匈奴之別種,是鮮卑拓跋部崛起時北方草原的勁敵,明元帝時曾修筑長城以御之。魏太武帝在擊破胡夏、北燕過程中,都要分兵防備柔然。429年,魏太武帝決心討伐柔然。臨行前,治兵南郊,舉行祭天典禮、誓師大會。“內外群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太武帝拓跋燾乳母竇氏)固止之,獨崔浩勸之。”
反戰派推出太史令張淵(《北史》避唐諱作張深)、徐辯為代表,稱述不宜出征的理由。張、徐二人過去是赫連夏主管天象的官員,是星占術方面的專家。他們說,今歲月食,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即使克敵,于主上也不利。他們的看法得到群臣的附和,說張淵當年曾經諫苻堅南伐,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拓跋燾有些猶豫不決,敦請崔浩與張淵等當面辯論。都是士人,都懂天文星象,崔浩號稱博學,可張淵等卻是專家。
對于張淵、徐辯的詰難,崔浩首先從星象開始:“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即發動戰爭)。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a,至今猶然。”這種天象意味著什么呢?“其占(指這種星象所指示的征兆),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b。蠕蠕、高車(北方游牧民族泛稱),旄頭之眾也。愿陛下勿疑。”
張淵、徐辯的失誤在于,他們沒有與崔浩在星象學上死磕,而是迅速轉換主題,說:“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
這下子,崔浩心底發笑了,回擊說:“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
崔浩又緊逼一步說,世人皆謂張淵、徐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兩年前夏國都城統萬未亡之前,你們作為夏國的天文專家,是否看出了敗征?若其不知,是無術也;若知而不言,是不忠也。當時胡夏亡國之君赫連昌就在辯論現場,張淵等確實未嘗預言,慚不能對。這樣的詰難,雖然使魏太武帝拓跋燾樂開了懷,也顯示出崔浩的伶牙俐齒、爭強好勝,總有些不夠厚道。
朝議會后,公卿有人擔心地對崔浩說:“今南寇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后有疆寇,將何以待之?”崔浩說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當年以劉裕之雄杰,吞并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斗虎狼也,何懼之有!”柔然恃其絕遠,以為我們力不能制,對我們的突襲沒有防備,“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短暫辛勞,換來的是永久安寧,此等時機,決不可失!“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a
太武帝拓跋燾親征,分道奇襲,柔然遁走后,魏兵舍棄輜重,輕兵追擊,直抵栗水(今黑龍江呼倫湖支流克魯倫河),大勝而歸。魏軍凱旋,回到平城,拓跋燾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于漠南,綿延三千里,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從此之后,“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b。
第三仗是滅北涼。
北涼(401—439)為匈奴支系盧水胡人沮渠蒙遜(366—433)創立,是十六國中的一個小國。北涼一直稱臣于北魏,沮渠氏與拓跋氏也是姻親關系。433年,沮渠牧犍(?—447)繼位,魏太武帝欲討之,先問崔浩。崔浩主張出其不意往擊之:“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拓跋燾稱善。
大將奚斤等三十人聯合反對,提出了兩條反對意見:一個是不必要,西陲下國,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罪惡未彰,何必動武;另一個是不值得,其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反戰派中的尚書李順,與崔浩為姻親,出身趙郡李氏家族,曾多次出使北涼,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力證其地皆枯石,絕無水草。“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坐實奚斤等人意見不虛。
是任其為朝貢之國,還是攻取為郡縣,這二者之間的差別,不言自明。因此,對于第一個理由大家不再堅持,于是“彼無水草”,就成為最主要的反對理由。
崔浩不愧號稱博學,他引《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怎么會在無水草之地筑城郭,建郡縣?再說,如果積雪融化之后,僅能收蓋住塵土,如何得以通渠溉灌?這不是明擺著在隱瞞真相嗎?李順堅持說:“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崔浩厲聲譴責:“汝受人金錢,欲為之游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雙方已經撕破了臉面。拓跋燾始終在會場之外隱蔽處聽著,聽聞至此,乃出來會見,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反對。a
及至攻下北涼,魏太武帝見姑臧(今甘肅武威)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崔浩回答:“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太武帝討伐涼州之前,太子拓跋晃也有疑慮。于是,太武帝特意寫信給太子晃說:“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溝渠流入大漠中,其間乃無干燥之地。”太子,你就放心吧!b
439年,魏太武帝大軍攻破姑臧(今甘肅武威)城,滅北涼,沮渠牧犍被擒,北魏終于統一了北方地區。
由于屢建奇功,拓跋燾對崔浩的欣賞,無以復加,可以稱之為北魏第一名士。皇帝到崔浩家就像朋友串門一樣,詢問災異之事。有時倉猝之際,崔浩不及束帶;有時恰逢用餐,有什么吃什么,雖非精美之食,拓跋燾必為之舉箸,或臨走時站著嘗一口,以示關系親密。
拓跋燾還引崔浩出入臥內,說:“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這番話的意思很明白:我有時候脾氣不好,你不要見怪,不要因此而噤口不言。
他曾指著崔浩,對新歸附的高車渠帥說:“汝曹視此人纖細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后施行。”a
431年九月,拓跋燾下詔,以太尉長孫嵩為柱國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長孫道生清儉廉潔。宮廷歌者唱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b這個歌詞是拓跋燾擬
定的。
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拓跋燾宴會上,拉著崔浩的手,對宗舒等人說:“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于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c魏太武帝請崔浩主持編修《國史》,也體現了對他的信任。
四、崔浩為何被殺?
崔浩的仕途,在魏太武帝時期,官至司徒,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卻也是在此時期,他被太武帝所殺,而且滿門抄斬。死后不到兩天,太武帝就頗帶悔意地說,崔司徒死得可惜。
其實,拓跋燾即位之時,崔浩的命運就有一些波折。《魏書·崔浩傳》稱:“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a《資治通鑒》記載這件事的時候,沒有“忌浩正直”四字,而且置于“尤不喜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之后。b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崔浩得罪的人不少,包括有佛教信仰的上層人士。
崔浩究竟得罪了誰?
崔浩在同僚之間說話,語氣比較沖,比較傲。包括對待胡族將領。他說長孫嵩長于治理,拙于用兵,可是,長孫嵩是北魏的名將,這話傳到他耳朵中,他能高興嗎?崔浩對太子晃也不放在眼中。《資治通鑒》是這樣記載的:“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拓跋晃反對說:“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征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太子的意思是,此前所征的士人(大約就包括高允等)任職時間長,應該先補州郡之職;新征之士應該先擔任郎吏等輔佐官吏,擔任郡守這樣的親民官,應該有一定的從政經驗,新征者并不合適。但是,崔浩“固爭而遣之”。
這件事的背景是,隨著北魏對北方統一的完成,很多地方郡守之類的文官,需要漢族士人出任,以方便統治漢地百姓,那些已經在政府任職的先征官員,與拓跋政權已經有很好的磨合,多少也有一定的合作經驗,太平真君四年(443)十一月,太武帝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崔浩無視太子的權威,“固爭而遣之”,實在是忘記了自己的本分。難怪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390—487)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a高允的意思是,崔浩的主張本來就不對,卻要與太子晃爭強好勝,恐怕沒有好下場啊。
在漢族門閥中,崔浩也樹敵甚多。
趙郡李順,同為士族高門,且是其姻親。426年,平定西夏時,拓跋燾欲以中書博士李順總前驅之兵,訪于崔浩,崔浩說:“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于去就,不可專委。”太武帝聽從了崔浩的話。“浩與順由是有隙。”b
神麚四年(431),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潁、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
于是,崔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盧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從,“由是得罪于眾”c。這個“眾”是多少人?從崔浩被殺,幾乎無人為其求情來看,崔浩其實在漢族儒士中已經很孤立。至于他是如何為漢族士人家族定流品高下的?我們現在沒有材料加以證明,但是,從其敢于出于一己之私,與太子晃爭執士族官員的任命上看,大約確實如高允所言:“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
在攻打柔然的問題上,崔浩與漢族出身的大將劉潔發生沖突,互相攻擊,最后以劉潔被罰告終。a《魏書·劉潔傳》說,劉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世祖心稍不平”。又說,劉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b。劉潔最后以謀反處死。崔浩其實也犯了與劉潔同樣的
錯誤。
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雖然到了太武帝時期,由于版圖的擴張,帶來了治理的復雜性,漢人參掌機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總體而言,漢族士人依然是參劃謀議的角色。神麚四年(431)廣征士人入朝,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三十五人,無一人任要職,即使是身為司徒的崔浩,雖獲寵任,手中毫無實權。c但是,隨著魏太武帝的寵任加深,崔浩就有些飄飄然了。
崔浩侄女婿王慧龍,出自太原王氏。東晉末,王氏被劉裕滿門抄斬,王慧龍輾轉來到北魏。在崔浩的策劃下,弟崔恬以女妻之。太原王氏家族素有齄鼻(酒糟鼻),江東謂之“齄王”。崔浩一見王慧龍的大紅鼻子,夸贊說:“確實是太原齄鼻王,真是貴種啊!”在朝廷公卿中逢人就夸贊不停。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對魏太武帝抱怨說,崔浩“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惹得魏太武帝大怒,特地把崔浩找來責難一頓,“浩免冠陳謝得釋”。王慧龍因此被壓著不予重用。d由此事可以看出太武帝對于漢人的疑忌。a
崔浩最后栽跟頭是在《國史》案上。
北魏的秘書監是一個學術機構,其下著作局主掌著述之事。有兩位著作令史(秘書)閔湛、郗標很會巴結崔浩,崔浩曾注《易》及《論語》《詩》《書》,水平如何,不得而知。這兩位下屬上疏皇上說,馬(融)、鄭(玄)、王(肅)、賈(逵)所注經書,不如崔浩注之精微,請收繳境內諸家所注經書,向全國頒發崔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請求國家正式命崔浩繼續注《禮傳》,“令后生得觀正義”。這不是明明給崔浩抬轎子么?官做大了,學問也就大了?馬融、鄭玄、王肅、賈逵,是東漢以來最著名的經學家,都不如崔司徒的經學水平?這種拍馬屁的言論,崔浩很受用,向朝廷推薦閔湛、郗標有著述之才。拓跋貴族大概不一定完全能搞清經書著述的優劣,可是漢族士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故高允說:閔湛、郗標干的這種事,恐怕會給崔大人找麻煩啊!這兩位馬屁精還建議把崔浩主持修撰的《國史》刊刻于石碑,以彰顯直筆。石碑立于郊祀祭壇之東,方圓百步,費功浩大。“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
罪狀。”
北人忿恚什么?“暴揚國惡”啊!把鮮卑族舊日的落后習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已經比較熟悉漢文明的鮮卑高層,對此已經高度敏感。也就是說漢鮮之間的民族矛盾,以這種方式暴露出來。之前,在北方統一戰爭中,鮮卑高層還需要漢族士人為其謀劃統籌,如今天下初定,對于漢族士人的高調行為,必須打壓,以儆效尤。崔浩的狂妄自大,招來殺身之禍,這是高允作為旁觀者看得很清楚的。
但是,事情還不至于如此簡單。用牽連到案情中的高允的話來說:“浩之所坐,若更有余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如果只是書寫國史的問題,罪不至死。那么還有什么“余釁”呢?高允說:“崔浩孤負圣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可見,崔浩有貪腐和枉法(愛憎蔽其公直)等罪。
公元450年農歷六月初十,平城的夏天,依然寒冷,崔浩的宗族及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并被夷族,其余被殺者數百人。在押送崔浩赴城南行刑的檻車上,衛士數十人往崔浩頭上溲尿,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兩天之后(六月十二日),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巡陰山,既誅崔浩而悔之,說:“崔司徒可惜!”a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不能說崔浩不懂政治,不能說崔浩不懂謀略。但是,政治有不同的層面,謀略有不同的側面。崔浩懂得謀事,不完全懂得謀身。謀身不是說要為自己的私利打算,相反,崔浩就栽在被私利私憤障蔽了自己的眼光和判斷力。謀身的最大保障是既明且哲,審時度勢,仁愛待人,知進知退;越是在官運亨通的順境中,越不要忘乎所以!崔浩倚仗皇帝的寵任,專權狂傲,死于非命!誠如魏太武帝所言:崔司徒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