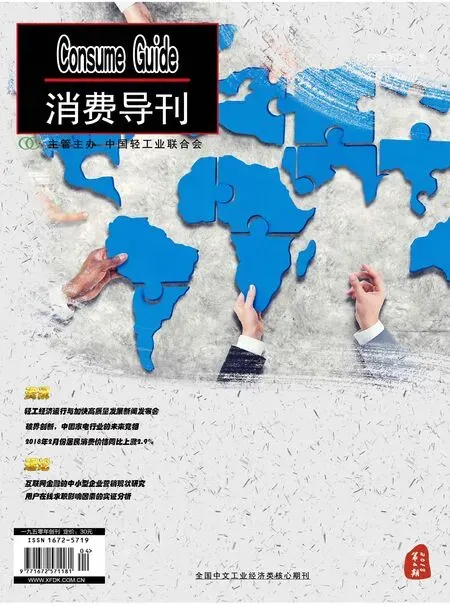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倒逼效應分析
邵博陽



摘要:中國民工問題由來已久,近兩年產能過剩和農民工返鄉潮等問題的出現加劇了農民工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間的矛盾。因此,借助產業結構偏離度和結構高級化指數,就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倒逼效應進行分析。
關鍵詞:農民工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結構高級化倒逼效應
2003年,民工荒的出現讓農民工問題躍成為焦點。農民工不僅僅是就業問題,還與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如何保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健康發展與相互促進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重視的個重要課題。
一、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化
中國最初的批農民工已經逐漸退出歷史舞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農民工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民工群體的就業傾向。當薪酬和工作環境不能達到他們理想預期時,他們就會做出其他選擇,“用腳投票”離開該行業。將2000-2014年各行業就業人數比例制成堆積柱形圖,可以看出農民工在行業選擇上出現了明顯的改變。
圖1 2000-2014年農村勞動力行業分布百分比堆積柱形圖
如圖1顯示,2000年到2014年,農村勞動力在第產業就業的人數比例直處于下降趨勢。2014年,農民工絕大部分被工業、建筑業和批零貿易餐飲業吸收,占到農民工總數的71%左右。
對于第二產業,就業的人數比例雖直在增加,但2008年之后,增速也有所放緩,至2014年的七年問,占比從24.25%上升到27.46%,僅提高了3.2%左右。并且其增長主要是由建筑業帶來的,農民工在工業就業的比例從2010年的高峰過后開始下降,由2010年的19.19%降低到2014年的16.03%。
第三產業的就業的比例則保持了較為平穩的增長,但增長并不明顯。在第三產業內,2000年從事交運倉儲和郵政業以及批零貿易餐飲業的農民工占總量的6.09%,到2014年這個比例上升到9.17%,上升了3.08%。但農民工在這些傳統服務業中就業比例的上升幅度是低于在第三產業中就業比例的變化,說明第三產業中其他行業的農民工數量的增長更加明顯。
可見,第產業轉移出的剩余勞動力最主要的流向從工業轉向建筑業。同時,流向第三產業的農民工也在穩定增多,并且從傳統服務業向現代服務業轉移。
二、農民工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同步性分析
某產業經濟的增長會促進該產業就業的增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時刻同步。農民工是傳統產業的主力軍,在其就業結構已然發生大幅變動的情況下,產業結構能否與之保持
致性是經濟穩步增長的重要前提。對產業前景的預期和對產業結構與全社會就業結構關系的判斷是農民工選擇職業方向的根據,因此農民工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矛盾是對產業結構亟待調整發出的信號。
(一)產業結構偏離度計算
本文采用產業結構偏離度作為分析工具來反映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關系。結構偏離度是就業結構相對于產業結構的偏離程度,是考察各產業結構與就業是否協調重要的指標之一。數學表達式為:
E=X/Y-1
其中,E為產業結構偏離系數,X為某行業的增加值與GDP之比,Y為行業就業人員與總就業人員數之比。
如果E=O,表明該產業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達到均衡狀態;如果E>O,說明該產業有繼續吸納勞動力的潛力;如果E (二)農民工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矛盾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2003-2014年問,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均衡狀況具有較大差異,對二者之間的結構偏離度進行分析,發現如下特點: (1)農林牧漁業的結構偏離度為負,基本保持在-80%左右。這意味著第產業還存在著剩余勞動力。農業就業業人員的比重雖然在大幅減少,第產業產值的比重卻也在不斷下降。使得E值保持在 定水平,難以提高。也就是說,第產業結構的首要矛盾,并非是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轉移的速度過慢,而是更為嚴峻的,第產業的生產效率難以提高。 (2)工業的結構偏離度為正,但是偏離程度并不大,并且2008年以后開始減小,趨近于0。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潛力在降低。造成這結果的原因并非工業增加值和工業就業人員的持續上升帶來的結構均衡,而是由于工業吸引農民工的能力在降低。由于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組織結構不合理、管理水平較低等問題,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行業近幾年發展并不景氣,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下降。加之農民工大量返鄉就業、創業,都極大的沖擊了工業的發展,使得大量勞動力流出。可以看出,工業方面的產能過剩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經顯現。如不盡快提升產業結構,未來幾年的工業即使以提高工資為代價挽留住勞動力,也將以衰退的姿態迎來低水平的均衡。 (3)建筑業的結構偏離度為負,并且偏離程度較大。這表明建筑業也產生了定的剩余勞動力。建筑業農民工的比重直在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近十年來房價飛漲,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及房地產開發投資不斷擴大,幾乎各個城市都在新建住房,勞動力需求大。從房地產業極高的結構偏離度我們可以發現,房地產業屬于暴利行業,而基礎層的建筑工人作為體力工種,薪水也較高,吸收的勞動力數量自然不在少數。但近兩年房地產業開始向常態邁進。2015年已有數據顯示,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多項指標惡化,可能在未來幾年里,建筑業產能過剩的惡果也將凸顯,對勞動力需求會大幅減少,剩余勞動力應轉向其他產業。 (4)第三產業的情況較為復雜。農民工主要從事的交運倉儲及郵政業和住宿和餐飲業的結構偏離度分別在0左右波動和趨近于0。這說明這些對勞動力文化素質要求相對較低的產業已基本達到均衡。批發和零售業的偏離度的提高,則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了可行性。總體來說,傳統服務業是吸收農民工的主要行業。可是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不高的現狀,限制了其進步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尤其是其中現代服務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并不強,仍存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酒店餐飲和家政等服務行業。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作枯燥乏味,重復性高,很難實現人真正的價值,將難以吸引到新生代農民工。于是,農民工的供給結構便會更加無法滿足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需求,加之農民工跳槽成本低,企業不僅勞動力成本在增加,培訓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在農民工群體的結構已發生巨變的情況下,產業結構的滯后,必然會造成勞動力市場供求的失衡。
三、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
通過對農民工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矛盾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農民工自身觀念和身份的“升級”走在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前面,農民工的就業結構變動不僅是產業結構問題造成的結果,最終也會倒逼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因此,可以對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果進行驗證與分析。
(一)結構高級化的度量
對于結構變動的衡量通常使用Moore指數,該方法運用空間向量的夾角來反映產業內部結構變動程度。本文采用在Moore指數的基礎上提出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構建方法(周明磊,2011)。該方法通過調查將產業由低級向高級排序,列為第產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批發零售餐飲住宿業和金融房地產業。由于農民工就業部門結構的高級化與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方向趨同,所以對各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和增加值比重運用同樣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構建方法進行處理,并將結果依上述排列計以不同次數,以反映高低級產業對結構高級化指數影響的不同比重。計算公式如下:
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受數據限制,以1986年為基期計算中國農民工就業結構高級化指數。近20年變動情況如表2所示:
(二)農民工就業結構變動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回歸分析
以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UIS)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農民工就業結構高級化指數(UES)作為解釋變量,構建元線性回歸模型。其中:α為常數,β為參數,ε為隨機誤差。
UIS=α+βUES+δ
經過ADF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對UlS和UES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顯示(表4),在0.1的顯著性水平下,UES是UIS的Granger原因,所以農民工就業結構的高級化會影響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農民工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矛盾分析,發現農民工就業結構的變動既是產業結構問題造成的結果,也是最終倒逼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的直接原因之一。農民工文化素質的提升和市民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其就業結構的高級化,對產業結構的升級具有推動作用。
要想實現產業結構調整,首先農業應轉變發展方式,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其次,東部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向中西部、中小城市轉移,以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加快現代服務業和新型工業發展,把有限的資源集中于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最后,勞動者素質的不斷提高也不可或缺。政府應加大財政上對農村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投入,實現農民工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同步高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