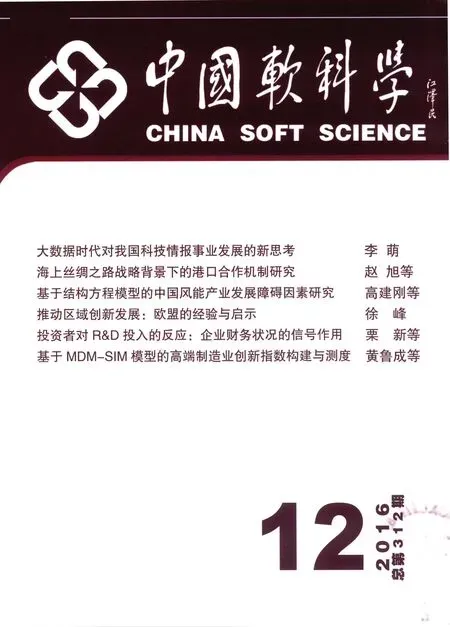“營改增”視角下流轉稅改革優化了產業結構嗎?
孫 正
(天津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200)
“營改增”視角下流轉稅改革優化了產業結構嗎?
孫 正
(天津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天津 300200)
稅制改革是我國經濟轉型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推動力。本文構建了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理論模型,重點考察“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與影響效果。并運用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實證檢驗“營改增”改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影響。研究表明: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降低了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占比,提高了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占比,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定量測度“營改增”對產業結構優化的貢獻程度,發現面對營業稅變量的沖擊第二產業反應程度更大,面對增值稅變量的沖擊第三產業反應程度更大。最后,依據數理模擬與實證分析結論,提出產業結構優化的政策啟示。
流轉稅;“營改增”;PVAR模型;產業優化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經濟增長不僅受到產業變遷的影響,經濟發展本身也可能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從理論層面講,探討產業結構優化的內在機理,可以在宏觀理論與中觀理論之間搭建橋梁。從政策層面上看,如果經濟發展是產業結構變遷的結果,那么產業結構優化就是政府發展經濟的必然選擇。現實經濟中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因素復雜多變,而這其中財稅政策無疑是關鍵的因素之一,產業結構優化進程與政府財稅政策息息相關。財稅政策通過影響稅收結構與負擔數量引起產業結構變化,同時稅制改革也是我國經濟轉型與產業結構重大調整的主要推動力之一。財稅改革的產業調整效應也是稅制結構效應重點研究領域,事實上政府大部分產業政策的出臺都是圍繞著稅收工具展開,或者有具體的財稅政策予以配套。考慮到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經濟環境日趨復雜,稅制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也更為多變,我們不禁要問,稅制改革如何影響產業結構變遷?通過稅制改革實現產業結構演進升級又是否可行?
產業結構作為過去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階段結果和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基石,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長期關注。國外學者主要通過恩格爾效應和鮑莫爾效應解釋產業結構的變遷。恩格爾效應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個人或家庭對農產品、工業品以及服務業的收入彈性不一樣,從而帶來產業結構的變遷,代表性作品有Kongsamut,Rebelo和Xie(2001);Buera和Kaboski(2012)[1-2]。鮑莫爾效應主要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產業結構變遷進行解釋,隨著全要素生產率在不同產業與部門之間的調整,帶來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的重新調配,進而帶來產業結構變遷,代表性著作包括Ngai和Pissarides(2004);Acemoglu和Guerrieri(2008)[3-4]。Dennis和Iscan(2009)考察了美國近一百多年的數據發現,二戰之前美國產業結構變遷主要受恩格爾效應影響,二戰以后鮑莫爾效應對美國產業結構變遷影響更大[5]。Rajan R G和Zingales L(2001)研究發現政府通過財稅政策為成長期中小企業的資本運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6]。Rogerson(2008)考察1956至2003年,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稅收、技術以及工作時間的演變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的差異[7]。Esteban-Pretel和Sawada(2009)以日本為例,考察了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勞動力流動障礙是否抑制了產業結構變遷[8]。Alvarez-Cuadrado和Poschke(2011)研究發現,農業生產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勞動推動效應,非農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勞動吸引效應,此兩種效應相互作用使勞動力更多的流入到非農業部門[9]。Herrendorf、Rogerson和Valentinyi(2013)研究了美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各行業財政支出的份額,發現消費性支出是產業結構變遷背后的主導力量,并且產業的增加值效應占據主導地位[10]。Lin等(2014)考察了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對不同行業發展的影響,認為寬松的市場環境,比較少的市場干預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11]。
國外也有經典文獻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研究。Vandermerwe和Rada(1989)指出,需求結構的驅動是產業結構升級演進最大的動力機制[12]。Robinson(2002)認為傳統產業以成本管理為導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主要扮演了創造競爭優勢以及差異化優勢的角色[13]。White(1999)研究發現企業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主要是為了獲得競爭優勢[14]。Roos(2013)指出產業結構升級演進過程中,有形的產品被無形的服務取代,這成為企業競爭優勢關鍵所在[15]。另有部分國外學者研究了財政行為波動性與產業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Ramey G和Ramey V A(1995)、Ali(2005)、Afonso和Furceri(2008)、Bleaney和Hallad(2009)均發現政府財政支出的波動對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6-19]。Lichtenberg(2008)和Lucas(2011)認為在市場化初期,地方財稅政策對產業結構變動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但財政支出水平的波動對轉型升級有顯著的抑制作用[20-21]。
對國內學者過往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大多數學者都是從稅收政策與稅收優惠兩個方面考察其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也有部分學者研究金融抑制等因素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魏福成等(2013)以新政治經濟學為分析工具,從新的視角探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因素,考察了中國式分權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抑制作用[22]。王文舉、向其鳳(2014)將財稅政策引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投入產出動態模型,對產品出口結構以及消費結構進行預測[23]。汪德華(2007)利用跨國橫截面數據,實證分析政府規模、法治水平與一國服務業比重之間的關系[24]。郭曄、賴章福(2011)運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不同區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25]。王勛、Anders Johansson(2013)運用經濟結構轉型模型,計量檢驗金融抑制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的關系[26]。張婕等(2013)從“制造-服務”國際分工的視角深入考察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需求滯后的原因,認為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可能會抑制產業結構的升級演進[27]。安苑、王珺(2012)探討了地方政府財政行為波動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影響[28]。劉悅等(2016)探討了價格與金融規模兩種配置方式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動態特征,闡述金融資源配置對產業結構變遷的作用機理[29]。李鋼等(2011)對發達國家三次產業效率與中國產業結構效率做了對比,研究發現財稅政策對中國產業結構效率的影響較為顯著[30]。
近年來土地財政收入占我國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部分學者從土地財政視角對產業結構優化進行解讀。曹廣忠等(2007)從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激勵的視角考察產業結構優化的演進升級,實證檢驗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促進作用[31]。國亮、王一笑(2015)在地方政府財政軟約束的前提下,探討我國土地財政對不同產業稅負的影響,進而分析其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32]。李勇剛、王猛(2015)研究發現土地財政明顯阻礙了產業結構服務化,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33]。也有部分學者考察財稅政策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影響。張同斌、高鐵梅(2012)通過一般均衡模型(CGE),考察財稅優惠政策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及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34]。王宇、劉志彪(2013)運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宏觀層面上,利用特定要素模型,研究不同補貼方式對傳統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的影響[35]。陸國慶等(2014)構建了包含外溢效應的超越對數CDM模型、并應用迭代3階段最小二乘法(IT3SLS),分析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補貼的績效評價[36]。柳光強、田文寵(2012)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稅收政策進行考察,依據稅收工具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提出加快發展我國戰略新興產業的稅制設想[37]。
另外,國內學者考察了財政支出、補貼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內在經濟邏輯。張培森、付廣軍(2003)分析財政補貼對各行業稅源規模及其增長速度的影響,分析得出財政補貼對稅源、稅基的擴大具有顯著影響[38]。郭小東等(2009)認為政府通過財政支出改變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的配置,并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改善,提高資源在第三產業的配置,抑制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降低了第一與第二產業中的要素配置[39]。石奇、孔群喜(2012)分析了政府生產性支出對不同產業要素積累的影響,認為財政支出不但影響國民經濟三次產業之間的資源配置,而且改善了產業內部生產要素的投入[40]。褚敏、靳濤(2013)研究發現中國經濟轉型大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特別指出中國特色財政支出的行政壟斷是抑制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41]。宋凌云等(2013)運用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政府補貼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研究發現政府補貼從短期來看可以影響產業結構變遷,但從長期來看效果有限[42]。
通過對前述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國內學者很少系統全面從流轉稅改革視角研究產業結構優化。與已有的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貢獻體現在:第一,借鑒Baumol(1967)提出的非均衡增長模型,將流轉稅改革變量引入,數理模擬“營改增”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豐富拓展了此類文獻。第二,從多個維度上,定量測算了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并對“營改增”影響不同產業占比變動的貢獻程度進行了對比,為后續產業結構調整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啟示。
二、影響機理與模型構建
在分析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作用機理基礎上,將“營改增”改革變量引入到非均衡增長模型。模型構建主要借鑒李勇剛和王猛(2015)文獻,數理模擬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傳導機制與作用機理,并提出有待檢驗的假說。
(一)“營改增”改革影響產業結構的作用機理
從稅制改革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影響過程來看,稅制改革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可以表現為“信號發出——傳遞信號——接收信號——信號反饋”的過程。首先,國家通過“營改增”改革發出產業結構調整的信號,通過稅制改革的替代效應與總量效應改變企業的投資收益率。其次,稅制改革通過改變企業的投資收益率,進而改變企業的投資結構與資源配置方向,將稅制改革的信號傳遞給微觀企業主體,微觀企業主體通過改變要素投入方向與資源配置調節整個社會的資本投向。最后,企業依據稅制結構變動帶來企業稅收負擔的調整,改變產業間以及產業內部投入結構,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級化。
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稅制改革作為近年來財稅領域最重要的政策調整,將原來增值稅并行于第二產業、營業稅并行于第三產業的二元流轉稅稅制模式,徹底轉變為以增值稅為主體的一元流轉稅稅制模式。產業結構的演進與升級主要取決于不同行業的資本回報率,我國一般政府預算收入超過70%來源于流轉稅,而流轉稅的稅負最終是由企業承擔,“營改增”所帶來稅負與稅制結構的改變必然導致不同產業資本回報率的變動。“營改增”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調整稅負在不同產業間的分配,“營改增”徹底貫通了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以及第三產業內部的增值稅抵扣鏈條,實質上對第三產業來說是一種變相的減稅。同時也為二三產業相互融合提供更好的稅制環境,綜合來看“營改增”降低了第三產業的稅收負擔,有利于資本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二,基于對稅收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機理可知,差異化的稅制結構影響投資、消費、資源配置,“營改增”帶來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之間商品稅負擔的調整,最終必然體現在商品服務的價格上,進而改變需求,有利于傳統工業轉型為服務型工業,促進工業服務化。
(二)理論模型構建
2015年,第一產業占我國GDP比重僅為5.1%,同時考慮到流轉稅的稅種屬性及其對第一產業作用的局限性,我們假設經濟系統中只有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將“營改增”改革變量引入到Baumol(1967)[43]提出的非均衡增長模型中,數理模擬“營改增”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傳導機制與作用機理,從流轉稅改革視角為產業結構優化提供經濟解釋。
在模型構建過程中,我們只考慮“營改增”改革對第二、第三產業的影響。其中,假設第二產業主要要素投入包括三部分勞動、資本、財政支出(主要來源于稅收,可近似地等價于稅收);考慮到第三產業主要是服務業,假設勞動為第三產業的主要投入要素,同時將一部分第二產業的產品作為中間投入。兩部門生產函數表達如下:
(1)
(2)
(3)
(4)
(5)
(6)
其中,n表示勞動人口增長率,κ為儲蓄率,g表示財政支出增長率,τ為稅收收入增長率,因政府支出近似地等價于稅收可知τ=g。那么,由公式(1)與(4)聯立,可以得到資本增長率的表達式為:
(7)
求公式(7)關于時間t的導數,并將公式(3)、(4)、(5)代入,可得:
(8)
(9)
同時,公式(9)分別與公式(1)、由公式(2)聯立,可得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產出增長率,公式(10)為第二產業產出增長率,公式(11)為第三產業產出增長率。
(10)
υ3=ρn+θυ2
(11)
本文主要考察“營改增”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為了數理模型的方便,我們令λ表示第三產業產出增長率與第二產業產出增長率的比值,即:λ=υ3/υ2,如果“營改增”與相對增長速度λ具有正相關關系,這就意味著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優化了產業結構,進一步可得:
(12)
隨著“營改增”推廣到全行業,增值稅徹底取代營業稅,完善了增值稅抵扣鏈條,減稅總額粗略估算超過一萬億,“營改增”從本質上說降低了第三產業的總體稅負,有利于資源配置向第三產業傾斜,促進傳統工業服務化。基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營改增”與稅收增長呈現負相關關系,我們假定稅收增長率τ=f(cta),cta表示“營改增”改革變量,可知f′(cta)<0。通過前述公式(6)可知,政府支出增長率與稅收增長率相等,將τ=f(cta)代入公式(12)中得:
(13)
對于不同的參數估值,相對增長速度λ的經濟含義不同,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經濟解釋:第一,當(1-β)ρn>(1-θ)[αn+f(cta)γ],此時λ>1,那么υ3>υ2,這時的經濟含義為第三產業的相對增長速度更快。第二,當(1-β)ρn=(1-θ)[αn+f(cta)γ]時,此時λ=1,那么υ3=υ2,這時的經濟含義為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與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相等。當(1-β)ρn<(1-θ)[αn+f(cta)γ],此時λ<1,那么υ3<υ2,這時的經濟含義為第二產業的相對增長速度更快。我們對求公式(14)關于“營改增”變量cta的導數:
(14)
因為f′(cta)<0、1-β>0,可知?λ/?cta>0,其經濟含義為相對增長速度(λ)與“營改增”改革(cta)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營改增”改革會提高相對增長速度。這說明“營改增”改革所帶來的稅制改革效應使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第三產業,優化了產業結構。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有待檢驗的命題:隨著增值稅徹底取代營業稅以后,營業稅、增值稅并行于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流轉稅二元模式轉化為一元流轉稅稅制模式,那么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優化了產業結構。
三、計量模型與指標設定
在前述理論模型構建基礎上,為突破傳統回歸方法的局限性,克服省級面板數據可能存在的個體效應,并且考慮到模型估計方法的可操作性。本文運用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從多個維度刻畫“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
(一)計量模型構建
根據Inessa Love、Lea Ziccino (2006)提供的 GMM估計方法[44],特設定如下模型來考察“營改增”改革對結構變遷的政策沖擊效應:
+φtfi+εi+μit
(15)

本文核心議題是“流轉稅改革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解釋變量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核心解釋變量,包括流轉稅(ctit)、營業稅(btit)和增值稅(vtit)三個變量;第二部分為控制變量。因此,本文用于分析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的PVAR模型可以具體表述為:
公式(16)為“營改增”改革對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的影響:
(16)
公式(17)為“營改增”改革對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的影響:
(17)
公式(18)為“營改增”改革對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的影響:
(18)

(二)變量與數據
1.變量設定
本文運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PVAR)檢驗“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優化的政策沖擊效應,并定量測算“營改增”對我國產業結構變動的貢獻程度。模型中變量設定主要包括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組三部分。

核心解釋變量:cta變量為計量模型的核心解釋變量,包括流轉稅(ctit)、營業稅(btit)、增值稅(vtit)三個變量。財稅政策是政府調整產業結構最重要的手段,而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考察“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因此,本文將上述三個變量設定為計量模型的主要政策沖擊變量。
其它控制變量:主要考察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其它系統性因素:(1)經濟發展程度(pgit),(2)城鎮化率(urit),(3)固定資產投資比率(fiit),(4)利用外資水平(fdiit),(5)政府規模(sgit),(6)經濟開放程度(owit),(7)人口密度(pdit)。表1是對模型各變量的經濟解釋。
2.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30個省級單位進行研究,西藏由于部分年份存在數據缺失,同時部分變量波動性太大,所以從樣本中剔除。我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

表1 主要變量說明
注:變量為作者定義

3.變量統計性描述
表2是對實證檢驗中各個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的結果。為了盡可能地消除異方差,本文按照表1中的要求對變量進行了處理。包括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樣本數、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從核心解釋變量的種類來看,增值稅變量的樣本均值大于營業稅變量的樣本均值。
四、主要實證結果
本文將從多個層面上檢驗“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計量檢驗的主要步驟包括廣義矩估計(GMM估計)、脈沖響應圖、方差分解三個部分。對于長面板數據,在做計量檢驗之前必須檢驗其是否平穩,主要目的是防止出現虛假回歸。如果進行VAR檢驗的變量不平穩,估計參數存在偏誤,則不能準確反映變量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一)平穩性檢驗
為更全面檢驗各個變量的平穩性,考慮到不同檢驗方法側重點不同,本文選擇IPS檢驗、LLC檢驗以及HT檢驗三種方法,考察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組的平穩性,得出結果見表3。結果顯示各個變量序列屬于平穩序列,可以進行后續實證分析。
(二)參數估計方法
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計量模型估計,主要是借助于連玉君(2010)編寫的PVAR2程序包。考慮到模型的有效性與穩定性,我們采用(AIC)信息準則判定P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通過檢驗發現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通過前述公式(16)-(18)模型的設定可知,模型的解釋變量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為了更好地控制個體效應以及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GMM)對模型參數進行有效估計。
(三)核心解釋變量實證結果
實證分析主要包含“營改增”對國民經濟三次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所有的計量檢驗過程都是采用stata12軟件。為了更全面地考察“營改增”對各個產業的政策沖擊效應,我們用如下三個部分考察政策的沖擊效應:第一,PVAR方程GMM結果,描述“營改增”改革沖擊對產業結構變動正負效果;第二,脈沖響應圖,刻畫“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動影響是否平穩;第三,方差分解圖,測算“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動的貢獻程度。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資料來源:依據各年度以及各個省級單位《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稅務年鑒》等整理

表3 各序列平穩性檢驗
注:***代表在該系數1%的置信水平通過檢驗,**代表在5%的置信水平通過檢驗,*代表在10%的置信水平通過檢驗。
1.PVAR模型的GMM估計
PVAR模型實際是包含固定效應的動態面板模型,在進行 GMM 估計之前首先采用組內均值差分法去除時間效應,然后用向前均值差分法去除個體效應。由傳統的VAR模型的原理可知,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并不區分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而是將所有的變量都等同為內生變量。所以本部分產業結構、營業稅、增值稅、流轉稅等變量均作為PVAR模型的內生變量。對于“營改增”改革對三次產業占比政策沖擊的檢驗,主要來自于公式(16)-(18)實證分析結果。表4為PVAR模型的GMM估計結果,分別是“營改增”對三次產業結構占比的實證分析結果。
依據表4中估計結果可知,被解釋變量為h_Y1方程的計量檢驗結果主要來自于公式(16),可以看出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的h_bt與h_vt變量實證檢驗結果都不顯著,這說明“營改增”改革對第一產業占比變動沒有影響,或者說是解釋力度不大,這主要是由于流轉稅主要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為課稅主體。另外,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變量

表4 PVAR模型的GMM估計結果
注:使用stata12軟件整理,***、**、*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通過檢驗,h表示對各個變量進行前向差分,括號內的數字則代表估計系數的t檢驗值,對所有數字均保留兩位小數。
h_Y1方程系數都為正,這說明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存在著自我增強機制。被解釋變量為h_Y2方程的計量檢驗結果主要來自于公式(17),營業稅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變量對第二產業比重變動的影響均較為顯著,并且估計系數符號都為正,這說明營業稅變量對第二產業占比的變動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正向影響。增值稅變量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對第二產業占比變量估計系數符號都為負,這說明增值稅變量與第二產業占比變動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被解釋變量為h_Y3方程的計量檢驗結果主要來自公式(18),營業稅變量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對第三產業占比影響顯著,并且估計系數符號顯著為負,這說明營業稅變量對第三產業占比變動有一個負向的影響。增值稅變量滯后一期與滯后兩期對第三產業占比估計系數符號都為正,這說明增值稅變量與第三產業占比變動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綜合分析來看,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降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提高了第三產業的比重,優化了產業結構。
2.脈沖響應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內生變量對于誤差變化大小的反應,是從動態反應角度判定各變量間時滯關系的一種方法,可以分析當某一個變量在基期發生單位變化時,對其它變量的影響程度,可以很直觀地刻畫變量之間的動態交互效應。這種動態反應主要是在其它變量對被解釋變量不產生影響的前提下,通過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信息差的沖擊對其它變量當前和未來值的影響軌跡來衡量。另外,我國每屆政府任期為5年,任期最多兩屆,為更好地刻畫流轉稅改革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動態傳導機制,我們將脈沖響應圖持續時間設定為10期。圖1 是本文通過模特卡羅500次模擬得到的“營改增”對三次產業占比變動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圖。
圖1中橫軸表示脈沖響應的時間維度,虛線表示零刻度線。三條實線中,中間實線表示“營改增”改革政策沖擊程度,兩側實線表示95%的置信區間。通過分析可知,對于一個標準差的流轉稅(ctit)變量的沖擊,第二產業在當期就有一個負向脈沖響應,第1期逐漸達到頂峰,然后開始遞減,在第6期以后逐漸平穩,第三產業當期有一個較大的正向脈沖響應,在第8期以后逐漸減少到0。對于增值稅(vtit)變量一個標準差沖擊,第二產業占比當期有一個負向脈沖反應,這個脈沖響應在第2期達到頂峰,到第6期以后衰減為0,第三產業在當期有個比較大正向脈沖響應,這個脈沖響應在第1期就達到頂峰,直到第10期才減少為0。對于營業稅(btit)變量一個標準差的沖擊,第二產業占比開始有一個正向的脈沖響應,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小,到第8期以后逐步衰減為0,第三產業占比有一個負向脈沖響應,第1期達到頂峰以后逐步減少,第6期以后趨向于平穩。另外,面對營業稅(btit)、增值稅(vtit)變量的沖擊,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的反應并不是很明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脈沖響應程度也顯得雜亂無章,繼續通過考察流轉稅(ctit)對第一產業比重的沖擊可以看出,“營改增”改革并不影響對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占比的變動。

圖1 “營改增”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沖擊(蒙特卡洛模擬500次)
綜合脈沖響應圖結果我們可以看出,“營改增”改革對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對第二產業比重的增加具有負向促進作用,流轉稅改革優化了產業結構。另外,面對營業稅(btit)變量的沖擊,第二產業的反應程度,也就是縱軸表示的時間刻度,大于第三產業的反應程度。面對增值稅(vtit)變量的沖擊,第三產業的反應程度更大。另外通過對比可以看出,面對流轉稅(ctit)變量的沖擊,第三產業的反應程度更大,這也從側面說明“營改增”改革對第三產業的影響程度大于第二產業。
3.方差分解
為了更好地驗證前述回歸與脈沖響應函數的結果,本文繼續使用方差分解從多層次考察產業結構、營業稅、增值稅、流轉稅等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方差分解分析是其自身擾動項共同作用的結果,通過分析內生變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 通常用方差來度量) 的貢獻度,考察PVAR模型中擾動項對預測均方差的貢獻度,進而評價不同內生變量沖擊的重要性。表5為“營改增”改革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方差分解結果。

表5 三次產業方差分解結果
注:運用stata12軟件計算得到
通過分析表5可以看出,在第1期,給定一個標準信息差增值稅變量的沖擊,第一產業比重沒有變動,對第二產業變動的貢獻程度為8.90%,對第三產業變動的貢獻程度為15.40%。而給定一個標準信息差的營業稅變量的沖擊,同樣對第一產業占比的變動沒有影響,對第二產業變動的貢獻程度為3.34%,對第三產業變動的貢獻程度為6.27%。隨著時間的推移,基于“營改增”視角的流轉稅改革對第一產業占比變動的影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對第二產業變動貢獻率一直維持在11%左右,對第三產業占比的影響在第一期以后貢獻程度略有升高,第十期以后基本穩定在17%左右。
(四)控制變量組實證結果
現實經濟復雜多變,除了“營改增”改革之外,還有其它諸多因素對產業結構變遷產生影響。圖4和圖5為其它控制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圖。
綜合控制變量組的實證分析結果來看,經濟開放度(owit)與人均國民收入水平(pgit)降低了第一產業占比。企業所得稅(etit)與個人所得稅(ptit)兩個變量提高了第二產業占比,人口密度(pdit)變量對第三產業占比提高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政府規模(sgit)對第三產業占比的變動具有負向的促進作用,固定資產投資(fiit)與政府規模(sgit)兩個變量都對第二產業占比提高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經濟發展程度(pgit)提高了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利用外資水平(fdiit)、城鎮化率(urit)、經濟開發度(owit)等變量提高了第二產業占比。這主要是由于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更多的人口進入到城市中居住生活,造成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出現下降,第二與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增加,進而帶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外,隨著人均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城鎮居民的增加,伴隨著社會進步,對高質量服務的需求也在增加,促進經濟結構服務化。

圖2 其它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沖擊(蒙特卡洛模擬500次)

圖3 其它變量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沖擊(蒙特卡洛模擬500次)
(五)穩健性檢驗
依據PVAR模型的原理可知,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不區分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而是將所有的變量都等同為內生變量。所以本部分產業結構、營業稅、增值稅、流轉稅等變量均作為PVAR模型的內生變量,為防止前述GMM估計系數,脈沖響應圖以及方差分解等實證檢驗結果受變量次序的影響,避免模型估計系數出現偏誤,本文在改變各變量的順序后,重新考察了公式(16)-(18)的GMM估計、脈沖響應以及方差分解的實證檢驗,發現主要計量檢驗結果與前述實證分析基本吻合。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模型正確反映了“營改增”改革與產業結構變遷之間的邏輯關系,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將實證結果一一列出。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討論了流轉稅改革與產業結構變遷的內在邏輯關系。首先,數理模擬“營改增”改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影響,提出有待檢驗的假說;其次,基于1998-2014年省級面板數據,采用面板向量自回歸(PVAR)模型,實證檢驗“營改增”改革政策沖擊影響產業結構變動的正負效果,并運用方差分解定量測度“營改增”改革對產業結構變動的貢獻程度。
(一)主要結論
綜合PVAR模型的GMM估計結果和脈沖響應函數的計量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以“營改增”為主線索的流轉稅改革降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提高了第三產業的比重,優化了產業結構。但是“營改增”改革對第一產業占比基本沒有影響,這主要是由于流轉稅的課稅對象主要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對第一產業稅負基本不產生影響。另外,營業稅變量對第二產業的政策沖擊作用更大,而增值稅變量對第三產業的政策沖擊作用更大,綜合來看流轉稅改革對第三產業的影響程度大于第二產業。通過對方差分解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一,“營改增”改革對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變動的貢獻程度非常小,這也從多個層面上說明流轉稅改革對第一產業占比變動基本沒有解釋力。其二,“營改增”改革對第三產業占比變動的貢獻率大于第二產業,隨著時間的推移,流轉稅改革對國民經濟中第二產業占比變動的貢獻率維持在10%左右,對國民經濟中第三產業占比變動的貢獻程度維持在16%左右。
(二)政策建議
數理模擬和計量檢驗結果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內生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反作用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雖然流轉稅改革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程度有限,但稅制改革制度成本最小。為了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本文參照實證檢驗結果中不同變量對國民經濟三次產業變動的沖擊傳導機制,提出以下幾個方面政策建議:
1.破除政府補貼的企業規模與所有制壁壘
產業結構優化是經濟轉型、產業調整的重心,同時產業結構的優化又離不開政策的引導與扶持。長期以來,政府的財政補貼大部分都是投入到國有企業,中小企業投入的比重偏低,而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的中小企業是產業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在以后的政策調整中,發展潛力大、創新能力強的中小企業應該成為政府補貼的重點。
2.做好“營改增”善后工作,切實減輕企業稅負
以“營改增”為契機,繼續推行減稅措施,采取一定的獎懲方式控制資本的投向結構,引導社會資源更多地配置到第三產業。同時降低宏觀稅負水平,使其處于合理范圍之內。宏觀稅負水平直接影響到生產要素的回報率,過高的宏觀稅負也扭曲了產品相對價格,加重企業的綜合負擔,不利于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減緩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因此宏觀稅負水平的降低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重要舉措。
3.完善官員考核機制,更多關注整體社會福利
在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機制中,弱化財政收入、GDP增長的重要性,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機制,逐步將生態環境、民眾滿意度、公共產品的供給、社會整體福利的改善列入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機制中。改變過去依靠政府財政投入發展經濟的增長模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注重通過政府財稅政策引導作用來激勵生產性服務業。督促地方政府建立適合服務業發展的財稅制度環境,切實做到通過發展第三產業來提高政府公共服務供給。
4.穩步發展循環經濟,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政府可以針對產業結構升級演進的規律,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增加研發投入的財政補貼,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鼓勵使用財政激勵政策,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高新技術領域,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及相關產業的增長,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演進。
5.實行區域性產業結構升級戰略
不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受到區域內其它經濟發展以及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諸如環境、國民素質、產業成本等。在“營改增”徹底推行到全行業以后,財稅政策的出臺不能一刀切,應該有針對性地出臺一些促進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優化的配套性財稅政策,調節不同區域之間的財政補貼力度,重點扶持服務業發展,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產業結構向服務化轉型創造條件。
6.發揮城鎮化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通過對控制變量組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城鎮化進程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城鎮化過程中,充分發揮稅收的收入和支出調節效應,合理調整稅收支出政策優惠取向,加大稅收支出力度,優化稅收支出方式,積極引導我國產業結構的演進升級。
[1]Kongsamut P, Rebelo S, Xie D.Beyond balanced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1, 68(4): 869-882.
[2]Buera F J, Kaboski J.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2540-2569.
[3]Ngai L R, Pissarides C A.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 429-443.
[4]Acemoglu D, Guerrieri V.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116(3): 467-498.
[6]Rajan R G, Zingales L.What do we know about capital structure? So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50(5): 1421-1460.
[7]Rogerson R.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8, 116(2): 235-259.
[8]Esteban-Pretel J, Sawada Y.On the role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postwar Japan[J].2009, Discussion Papers, 9001.
[9]Alvarez-Cuadrado F, Poschke M.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1, 3(3): 127-158.
[10]Herrendorf B, Rogerson R, Valentinyi A.Two perspectives on preference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7): 2752-2789.
[11]Lin J Y, Sun X, Jiang Y.Endow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3, 16(2): 109-122.
[12]Vandermerwe S, Rada J.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6(4): 314-324.
[13]Robinson T, Clarke-Hill C M, Clarkson R.Differentiation through service: A perspective from the commodity chemicals sector[J].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2, 22(3): 149-166.
[14]White A L, Stoughton M, Feng L.Servicizing: The quiet transition to 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J].Tellus Institute, Boston, 1999, 97.
[15]Roos I, L?fgren M, Edvardsson B.Customer-support service from a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best practice for telecom[J].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3, 5(2): 5.
[16]Ramey G, Ramey V A.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volatility and growth[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4.
[17]Ali A M.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 of fiscal volat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JBER), 2011, 3(5).
[18]Afonso A, Furceri D.Government size, composition,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26(4): 517-532.
[19]Bleaney M, Halland H.The resource curse and fiscal policy volatility[J].CREDIT Research Paper, 2009, 9.
[20]Lichtenberg F R.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funding on private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 re-assessment[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87: 97-104.
[21]Lucas.On the mechanizes of economy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1,( 5) : 3-42.
[22]魏福成,鄒 薇,馬文濤,劉 勇.稅收、價格操控與產業升級的障礙——兼論中國式財政分權的代價[J].經濟學(季刊),2013(7):1491-1512.
[23]王文舉,向其鳳.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及其節能減排潛力評估[J].中國工業經濟,2014(1):44-56.
[24]汪德華,張再金,白重恩.政府規模、法治水平與服務業發展[J].經濟研究,2011( 5) : 4-16.
[25]郭 曄,賴章福.政策調控下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J].中國工業經濟,2011( 4) : 74-83.
[26]王 勛,Johansson A.金融抑制與經濟結構轉型[J].經濟研究,2013 (1):54-67.
[27]張 婕,張媛媛,莫 揚.對外貿易對中國產業結構向服務化演進的影響——基于制造服務國際分工形態的視角[J].財經研究,2013(6):16-27.
[28]安 苑,王 珺.財政行為波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了嗎?——基于產業技術復雜度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2(9):19-35.
[29]劉 悅,鄭玉航,廖高可.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6(8):149-158.
[30]李 鋼,廖建輝,向奕霓.中國產業升級的方向與路徑——中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例過高了嗎[J].中國工業經濟,2011(10):16-26.
[31]曹廣忠,袁 飛,陶 然.土地財政、產業結構演變與稅收超常規增長——中國“稅收增長之謎”的一個分析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07(12):13-21.
[32]國 亮,王一笑.土地財政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基于產業間稅種差異和土地財政的視角[J].江西社會科學,2015(8):33-40.
[33]李勇剛,王 猛.土地財政與產業結構服務化——一個解釋產業結構服務化“中國悖論”的新視角[J].財經研究,2015(9):29-41.
[34]張同斌,高鐵梅.財稅政策激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J].經濟研究,2013(5):58-70.
[35]王 宇,劉志彪.補貼方式與均衡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與傳統產業調整[J].中國工業經濟,2013(8):57-69.
[36]陳國慶,王 舟,張春宇.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創新補貼的績效研究[J].經濟研究,2014(7):44-55.
[37]柳光強,田文寵.完善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設想——從區域稅收優惠到產業優惠[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3):1-5.
[38]張培森,付廣軍.我國經濟稅源的產業與行業稅負結構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5):5-14.
[39]郭小東,劉長生,簡玉峰.政府支出規模、要素積累與產業結構效應[J].南方經濟,2009(3):51-61.
[40]石 奇,孔群喜.動態效率、生產性公共支出與結構效應[J].經濟研究,2012(1):92-104.
[41]褚 敏,靳 濤.為什么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步履遲緩——基于地方政府行為與國有企業壟斷雙重影響的探究[J].財貿經濟,2013(3):112-122.
[42]宋凌云,王賢彬.政府補貼與產業結構變動[J].中國工業經濟,2013(4):94-106.
[43]Baumol W 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44]Love I, Zicchino L.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J].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6, 46(2): 190-210.
(本文責編:王延芳)
Did the Reform of Turnover Tax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SUN Zheng
(SchoolofEconomics,Tianji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ianjin300200,China)
Tax reform is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effect of turnover tax reform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reform of “business reform” on industrial structure.(PVAR) model to test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 that turnover tax reform, which is the main clue of “business change and increase”, reduc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improv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t the same time, by the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quantitative measure “camp to increas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degree,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business tax variables greater degre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impact of the face of VAT variable tertiary industry responsemore.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olicy enlighten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s put forward.
turnover tax ;camp to add; PVAR model; industry optimization
2016-07-01
2016-11-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16XDJ017),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TJYY16-002Q)。
孫正(1985-),男,山東五蓮人,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財稅政策、稅收經濟學。
F812
A
1002-9753(2016)12-00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