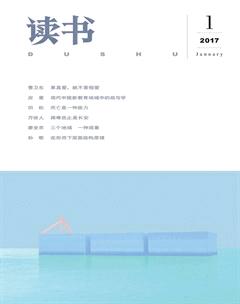不一樣的“戰壕真實”:巴布琴科的戰爭小說
阿爾卡季·巴布琴科(一九七七— )是第一位以車臣戰爭為創作素材的俄羅斯作家,他以充滿人文情懷的筆法,將自己親歷的戰壕生活展現給讀者,其創作風格讓人一下子就聯想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壕真實派”。在蘇聯時期的戰爭文學領域,繼老一輩作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西蒙諾夫之后,出現了“戰壕真實派”。該派作家大多是在前線打過仗的年輕軍官,他們結合自己在戰場上的所見所聞,創作出一批堪稱經典的戰爭文學作品,包括邦達列夫的《最后的炮轟》、巴克蘭諾夫的《一寸土》、貝科夫的《第三顆信號彈》等。“戰壕真實派”的創作出發點有別于此前的蘇聯戰爭文學,沒有將戰爭的勝利全部歸功于最高統帥的英明指揮,而是將鏡頭對準了在前線浴血奮戰的普通官兵,突出了蘇聯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無可替代的貢獻。相對于此,車臣戰爭作為一場現代局部戰爭,缺少那種全民皆兵、同仇敵愾的高昂情緒,戰爭似乎與普通百姓無關,而參戰士兵也將前線作戰理解為一項職業任務,很少表現出英雄主義氣概或愛國主義熱情。因此,巴布琴科的車臣戰爭小說雖然同樣力求表現“戰壕真實”,但他筆下呈現出來的戰爭已是另一種樣子。
巴布琴科創作的初衷首先在于揭示車臣戰爭的真相,對“戰壕真實”的再現達到了新聞報道那樣的準確程度。在談到文學創作時,他宣稱自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戰壕真實”,要將“親眼看到的那種戰爭呈現出來,不會是那種被宣傳加工過的樣子”(二○○八年四月七日接受BBC采訪)。評論家普斯特瓦婭曾撰文,專門談到了巴布琴科小說的這種真實感:“巴布琴科被戰爭的真實壓得喘不過氣來。像一面鏡子的碎片,穿行在戰場上,并將戰場映射出來。”(《新世界》二○○五年第五期)為了強調這種“戰壕真實”的價值意義,巴布琴科曾與老一輩作家馬卡寧(一九三七— )展開論戰。馬卡寧從一九六五年就開始文學創作,數十年來筆耕不輟,代表作品有《鋪著呢子,中間放著長頸瓶的桌子》(一九九三年獲俄語布克文學獎)、《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一九九八)等。一九九九年,馬卡寧推出了以車臣戰爭為背景的中篇小說《高加索俘虜》。在馬卡寧看來,即便是對于戰場上經受生死考驗的人,美仍然是一種拯救力量,它可以讓人保持自己的本性。巴布琴科則認為這種論調純屬無稽之談,為此他不無針對地指出:“沒有打過仗的人不能講述戰爭,這不是說他笨或遲鈍,而是因為他沒有能用來理解戰爭的感官。這和男人不能懷孕、生孩子是一個道理。”(《戰爭藝術》二○○六年第一期)二○○八年,馬卡寧以車臣戰爭為題材,創作出長篇小說《阿桑》,并獲得了當年的文學巨著獎。《阿桑》中的主人公建筑工程師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齊林,曾在車臣地區從事軍火庫和燃料倉庫的建筑工作,在車臣戰爭之后成為俄軍敬仰的汽油大王、車臣人敬畏的“阿桑”。就馬卡寧的這部新作,巴布琴科在《新報》上做了毫不客氣的批評,認為馬卡寧對戰爭的描寫純屬杜撰,根本沒有真實性可言,稱這部小說是“借車臣題材對戰爭的胡編亂造”(《新報》,二○○八年十二月八日)。在巴布琴科的小說中,饑寒交迫、驚恐不安才是士兵每天面對的生存狀態,危機四伏的環境要求戰士們時刻保持高度警惕,而美的東西背后往往暗藏著危險:“是很好,好看。但那兒會有車獨分子藏身。那兒會有一場戰斗,死神就在那兒。狗東西,潛伏在那兒,躲在太陽底下。等待,在等著我們。等我們懈怠了,就會跳出來。”(《阿爾罕-尤爾特》)
巴布琴科在小說中體現的“戰壕真實”,擺脫了正義戰勝邪惡、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等宏大敘事的誘惑,“活命”被視作戰場上的最高法則。戰爭怎樣讓一個人變成一名戰士,這才是他要表現和思考的主題。從生命價值的角度,巴布琴科將戰場上的“活命”與社會生活中的“生存”等量齊觀,戰區類似于現實生活中的另一個街區,在戰區里生活著一種從事特殊職業的群體。二○○五年在接受《新報》采訪時,巴布琴科說過:“有兩個俄羅斯,正在打仗的俄羅斯和另一個俄羅斯,它們存在于平行的兩個世界。”在小說《阿爾罕-尤爾特》(《新世界》二○○二年第二期)中,通過主人公阿爾喬姆,巴布琴科講出了戰區“居民”最關心的事—“在極端情況下,所有機體活動都指向一個目標,那就是活命。”在生死瞬間,阿爾喬姆處于極度驚恐之中,他最為關心的只有一個問題—“活命”:“重要的是活下來。什么都不要想。至于將來會怎樣,只有上帝知道。”阿爾喬姆將打仗等同于職業行為,殺人不過是這種職業要求完成的任務而已:“對車獨分子,他沒有絲毫同情或良心不安。我們是敵人。應該殺死他們,就該這樣。采取一切手段。辦起來速度越快、手法越簡單越好。”我們還記得,在當年的“戰壕真實派”作品中,頌揚英雄主義,捍衛正義與真理,是巴克蘭諾夫等一代作家始終堅持的創作宗旨。無論是在《最后的炮轟》,還是在《一寸土》中,盡管戰士們英勇戰斗的畫面充滿了血腥,但經常讓老兵們陷入噩夢的那些殘酷經歷讓他們成為更高意義上的人,成為捍衛和平與真理的高尚之人。在《一寸土》中,巴克蘭諾夫借中尉莫托維洛夫之口,道出了蘇聯官兵為贏得戰爭勝利而忘我戰斗的意義:“我們打仗,是為了消滅所有的卑鄙行徑,是為了戰后能過上充滿人性、誠實而正當的生活。”不難看出,在“戰壕真實派”的作品中,消滅敵人而讓自己活下來并不是最終目的,這顯然與巴布琴科的“戰壕真實”所體現的“活命”原則不能同日而語。
在巴布琴科的戰爭小說中,作者從全新的角度開啟了當代人對生命的意義、對戰爭的另一種理解。參與戰爭的人遵循著冷酷而僵硬的“活命”原則,由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名戰士,完成這種蛻變的代價是人性的喪失,這與戰士對和平生活的渴望產生了難以克服的沖突。在現代化戰爭條件下,傳統意義上的那種交戰雙方或陣地已不復存在,交戰經常發生在人們仍在正常生活的街區或巷道,執行作戰任務的戰士穿行在和平生活的空間之中。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對和平生活的渴望就變得格外強烈。此外,現實中車臣戰爭引起的社會關注度不高,新聞媒體對戰事沒有連篇累牘的報道,退伍后的戰士也感受不到社會的關心,體驗不到參戰本應帶來的自豪感,由此產生的落差讓參戰者更看重普通人所過的安寧生活。巴布琴科在描寫令人膽戰心寒、噩夢縈繞的戰斗場景之際,始終未忘展示主人公內心對正常生活的向往與渴望。戰爭殘酷之“冷”與向往和平生活之“熱”交織在一起,在這種沖突中,主人公一方面要捍衛“職業”操守,去完成作為戰士所肩負的任務,另一方面還要像普通人那樣,時刻想著保全自己的性命。為此,巴布琴科所要表現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和敵人的沖突,而是主人公內心的沖突。小說中塑造的主人公不關心為什么而戰,為誰而戰,戰爭對他們來說更像是必須完成的工作。在巴布琴科的作品中,普通人經受戰爭的考驗,成為一名戰士,這并不意味著他在人格上的升華,也不能證明他在價值觀或人生觀方面變得更崇高。相反,人之蛻變為戰士,往往意味著心靈活動的結束:“這片戰場他不會忘記,他是在這兒死去的,他身體里的人跟在納茲蘭時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一個戰士誕生了。一個好戰士—空虛、沒有思想,帶著冰冷、仇恨的心看待整個世界。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阿爾罕-尤爾特》)
在巴布琴科的小說中,按“活命”原則,將個人的生存放在首位。阿爾喬姆是小說《阿爾罕-尤爾特》中的主人公,在一次執行任務時,由于他的誤判,導致一名車臣老人及其八歲的孫女遭到槍擊,女孩當場死亡。這件事讓阿爾喬姆追悔莫及,幾近瘋狂,差點兒吞槍自盡。為了證明“活命”的合理性,他反過來想,被槍擊的目標如果真是車臣匪徒呢,那樣的話,命運就換過來了,死的就不是對方,而是自己了。最后,阿爾喬姆認識到,開槍是必需的,由此也完成了由普通人到一名戰士的蛻變。在這個蛻變過程中,將個人放在首位的“活命”原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與以往的戰爭文學大相徑庭。人們在談論“戰壕真實派”的起源時,常常追溯到維克多·涅克拉索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七)的中篇小說《在斯大林格勒的戰壕里》(一九四六)。小說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克爾任采夫中尉在前線的所見所聞及其成長過程。在反擊德軍的戰斗中,人之成為戰士,意味著這個人經受住了考驗,其人性得到了升華,進而變成英雄。對于涅克拉索夫來說,戰爭是驗證和提升人格境界的手段。對于巴布琴科而言,戰爭中的人也是普通人,而戰區不過是另一種生存區域而已,爭取活下來才是天經地義的頭等大事,這成為其作品中缺少英雄人物形象的原因之一。
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將主人公“平民化”是巴布琴科戰爭小說的一大亮點,這有別于以往帶有“英雄化”“妖魔化”傾向的做法。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壕真實派”文學中,對人物形象的描寫大多表現出主人公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存在著英雄化的傾向。在八九十年代關于阿富汗戰爭的作品中,不僅見不到對英雄主義的頌揚,而且表現出另一種極端,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存在著“妖魔化”傾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奧列格·葉爾馬科夫(一九六一— )曾在蘇聯駐阿富汗的炮兵部隊服役。一九八九年,葉爾馬科夫開始根據親身經歷,創作出系列小說《阿富汗故事》。在葉爾馬科夫的代表作《野獸的標記》(原文發表于一九九三年,由劉憲平、王加興完成的中文譯本已于二○一五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主人公切列帕哈是蘇軍的一名校炮手,小說重點講述的不是他在戰場上的表現,而是其所在的軍營生活。借助“妖魔化”手法,切列帕哈被塑造成一個與“野獸”無異的軍人形象,他不僅欺負新兵,吸食大麻,還恫嚇平民,槍殺俘虜。而在閱讀巴布琴科的《山地步兵旅》(中文譯本見《世界文學》二○一○年第三期,胡學星譯)等小說時,我們能從主人公平淡無奇的言談舉止中,深切感受到他們對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珍惜,這都要歸功于作者將主人公“平民化”的處理方法。
在巴布琴科的小說中,軍人沒有被塑造成“高大上”或“高大全”的形象,不過,他們還是會讓自己適應殘酷的戰場生活,以盡職盡責的敬業態度,去履行軍人的天職。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戰士們在險象環生的戰爭環境中,每時每刻都在尋找機會體驗和平生活,有時候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山地步兵旅》講述了俄羅斯士兵與車獨分子作戰的種種經歷,同時還不吝筆墨,描寫了戰士們在戰斗間隙或休整期間的“閑情逸致”—到河里洗澡,收養小狗,救護瀕死奶牛等故事。有一次,戰斗剛告一段落,兩名戰士去車獨分子把守的樓內偵察,發現“一個很像樣的爐子”,便想帶回去取暖用,這時候被對方的狙擊手發現:“我們朝己方的樓房飛奔,像高鼻羚羊那樣,兩跳就跨過了五十米的距離,但還是沒扔下爐子。我倆剛跑進樓門,就開始像瘋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個小時,停不下來。”為了弄到取暖用的爐子,兩名戰士差點兒丟掉自己的性命。這是正常人所難以理解的,因為人們不了解戰士們所過的那種非人生活:“一個星期沒洗的雙手布滿裂紋,經常出血,因為寒冷而變成了密密麻麻的濕疹。我們不再洗臉,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們已經一星期沒烤過火了—濕漉漉的蘆葦點不著,而在草原上又沒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們開始變得像野獸一樣。寒冷、潮濕和泥濘把我們身上所有的感覺都剝蝕掉了,只剩下仇恨,我們仇視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們自己。”正是為了避免變成“野獸”,需要用爐子來取暖,讓自己保持正常人的狀態,兩名戰士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將爐子帶回去。
在巴布琴科講述的車臣戰爭中,類似的故事并不少見。短篇小說《一套住房》講的是俄軍士兵入住攻占區無人留守的民宅時發生的故事。主人公發現一處住宅的房門上掛著鑰匙,室內陳設簡樸但很溫馨:“在一號小區,在一座黃色的五層高的樓里,我發現了這套住房。房門上包飾著便宜的人造革,門鎖上插著一串鑰匙,主人沒打算把門鎖上:在這里住吧,別破門而入就行。房子并不豪華,但很齊全。很有生活氣息,看來主人剛剛離開,就在突襲之前。不像是在戰爭時期,這里很溫馨、安靜。簡陋的家具、書籍、陳舊的壁紙、毛織無絨頭的雙面地毯。所有東西都收拾得規規矩矩,沒有遭到洗劫。甚至連玻璃都沒被打碎。”房子的主人非但沒有將家中的物品帶走,還把鑰匙也留了下來,這讓見慣了人去樓空的主人公產生好感,喚起了他對和平生活的渴望。于是,他將這一處住宅“藏匿”起來,經常到此待一會兒,將房主想象成自己的妻子,與之一起享受片刻的安寧生活:“這里是一個小世界,是我極其渴望的安寧生活的一片小天地,我渴望從前沒有戰爭時的那種安寧生活,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守著心愛的妻子,晚飯時邊吃邊談,暢想著未來。”在故事的結尾,主人公再次來到那處由于他的努力而保持完好的住宅:“我們要繼續向前開拔時,我最后一次去那兒看了一眼,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后仔細地把門鎖上。我把鑰匙留在了鎖上。”
從這類故事中,我們看不到戰士們追求建功立業的英雄主義,也看不到那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當然也無從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作者對戰士的污蔑或貶損。換言之,巴布琴科的小說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既不熱衷于“英雄化”,也不喜歡“妖魔化”。巴布琴科描寫的戰士活躍在戰場之上,輾轉于生死之間,但仍渴望能像和平環境中的人們那樣過正常生活,做個正常人。可見,“平民化”才是巴布琴科塑造軍人形象的手段,這讓他筆下的戰士更真實,更接地氣。
在巴布琴科嘗試戰爭文學創作之時,蘇聯解體后一度受追捧的后現代主義已風光不再,現實主義傳統開始回歸。在這種文學背景下,巴布琴科追求“戰壕真實”的小說一經問世,便被評論家貼上了“新現實主義”的標簽,并得到涅姆佐爾、斯拉夫尼科娃等文壇大腕的一致力捧。近年來,巴布琴科受聘為《新報》等媒體的戰地記者,多次到南奧塞梯、烏克蘭前線采訪,這無疑會為他今后的戰爭文學創作提供幫助,我們期待著他更多更優秀的作品問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張載
正統的中國近代史書寫一般是從一八四○年開始,但這種書寫帶有濃厚的“沖擊—反應”模式的痕跡。如果從“中國中心觀”來看,在長時段的意義上,中國近代發生的“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實早從明到清前期就已埋下變因;而在短時段的意義上,中國社會巨變的來臨又比一八四○年要晚得多。孔飛力的經典研究表明,傳統中國的衰落是自太平軍起義被撲滅的一八六四年才開始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敵人及其叛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如果說一八六四年構成了中國近代巨變的第一個歷史界點,那么,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敗和一九○五年的廢除科舉就構成這場巨變的第二個和第三個歷史界點。這些界點的確定與構成中國社會結構重心的士紳階層的演化息息相關。一八九五年前,科場是帝制后期的社會支配關系賴以不斷再生產出來的一個重要場域,支撐著科場場域的是所謂的“士紳慣習”。但自一八九五年后,“士紳慣習”開始不斷遭到嚴重的沖擊,并由此影響到了原本以科場為中心的教育場域。這個影響過程又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九五到一九○五年,在此期間,新舊兩種文化資本在科場場域展開競爭,由此導致了士紳慣習的衰變,并最終造成了科場場域的終結。其標志性事件是一九○二年《壬寅學制》、一九○四年《癸卯學制》的先后頒布和一九○五年科舉制度的停廢。第二個時期是從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在此期間,科舉被廢、書院改制、學堂遍立,新文化資本占據了教育場域的主陣地。其標志性的事件是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壬子癸丑學制》的頒布。新式學堂雖然在統治集團內部實現了權力的重組,但并沒有為原來的被統治階級帶來更多的上升機會,反而使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的交換日漸公開化,從而使這種支配關系的遮掩機制被破壞殆盡。如果說科場場域實現的是統治者及其統治集團內的被統治者之間的內部整合,那么,新式學堂崛起導致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分化與瓦解,而傳統的“士紳慣習”則突變為新式學生的“反體制沖動”。這種反體制沖動雖然瓦解了科場場域的存在基礎,卻只是一種特殊的、不穩定的、去合法化的慣習,因而,取代科場場域的并非一個相對獨立于政治場域的學校場域,而是一個與權力、政治、革命密切糾纏在一起的“后科場場域”。“反”字當頭的慣習不足以建立起新的道統,終究也難免被政統所裹挾;而缺乏道統支撐的政統在近代中國不斷上演著的就是“有槍就是草頭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戲劇。
可以說,從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雖然展開了教育制度的巨變,但并沒有隨之完成教育理念的真正更新。所謂“新教育理念”之“新”究竟在什么地方?學界一種觀點認為新教育是從精英主義、道德化的傳統教育走向了實用化、科技化、大眾化的現代化教育。另一種觀點認為新教育場域作為連接國家與社會的場所,既是新式學生通向現代世界和民族—國家的橋梁,也是國家對鄉土社會進行滲透整合的通道。這兩種觀點顯然是現代化理論以及國家—社會理論在中國現代教育史研究中的移植,并沒有從中國教育思想發展的內在脈絡來貼切地理解中國教育的現代轉型。
如果從中國傳統教育本身的內涵來說,其基本精神是德行教育;而如果從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謂“場域”(field)的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教育場域的基本特點是“學而優則仕”“內圣外王”。讀書人通過“修身”“齊家”,希望最后能夠通向的是“治國”“平天下”,因此,傳統教育的重心放在為統治者提供優秀人才上。士階層不僅以文化主體自居,更發展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識,造成了學與政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密不可分。因此,當嚴復一八九八年提出治學與治事不能相兼,“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當梁啟超一九○二年道出“天地間獨立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實際上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所謂“新教育”的實質在于政與學的關系重構。不過,這些在當時甚為微弱的呼聲為革命的浪潮所淹沒,更何況這兩位過渡時代最著名的代言人自己也沒能真正做到治學的獨立。
真正為新教育場域的興起揭開大幕的是蔡元培,他一九一七年開始對北京大學的整頓。在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以“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之地也”為宗旨,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為手段,努力使北大廣泛接納學有專長的人才、全面打造學術研究的體制、深入塑造學術所謂“科學的精神特質”,從而使一個獨立于政治的“學術社會”逐漸得以孕育、催生和成熟。蔡元培對北大的整頓為學術與政治的關系開啟了一種嶄新的可能性。如果借用牟宗三的術語,那就是說,蔡元培試圖在政統與道統之間增添一個新的東西:“學統”(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五年版)。所謂“政統”是指政治權力系統,所謂“道統”是指道德人心世界,所謂“學統”是指科學話語世界。蔡元培試圖通過北大的整頓實踐,在教育場域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學術社會”—這個“學統”以西方的經驗科學為基礎,以“為學問而學問”為旨趣,以“兼容并包”為手段,一方面以相對獨立自主的精神構筑起與政統的張力,另一方面又在美育的輔佐下統攝對道統的重塑。也就是說,蔡元培希望通過“政統—道統—學統”的三角平衡關系的建立,使新教育場域得以真正成型。如果從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史的角度來看,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時期也正是從《壬子癸丑學制》過渡到《壬戌學制》(一九二二)的時期。
盡管蔡元培的努力為中國現代教育與學術的成長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但他所冀望的“政統—道統—學統”的平衡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還是一種相當脆弱的平衡,他所追求的“教育超秩于政治”只是一個理想形態。在他治下的北大雖然一直采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但到后期已經出現了一些難以兼容的裂變。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北大在這次運動中一馬當先,一代新青年由此嶄露頭角。但五四運動對蔡元培所追求的學術獨立也隱微帶來了某種挑戰。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被免;隨后陳獨秀就因為在五四運動中被捕而自動脫離了北大。陳獨秀從北大離職固然有眾多因素,但追求政治的激進顯然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另一方面,一九一九年被蔡元培破格請進北大執教的梁漱溟對北大只重知識而不重人倫和實踐的西式教育漸生不滿,先后幾度請辭而被蔡元培挽留,直到一九二四年最終離開北大,去山東菏澤接辦省立第六中學,謀求將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結合在一起的新教育實踐。陳獨秀和梁漱溟從北大的離職,標志著“兼容并包”并不能完全解決新教育場域塑造中學術與政治之間、學術與倫理之間的張力。
政與學的張力在面臨學生運動時尤顯突出。蔡元培對學生運動并非一概采取反對態度。在他看來,學生“干預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不過當此一發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智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民眾,那么,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44頁)。對蔡元培來說,學生卷入政治,只能是在“一發千鈞”這樣的非常態情況下。但是,自清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中國始終處在戰爭狀態,“一發千鈞”的非常態變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常態。因此,新教育場域的塑造走向,不僅取決于學校里的校長和師生的行動,更取決于政治場域的局勢變化。正所謂“這一代的政治培養出這一代的學運,這一代的學運反映出這一代的政治”(楊人
:《從這一代的學運看這一代的政治》)。從“五四”到北伐,整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學生運動的政治化色彩日益濃厚,從五四運動的注重外交問題轉而注重內政問題,從學生運動獨立成潮到與政治反對運動合流,從學生運動到由政黨主導的“運動學生”(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四年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為了革命既相互爭奪學生運動的主導方向,又在某些情形下共同助力于學生運動的激進化。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高等學府里的學與政已經呈現出此消彼長、相互推拉的局面,那么,在某些普通中學和師范學校,學生與政治、學生與革命的關系就變得更加密切。科舉廢除后的新教育體制既喪失了科舉體制原有的社會凝聚和整合機制,又喪失了科舉體制所特有的消解政治參與壓力的功能;新式學生群體數量龐大、出路堵塞,加上“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慣性,因而形成比帝政時代遠為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二○一○年版)。盡管蔡元培提出“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但要真正做到讀書與救國兩不誤,既需要學統的堅固,也需要學生個人的涵養。面對風雨如磐的時局,那些從草根社會走入神圣學府的中學生尤其是中等師范生,他們是充滿激情、“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中小知識分子,覺得自己對苦難、不公和黑暗的世界有著深切的體會,身負著教化社會、重整河山的重任;而他們的學養又不足以安頓人身、涵養人性與撫慰人心,“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峻急心態常常使他們選擇了通過革命去成就道德人生的道路。而二十年代既是中國教育制度史上從《壬戌學制》(一九二二)演化為《戊辰學制》(一九二八)的時期,也是政治史上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的時代。中國共產黨雖然對二十年代早期的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相當激進的政治組織,但它在初創時仍須找到合法性授予的制度基礎。民國時期的新式學校尤其是中等學校就成為中共早期領導人在各地建立組織網絡的一個主要依托。一些由國民黨員控制的中等學校營造出結社自由和追求進步的濃烈氛圍,為中共組織的早期發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而普通中學與師范學校的不同類型又促生了中共早期不同的組織結構。
《新教育場域的興起,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六》一書研究的是三個個案: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三年的湖南士紳的裂變;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江西中等學校與中共組織網絡的關系。該書研究的時段也正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五個學制方案(《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壬戌學制》和《戊辰學制》)相繼出臺的時期。盡管該書并非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史或教育思想史的專門研究,但將這三個研究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從一八九五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教育場域在中國的興起及其所伴生的學與政的關系變遷。
當然,所謂“新教育場域”的概念雖然有其整體的意涵,但也因教育層級、地域和世代等諸因素的影響而存在具體內涵的差異,需要分別略加討論。
首先,不同教育層級的差別。政學的張力在不同層次的學校表現出來的強度有著明顯的不同。對大學來說,這種張力的強度最大。一方面,大學作為擔負著學術創造使命的教育場域,作為高級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其問道為學常常形成較強的傳統;另一方面,大學生的社會使命意識比中學生更強,對政治的敏感度也更高,介入政治的資源更廣,從事政治的能力也更強。因此,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學數量還很少的情況下,一所大學里往往既有較強的學術風氣,也可能同時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度。而中學和師范學校則因為各自面臨的校園環境的差異,容易在向學與革命上形成一邊倒的趨勢。比如,同樣是二十年代江西省最著名的中學,南昌一中與南昌二中就有著顯著的差異:前者有著更濃厚的學術風氣,而后者則因為與國民黨人士的淵源成為江西早期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地學校之一。又如,在省立中學與師范學校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省立中學常常是通向大學的臺階,因此對學生的學業有著更嚴格的要求;而師范學校則因為生源多來自貧寒之家的優秀學子,畢業出路大多是回鄉當小學教師,他們既對個人能力有優越感,又易生不平感,因此更易走上改造舊社會的革命道路。
其次,不同地域的差別。就中國晚近士紳群體的分布來說,有三大區域的士紳是最為重要的:湖湘、江浙和嶺南(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湖湘知識群體是晚清儒學地域化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晚清地方軍事化的重要助力。湖南既是晚清紳權擴張最為強盛的地方之一,又是產生諸多影響中國近現代史進程的政治、軍事人物之重鎮。在傳統科舉考試中,湖南遠非稱得上文風鼎盛之區。但在從科場場域到后科場場域的嬗變中,湖南民風中的蠻勇與新學堂環境中醞釀出的反體制沖動結合在一起,使其近代涌現的政治軍事人物在全國高居榜首。這也使我們對湖南清末民初教育場域的個案研究在全國頗具典型性。而在對五四運動學生代的研究中,則需要考慮到另一種典型性。美國學者葉文心在研究杭州的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根源時曾指出,以往對五四運動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北京,但新文化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其實從“五四”開始就存在諸多分支流派。五四運動在杭州,代表了與北京的運動所不同的另一種訊息,即不是來自通都大邑對外開放的口岸的求變,而是來自中國內地鄉土社會的求變(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和傳播大體分為三個層次:上海和北京位居全國的中心,廣東、湖南、湖北、山東等位居區域的中心,江西等位居革命思想傳播和組織發展較為遲緩的第三類地區。以往對早期中共組織的研究多集中在前兩類地區。而對江西這樣的第三類地區的關注,可以使我們較好地把握五四運動學生代在投身共產主義運動時從中心擴散到邊緣的發展脈絡。
再次,不同世代的差別。所謂“世代”(generation)更多是從社會結構的意義上說的,而不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代。也就是說,“世代”指的是一個特定社會結構中因個體占據了相似位置而構型成的具體的社會群體,故此,某代人的社會構型可以遷延上百年不變,而另一代人則可能整代處于被遮蔽狀態,其中的關節便在于社會的變遷程度(《卡爾·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二○○二年版)。一八九五年前后活躍著的是傳統社會最后的兩代士紳:此時已進入士紳上層隊伍的一代;以及一八九五年仍處在士紳下層地位的一代。從一九○五到一九一一年,第一代新式學生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這代人被通稱為“辛亥革命一代”。緊隨“辛亥革命一代”的是“五四運動一代”。嚴格來說,五四運動一代又可分為師生兩代,其中五四老師一代與辛亥革命一代在相當程度上是交叉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后是五四運動學生代投入政治的短暫高峰時期,隨即學生運動即陷入了消沉的時期。其后新學生與政治及革命的關系已經揭開所謂“后五四時期”的新篇章了。
如果用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來衡量的話,二十年代新教育場域的政學關系似乎是清末民初“后科場場域”的重返:學生與政治、政黨與革命又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的確,在辛亥一代學生與五四一代學生之間,在國民黨老同志與共產黨新青年之間,不僅存在著在“反體制沖動”這樣的精神氣質上的傳承,而且在革命的道路與組織的壯大上也存在著相互的照應。
但是,五四新青年在二十年代投身于共產主義運動的洪流中,與辛亥一代學生投身反清革命仍有重要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革命理想與組織形態上,而且也表現在場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對辛亥一代學生來說,其所置身的教育場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場域的邊界非常模糊,他們與科場時代的士紳慣習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是許多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也充滿了疏離感和迷惘感,他們懷疑自己改變現實的能力,對個人前途也并沒有十足的信心。而對五四一代學生來說,其所置身的學府開始具有了新生的場域特征,他們徹底遠離了士紳慣習,無論是勇敢地投身革命,還是安靜地問學,他們對未來的世界和個人的前路都顯得比上一代自信、從容,他們在反對所謂“科舉教育、奴隸教育、貴族教育、老大教育、部章教育、機械教育”上已經取得了高度的共識。盡管在這個場域里,仍然存在著“愛國不忘讀書”與“讀書不忘愛國”之間的張力,但“為學問而學問”與“為救世而學問”已經成為并置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二十年代的學府盡管充滿了各種分岔,但我們仍可以說這是一個新教育場域初步成型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