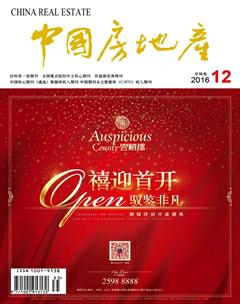折疊起來的北京
呂慧明
22世紀的北京,建立在一個轉軸上,分為三個空間。第一空間居住著500萬人口,非富即貴,掌握著最好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甚至支配著時間的轉換,每天生活24小時,之后折疊,進入24小時的休眠;第二空間居住2500萬人口,大多是白領,想方設法擠進第一空間,他們生活16小時,休眠8小時。當他們睡下后,城市折疊,第三空間出現;第三空間居住著5000萬人,大部分是清潔工和個體戶,他們生活在貧窮、擁擠、骯臟的空間里,生活8小時,休眠16小時。
這是小說《北京折疊》里描繪的關于未來城市的想象。
“貧民窟”是城市的傷口
縱觀世界城市的發展,“貧民窟”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普遍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或者正在面臨“貧民窟”問題的困擾。貧民窟之所以存在,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里可能的經濟機會驅動農村貧困人口轉移到了城市。而面對龐大的人群,城市的管理體系又無法接納如此眾多的人口,因此,貧民窟得以形成和擴大。
正如美國學者邁克·戴維斯在《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中提到的:“未來的城市,不像早期都市學者們所想象的那樣,由玻璃和鋼鐵構成,而是更多地由粗糙的磚頭、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塊和廢木頭構成。不是炫目多彩直達天堂的城市,而是蜷伏在泥濘之中,被污染、糞便和腐爛包圍。”
站在邁克·戴維斯的角度來看,《北京折疊》是對未來城市發展的一種預言,小說中描寫的未來城市的貧困問題展示了城市發展過程中并不光彩的一面,貧民窟成為一道傷口,時刻提醒我們關于美好城市的想象多么容易破碎。
城市是“磁體”還是“容器”
從第三空間到第二空間再到第一空間,一個城市被割裂成三個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階層的固化。并且按照小說的描寫,這樣固化方式,永遠都可能打破。很顯然,這并不是城市發展的初衷,也不是眾多學者心目中理想城市的樣子。
著名城市規劃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中,對城市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經典的論述。
在有關城市形成過程的論述中,芒福德強調的是城市的精神本質(磁體)而非物質形式(容器);而在有關城市發展過程的論述中,芒福德強調的是城市的貯存功能(容器)而非融合功能(磁體)。這是一個基于不同標準的雙重隱喻。一方面,從“磁體”的功能而言,城市的活力源于吸附越來越多的人口、資本、資源、信息等,這是城市必然突破數量和空間的限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從“容器”的功能而言,一旦城市吸附的東西超過了城市可以承載的底線和極限,導致城市“容器”功能損傷,最終城市會走向解體。
所以,未來的北京用折疊的方式,避免了城市的崩潰。然而,隱藏在城市發展中的矛盾和困境,并沒有解決。
我們的美好城市
目前,相對鄉村而言,城市正在取得勝利。但是,城市自身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大城市的過度膨脹,人口的高密度集中,社會資源的高密度集中,這些都城市遭遇的史無前例的危機。
如何應付危機,是城市建設者以及決策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讓我們再次回到芒福德觀點。從古希臘、羅馬的城市到現代的超級大都市,他始終關注的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時代精神。這是一個城市得以延續的關鍵。
每一個時代的精神,都在這個時代,以人間戲劇的形式,在每一個城市里不斷上演。在羅馬時代,芒福德批評了窮奢極欲的貴族對整個城市的綁架;在中世紀,他關注了在混亂的社會里人們百家爭鳴、欣欣向榮的社區環境;在巴洛克時代,他批判了王公貴族對權力和暴力的炫耀,對奢華生活的追求,以及凌駕于眾生之上的優越感;在超大城市時代,他表達了對金錢和強權對每一個市民的強力控制的不滿。
芒福德想要的理想城市是,通過科學的城市規劃,結束攤大餅建設城市的非科學方法,城市能夠形成分功能、分區塊的有機體,城市的各個部分能夠相映成趣。而在這個設計下,城市的管理機構能夠更多的關心每一個市民的精神思想,讓轄區內的市民能夠恢復古老、自由、溫情的鄰里關系。而透過城市這一平臺,自由的風氣能夠得到鼓勵,從而達到“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輝”這一目的。
說到底,美好的城市的最終理想是對人的關懷。《北京折疊》并沒有指出一個未來的理想城市的樣子。就連郝景芳本人在接受采訪時坦言:“不希望未來的城市是小說中的樣子。”今天我們站在城市建設的角度看待這部小說,它的意義在于為我們指出,無節制的城市發展的最終結果。最終,引導我們思考,我們究竟該如何建設我們理想中的美好城市。
就像科特金所說的:“最終一個偉大的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對他們的城市所產生的特殊的深深眷戀,一份讓這個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獨特情感。最終必須通過一種共同享有的認同意識將全體居民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