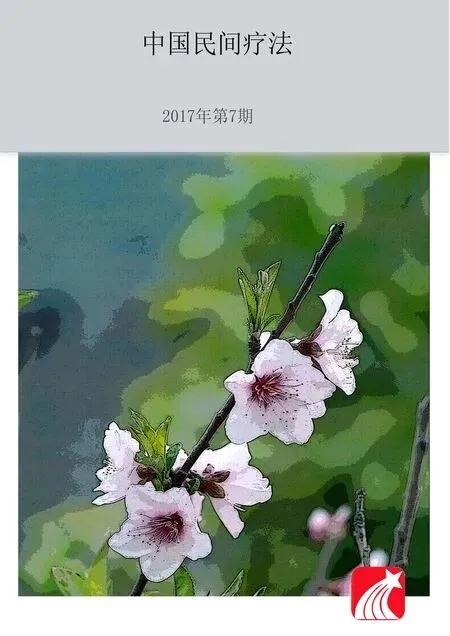仲景偶方為君治療腎臟病探析
韓履祺
(山西省中醫院,山西 太原 030012)
仲景偶方為君治療腎臟病探析
韓履祺
(山西省中醫院,山西 太原 030012)
偶方;傷寒雜病論;腎臟病
東漢時期,著名醫學家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對中醫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所創立的方劑,被后人稱為“醫方之祖”。張仲景的很多方劑,歷經千百年實踐考驗,在臨床中廣泛運用,行之有效。其中偶方即“藥味合于雙數,或由兩味藥組成的方”[1],雖然構成簡單,但立法遣方以病機、病證為依據,主治功能明確,凸顯仲景方劑精華。運用仲景偶方為君,在腎臟病治療中可化頑疾,起沉疴。
桂枝甘草湯
本方原治發汗過多,損傷心陽之心下悸。方中桂枝辛甘性溫,入心溫陽;炙甘草甘溫,益氣和中,二藥合用辛甘化陽,扶陽補中,是溫補心陽之主方。對平素心陽不振,動則心悸,且易于反復感冒的慢性腎臟病,常以桂枝甘草湯合玉屏風散扶陽補中,益氣固表,有助于腎病的緩解和穩定。又如慢性腎衰合并心臟病變,出現心悸氣短、乏力干咳之氣陰兩虛證,則以桂枝甘草湯合生脈散,溫心陽,益氣陰,使陰陽兩復。
桂枝甘草湯為仲景治療心陽虛之急重證候而設,故藥味少,用藥量大,且服法為“頓服”。清代名醫王子接在《絳雪園古方選注》中指出,桂枝甘草湯從“桂枝湯中采取二味成方,便另有精蘊,勿以平淡而忽之。桂枝復甘草是辛從甘化,為陽中有陰,故治胸中陽氣欲失。且桂枝輕揚走表,佐以甘草留戀中宮,載還陽氣”。對慢性腎病僅出現心陽不振之心悸,而無“叉手自冒心,欲得按”,也可用本方加味治療,可酌減原方劑量,不以頓服,同樣有效。本方是從桂枝湯化裁,又可從其配伍角度理解、探求仲景用含桂枝甘草方劑所治病證特點及用藥規律。
甘草麻黃湯
本方原治表寒兼皮水。方中以甘草和中補脾,麻黃宣肺、發汗、利水,可從表解風邪水氣,又可利小便去水。對于肺脾氣虛之水腫,常以甘草麻黃湯合五皮飲,有宣肺健脾、增強利水之功。
水腫是腎臟病常見病證,仲景提出“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一般而言,水腫伴有表證,或發病時間短,腰以上腫者,多從肺論治,宜宣肺發汗。所用方劑多含有麻黃,《本草綱目》曰:“麻黃乃肺經專藥,故治肺病多用之。”《藥征》曰:“麻黃主治喘咳,水氣也。”臨床上辨為風水證,選用甘草麻黃湯治療較多。甘草麻黃湯證病機單純,此方更適宜與他方聯用,依據偏重風熱或風寒,隨癥加味,不僅水腫減輕,也可減輕蛋白尿。
甘草干姜湯
本方原治虛寒肺痿。由于中焦陽虛,肺中寒冷,陽不化氣,在上則吐涎頭眩,在下則遺尿,小便數。方中炙甘草益氣溫中,干姜回陽祛寒,二藥合用辛甘化陽,可溫中復陽,溫散肺寒。對于老年尿頻夜尿多,或小兒遺尿、流涎,辨證為陽氣虛寒,水氣失制,輕者可單投本方,重者則合五苓散化氣行水,或合縮泉丸溫腎固澀。
仲景以甘草干姜湯既治肺痿虛寒證,又治陽虛之手足逆冷,二者雖證候不同,但病機相同,均為脾陽虛所致。因此脾陽虛之水腫,中焦虛寒的胃痛、腹瀉等,均可用本方加味治療取效。甘草干姜湯被后世稱為“溫中祖方”,是治療陽虛里寒證的基礎方,理中湯、四逆湯等方均以此方為基礎加味。此外,本方炙甘草用量倍于干姜,且有干姜炮與不炮的區別應用,都值得細細品味。
小半夏湯(半夏干姜散、橘皮湯、大黃甘草湯)
本方原治飲停于胃,上逆作嘔。方中以半夏降逆化飲,生姜溫中止嘔,共成和胃止嘔、散飲降逆之劑。對慢性腎病素體脾虛,痰濁中阻之惡心嘔吐,不能進食,常先以此方降逆、止嘔、化痰,待嘔吐減輕,再合六君子湯益氣健脾和胃。
如中陽不足,寒飲嘔逆,仲景以半夏干姜散溫中止嘔,即以干姜易生姜,干姜溫陽,“守而不走”。對腎臟病中出現胃寒嘔吐,腹脹腹瀉,常以半夏干姜散合理中丸溫中止嘔,祛寒健脾。
如寒邪中阻,胃失和降而出現干嘔、呃逆及手足厥冷者,仲景治以橘皮湯。方中橘皮理氣和胃,生姜降逆散寒,二藥合用溫散寒邪,理氣通陽。腎臟病中痰濕內阻也是常見證型,表現為胸悶脘脹,納呆身困,大便黏滯,或有咳痰,常以橘皮湯合三子養親湯加味理氣通陽,化痰除濕。
大黃甘草湯,原治胃腸實熱,食已即吐。方中大黃蕩滌腸胃,瀉濁降逆,甘草緩急,使攻下瀉火不傷正,二藥合用,通腑瀉實,則胃氣和降。如尿毒癥中出現腸胃實熱,腑氣不行,逆而上沖之嘔吐,常先以此方攻下,急治其吐,再合溫膽湯清熱和胃。
小半夏湯被冠以“治嘔祖方”,專以和胃止嘔。由本方衍生的方劑有半夏干姜散,以干姜易生姜,且以“頓服”集中藥力,溫中和胃止嘔;橘皮湯理氣通陽,和胃止嘔;大黃甘草湯泄熱降逆,和胃止嘔。在臨證中,以嘔吐為主癥,惡心嘔吐,不能進食者,可依證選用各止嘔之方,如小半夏湯和大黃甘草湯,在一些腎臟疾病出現急重嘔吐時常會用到。仲景云:“諸嘔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如嘔吐,口不渴,頭眩心悸,可用小半夏加茯苓湯。對嘔吐兼有他癥,要根據辨證治本的原則,或健脾化痰,或溫中止嘔,或清膽和胃等。
桔梗湯
本方原治熱邪客于咽喉而咽痛。方中甘草生用清熱解毒,桔梗辛開散結。咽痛是導致腎病復發或加重的重要因素。對邪熱壅滯上焦,肺氣不宣之咽部紅腫疼痛,以桔梗湯合銀翹馬勃散(金銀花、連翹、馬勃、半夏、射干)清熱解毒,瀉肺利咽;對邪熱日久傷陰,咽痛遷延,以桔梗湯合增液湯(生地黃、元參、麥冬)清熱利咽,滋陰潤燥。此方對咽痛有較好療效,亦可使腎病盡快緩解。
桔梗湯被稱為治療咽痛的祖方,后世很多治療咽喉痛的方中,都可以看到桔梗湯。咽痛是腎病治療的重要環節,咽痛較輕者,單用本方即可;咽痛較重者,常需加用清熱解毒藥物。咽痛遷延發為慢性咽炎,當清熱解毒,滋腎潤肺,如時振聲先生的經驗方銀蒲玄麥甘桔湯[2]。
蒲灰散
本方原治膀胱有熱之小便不利。方中蒲黃涼血消瘀、通利小便,滑石清熱利濕,合用具有化瘀利竅、清利濕熱之功。對下焦濕熱,熱傷血絡之血淋或泌尿系統感染反復發作,或以濕熱瘀阻為主者,均可用蒲灰散合五淋散(赤芍、當歸、甘草、赤苓、梔子)化瘀涼血、利尿通淋。
淋證亦為腎臟系統常見病,易反復發作。初病主要是濕熱蘊結下焦,膀胱氣化不利;發病日久,則可由實證轉為虛證,或虛實夾雜證。仲景偶方在治療淋證中各有所長,血淋以尿血而痛為特征,尚有虛實之分,蒲灰散以涼血行瘀為主,治濕瘀互結之血淋,合五淋散則療效更顯著。
百合地黃湯、百合知母湯
百合病主因心肺陰虛內熱而致百脈失和,出現多種證候。仲景治百合病,多取百合為主藥。其中百合地黃湯滋陰清心,百合知母湯清熱養陰安神。氣陰兩虛、陰虛內熱是很多腎臟病的常見證型,在糖尿病腎病早中期尤為突出。如氣陰兩虛偏心肺,表現為乏力倦怠,煩熱失眠,心慌汗出,常以百合地黃湯合生脈散,氣虛明顯則合四君子湯;如氣陰兩虛偏于腎,表現為腰膝酸軟,乏力口干,失眠,便干,則以百合知母湯合大補元煎(熟地黃、山萸肉、山藥、人參、枸杞子、當歸、杜仲)加減。仲景百合湯方證既反映了疾病在不同階段癥狀各異,又體現了辨證的精準,“各隨證治之”的靈活性。陰虛內熱是慢性腎病的常見證型,不僅心肺陰虛,更有腎陰虧虛、氣陰兩虛等證。此時治療,一法一方已不能勝任,當數方合用,多方并進。百合地黃湯與百合知母湯以養陰清熱,除煩安神為長,又各有偏重。因此,臨證還要細辨心、肺、腎陰虛孰輕孰重,區分氣虛、陰虛何者為主,以及不同的表現,依證選方。
討論
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從整體觀念出發,創造性地把理法方藥融為一體,在《傷寒雜病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方劑是中醫辨證論治的集中體現,偶方則是仲景方劑精華的濃縮,也體現了仲景辨證用藥的特色與規律。正如黃煌教授在研究仲景藥證用藥規律后指出“最簡方原則:配伍最簡單的處方,其指征可視為該藥藥證”[3],對我們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在臨床中,對一些病機單純的病證,只要方劑與病證相應,選用仲景偶方治療均可取效。但腎臟病的病因病機復雜,病情證候多樣,故臨證中常選仲景偶方為君,配選他方合和,把偶方看作合方的君藥,即針對主病或主癥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其為方劑組成的核心,藥味雖少,但藥效強力。同時又能使一方兼幾法,一方多用。在仲景書中多處都看到他用一方可治多病、治一病可用數方的記載,體現了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靈活性。
運用仲景偶方為君藥治療腎臟病,充分顯示偶方“四兩撥千斤”之力,偶方合和可治大病。桂枝湯調和營衛,調和陰陽,不僅解表,還能和里,臨床應用較廣,被譽為群方之冠。桂枝甘草湯由桂枝湯化裁而來,以溫補心陽見長,在慢性腎病表現為素體心陽不振,或氣陰兩虛之心悸怔忡、乏力氣短者,均可用本方加味取效。麻黃湯主治太陽傷寒證,麻黃為辛溫散寒的要藥。仲景治傷寒,無汗則用麻黃,有汗則用桂枝。甘草和中補脾,麻黃解表散寒,宣肺利水,對腎病出現外感風寒表實證水腫明顯者,常選甘草麻黃湯為底方,《金匱方歌括》概括其功效為“二藥上宣肺氣,中助土氣,外行水氣”。甘草干姜湯為脾陽虛而設,以溫補脾陽為主,重用炙甘草,炮干姜辛溫散寒為輔,合成辛甘溫陽之劑,為治脾陽虛諸癥之溫中祖方。治嘔祖方小半夏湯,為治腎病中出現脾胃氣虛,痰濁中阻之嘔吐的基礎方,如胃寒嘔吐者則以干姜易生姜,溫胃止嘔,此外胃熱及飲食積滯者,都可用本方加味論治。對尿毒癥濁毒上逆之嘔吐可以用本方或大黃甘草湯加味治療。還有治咽痛祖方桔梗湯及百合湯等,在腎病中常會出現與上述方劑相同的病機、病證,都可靈活選用這些偶方。從這些偶方中均能感受到仲景“用藥法度謹嚴,變化靈活,嚴而不死,活而不亂,是有規律可循的”[4]。只要把握病機,選用仲景偶方為君藥,合和他方,不僅可使腎臟病中的疑難病如慢性腎炎、腎病綜合征、糖尿病腎病、腎盂腎炎、慢性腎衰竭等病情緩解,漸趨穩定,而且也能使慢性腎病中出現的一些急重癥盡快減輕癥狀。運用仲景偶方為君藥治療腎臟病不但提高了腎臟病的療效,同時加深了對仲景方證和用藥配伍規律的認識。
[1]《中醫詞典》編輯委員會.簡明中醫詞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799.
[2]肖相如.肖相如論傷寒[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331.
[3]黃煌.張仲景50味藥證[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11.
[4]陳瑞春.陳瑞春論傷寒[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125.
2016-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