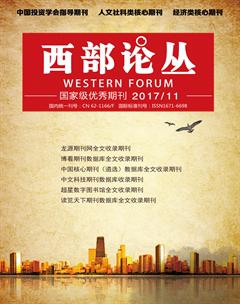淺析我國水資源的刑事立法保護
李小梅
摘 要:我國現行刑法雖然規定了污染環境罪以及其他涉及水資源的相關犯罪,但尚無真正意義上的針對破壞水資源犯罪的刑事規制,使得水資源得不到更好的保護。因此,應結合我國水資源犯罪的實際情況,針對我國水資源犯罪存在的立法缺陷,進一步強化我國水資源犯罪的刑事立法保護。
關鍵詞:水資源 刑法保護 污染環境罪
一、我國水資源刑法保護的現狀
縱觀我國刑法典,涉及水資源的犯罪主要有3個,分別是:決水罪、過失決水罪、污染環境罪。但這三個罪名都存在缺陷。決水罪與過失決水罪兩者在立法意圖上不是憲法上所提及的“為了保護和完善生活環境、生態環境”,它的意圖是保護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財產。只有公民在故意或者過失決水,導致公共安全受到損害的時候刑法才會追究公民的刑事責任。污染環境罪,則是以列舉方式對污染水資源的行為進行規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水資源,但其真正目的是為了保護人類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并不是為了專門保護水資源的安全。這也正說明了我國當前奉行的是“人本主義”的環境刑法理念。
按照我國《環境保護法》對環境的定義,環境犯罪可以分為污染環境犯罪、破壞自然資源犯罪。但在我國刑法規定中,針對污染水資源非沒有單獨設立罪名,也沒有對破壞水資源犯罪進行規定。綜上所述,我國刑法雖然規定了污染水資源的犯罪,但刑法介入的范圍非常窄。刑法對水資源犯罪的規定是從危害公共安全的角度來進行立法,并沒有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進行立法。因此,當前我國刑法關于水資源犯罪規定需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現行水資源刑事立法保護的缺陷
(一)水資源犯罪規定過于嚴格
1、以故意為犯罪主觀構成要件
污染環境罪主觀方面的要件是故意,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嚴重水污染的后果,而對這種后果采取一種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并沒有對過失造成水污染該如何定罪進行規定。而在實際生活中,行為人實施水污染行為時并不全是故意的,在過失的情況下也會造成水污染。而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對過失造成水污染該如何定罪找不到法條依據。而根據刑法理論,過失犯罪只有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負刑事責任。可見,如果過失造成水污染,則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事實上行為人在實施水污染行為時,過失和故意對水資源造成的危害是一樣的。這就使得過失行為無法進行刑法規制,水資源犯罪得不到應有的處罰。
2、以客觀危害結果的存在作為既遂標準
污染環境罪規定以犯罪結果作為犯罪既遂標準。造成水污染的實質性損害后才達到既遂,這就使得刑法介入水污染犯罪的時間推后,刑法難以在第一時間遏制水污染犯罪危害結果的發生,發揮刑法的最嚴厲制裁作用。在自然界中,生態系統是一個整體,水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水具有流動性的特點。水被污染以后,被污染的水就會影響整個生態系統,使污染水源進入到其他的水域、土地之中,以及揮其他相關領域,從而對整個生態系統造成影響,使整個生態系統面臨嚴重威脅。而水污染后需要治理,其治理成本又非常高,影響經濟發展。因此,必須使刑法提前介入到水污染犯罪前。以客觀危害結果的存在作為犯罪既遂的標準,推后了刑法介入時間,不利于水資源的保護。
(二)刑罰設置不合理
《刑法》第338條規定,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由于我國在環境污染犯罪上采用的是混合型罪名,因此,污染環境罪的法定刑同樣也適用于水污染犯罪。罪刑責相適應是我國刑法基本原則,三者的有機統一,是正確定罪與適當量刑的根本方針。水污染犯罪具有嚴重的生態和社會危害性,應當受到嚴格的刑罰制裁。但是,我國刑法在污染水資源犯罪的罪刑責存在不合理之處,使得水污染犯罪行為難以受到應有的制裁,刑法制裁水污染犯罪的作用沒有有效的發揮。
(三)罪名體系有缺陷
污染環境罪規定過于籠統污染環境罪籠統性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未對水資源、大氣、土壤等環境因子做區分規定。一般認為,我國現行刑法第338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其污染對象包括水資源、大氣、土壤等環境因子。就污染水資源犯罪而言,以混合立法的方式防治水污染,會給司法實踐帶來定罪上的困難,既可能定污染環境罪,又可能定投放危險物質罪,還有可能定危險物品肇事罪。我國刑法只對污染水資源的行為進行了規定,而對破壞水資源的行為都是作為普通犯罪進行調整,專門規定處空白狀態,導致了非法取水、嚴重浪費水資源、非法占用水面、破壞性開采水資源等普通違法行為被排除在刑法之外。
三、我國水資源刑事立法保護的完善
(一)單獨設立水污染罪
鑒于水環境重大污染事故的后果嚴重性可以考慮將其從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中分離出來,確立水污染罪,用刑罰手段保護水資源的清潔使水污染行為承受犯罪的后果。水環境污染罪的主體包括個人和單位,主觀方面是故意。客觀方面包括污染行為與造成的危險狀態,對擅自排放污物、污染水體的行為,超標排污、隱瞞、謊報污染物排放濃度及數量的行為,向禁污水域排污的行為,按照私自停止使用水污染物處理設施的排放總量與接受行政處罰規定相結合確定一個合適的標準注重刑法的預防功能懲治危險犯甚至舉動犯,進而強化執法力度。
(二)增加環境抽象危險犯
相比德國有關規定,我國對水資源的保護還具有不徹底性,沒有充分貫徹生態法益獨立性的理念。因此,依舊有必要繼續擴大處罰污染環境的范圍,吸取德國規定污染環境罪中對環境危險犯的經驗。繼續增加對環境的危險犯的立法。即:應當將行為人未經許可排放、傾倒、處置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并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足以污染水域、空氣、土壤,或對其做不利改變,或危害動植物、生存的納入犯罪打擊范疇。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在立法上貫徹“生態法益”的理念,不致于把“生態法益”空洞化。
(三)增設非法取水罪
非法取水罪是指行為人實施了未經許可取水或雖經許可但沒有按照規定取水造成或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其犯罪構成為:犯罪主體包括一切單位和個人。犯罪客體是國家對水資源的管理制度、正常的用水秩序和水資源的國家所有機犯罪客觀方面是指行為人未經許可取水或雖經許可但沒有按照規定取水且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嚴重后果包括:國有水資源大量流失、地面塌陷或沉降、造成生態破壞、地下涵水層被挖穿地下水流失等。在認定犯罪林必須達到后果嚴重的程度。行為人的行為與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四)完善刑罰設置
第一,加大水污染犯罪的處罰。對于污染水資源造成極大危害的,在判定自由刑方面應增加相應的力度,即對自由刑的時間有所增加。對于污染水資源造成嚴重污染并進而影響到了公眾的正常生產生活的,可以對其判處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對于排放污染物危害水資源造成公私財產或人員受到重大損失的行為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對于造成公眾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財產特別重大損失危害的,對其判處的自由刑的年限可以達到十年以上,這樣更能體現我國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第二,加大罰金處罰力度。我國在對于罰金制度的制定時要更為明確一些具體的罰金金額,這樣法官在執行的過程中才能不打折扣的執行,我國的法律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由于倍比罰金制的實行需要以明確的銷售金額、違法所得額等為基準,其本身就模糊不定,增加了操作的難度,而破壞水資源的犯罪,其危害主要在于對水資源本身所帶來的短期和長期損害,以物質利益計算的違法所得等難以衡量水資源自理的損失。日額罰金制的數額需要根據犯罪人的實際經濟狀況確定,并要求犯罪人在判決生效后每日向法院繳納罰金,這對于金融等配套制度尚不完善而又地域遼闊的中國來說,實施起來實非易事,為此我國更適宜采用較為合理的限額罰金制度,這樣的制度可能會更加符合我國國情。就像是美國或者日本在水資源犯罪中的刑罰規定,我國也可以在規定罰金時明確數額的上限與下限,這樣既能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又可以防止出現無限額罰金可能造成貪腐的空子。而在具體的實踐中,罰金的上下限的具體額度,可以參照相關行政法規如《環保法》等對于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金額來制定,然后根據犯罪者的情節等再設定不同的金額幅度。
水資源的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應當遵循以憲法為指導,行政法、經濟法為基礎,刑法為保障的原則。刑罰規定不夠科學,尚未與環境民事、行政法甚至其他相這顯然與國家號召的實施“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合。以刑法立法視角研究水資源的保護應當具有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2] 瑪軍等:《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3] 張明楷:《刑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