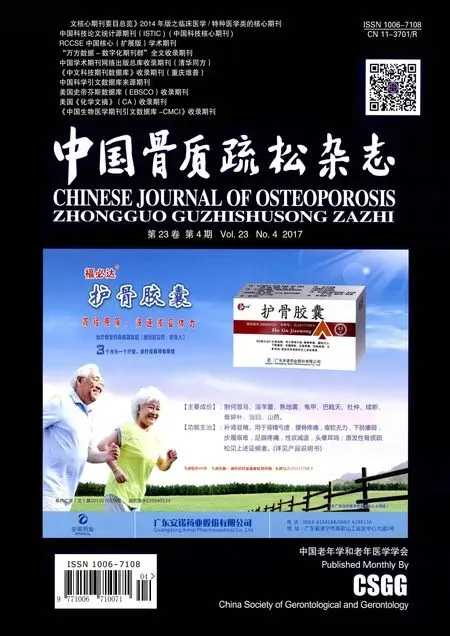骨轉換標志物在糖尿病中的研究進展
尚芬蘭 徐晶晶 赫榮波 葛曉琴 戴靜 楊濤 何畏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科,江蘇 南京 210029
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糖尿病和骨質疏松癥的患病率迅速增加。糖尿病性骨質疏松癥(diabetic osteoporosis,DOP)是指糖尿病并發單位體積內骨量減少,骨組織微結構改變,骨強度降低、脆性增加等易發生骨折的一種全身性、代謝性骨病,是糖尿病在骨骼系統的重要并發癥之一。糖尿病患者骨質量下降,骨折風險增加,雙能X線骨密度僅提供骨量的變化,不能完全反映骨質量,而骨轉換標志物具有靈敏性高、特異性強、無創、易重復等優點,較骨密度更早的反映骨量的變化,還反映骨強度。聯合監測骨轉換標志物和骨密度,為DOP的診斷和治療提供了新思路。
1 糖尿病和骨質疏松癥的流行病學
糖尿病是最常見的內分泌代謝紊亂性疾病,全球大約有3.27億人患有此類疾病[1]。隨著人口的老齡化,糖尿病并發骨質疏松癥的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流行病學調查顯示,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患者的骨密度是減低的[2-3],其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癥的發病率為48%~72%[4]。對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患者,骨密度增高、降低或不變的結果國內外文獻均有報道[5~8]。近年來研究發現,T2DM患者代謝性骨病和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明顯高于普通人群,其骨質疏松癥的發生率可達20%~60%[7]。
2 骨轉換標志物
骨轉換標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BTMs)[9],是骨組織本身的代謝(分解與合成)產物,在骨骼重建過程中釋放于血液、尿液中,是能夠被檢測出來的一些活性物質。它分為骨形成標志物和骨吸收標志物,前者代表成骨細胞活動及骨形成時的代謝產物,后者代表破骨細胞活動及骨吸收時的代謝產物,特別是骨基質降解產物。BTMs的測定具有創傷小、靈敏度和特異性高,判斷骨轉換類型,反映骨丟失速率,部分反映骨質量、骨強度,早期診斷骨質疏松癥,監測骨質疏松藥物療效,評估骨折風險等優點。
2.1 常見骨形成標志物
2.1.1血清堿性磷酸酶(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骨堿性磷酸酶(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BALP):ALP通過水解磷脂釋放無機磷,使局部磷濃度增加,促進骨礦化,有利于骨形成,是目前很常用的評價骨形成的指標。但它在全身多個組織均有分布,對骨組織的靈敏度和特異性差,BALP具有較高的骨組織特異性,臨床上多檢測BALP。絕經后婦女的BALP隨年齡增加呈負相關,與骨密度呈正相關,證明與骨代謝相關[10]。BALP為骨化活動指標,已在骨代謝性疾病中廣泛使用[11]。
2.1.21型前膠原氨基末端前肽(procollagen 1 N-terminal peptide,P1NP)和 1型前膠原羧基末端前肽(procollagen 1 C-terminal peptide,P1CP):90%以上的骨基質是由Ⅰ型膠原組成,Ⅰ型前膠原分子由成骨細胞合成,其羧基末端和氨基末端有延伸的多肽,這些多肽在膠原細胞代謝過程中被蛋白酶分解,產生P1NP和P1CP,因此P1NP和P1CP反映了Ⅰ型膠原的合成和轉化,二者水平升高提示Ⅰ型膠原合成加快,骨形成活躍。比起P1CP,P1NP受晝夜節律和飲食的影響較小[12-13],且不受激素的影響,是反映骨形成更為特異和靈敏的指標。Zhang等的實驗表明,骨質疏松組病人P1NP值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14]。
2.1.3骨鈣素(osteocalcin,OC):骨鈣素由成骨細胞分泌,在骨組織含量豐富,大部分沉積于骨基質。在骨吸收及骨溶解時,沉積在骨基質中的OC就會游離出來,釋放入血。測定血中OC,一方面能反映成骨細胞的活性,但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骨轉換。當骨轉換升高,血中OC水平升高,反之則下降。骨鈣素的主要功能是維持骨正常礦化速率,抑制異常的羥基磷灰石晶體的形成,抑制生長軟骨礦化的速率,增加破骨細胞的募集和(或)分化,從而刺激骨的吸收[15],是成骨細胞功能和骨質礦化的特殊標志物。
2.1.4骨保護素(osteoprotegerin, OPG):OPG和細胞核因子kB受體活化因子(RANK)是腫瘤壞死因子受體家族新成員,由成骨細胞產生。OPG是一種可溶性糖蛋白,能特異性地抑制破骨細胞形成與分化,增加骨密度。RANK存在于破骨細胞和前破骨細胞表面,RANKL是其唯一配體。OPG/RANK/RANKL系統在骨形成和骨重塑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6]。RANK與RANKL相互結合誘使破骨細胞分化,而OPG通過與RANKL競爭性結合,阻止其與RANK的結合,從而抑制破骨細胞的形成及分化,抑制骨吸收[17-18]。研究表明[19],外周循環中OPG和RANKL水平與BMD成負相關,并且促進絕經后婦女骨質疏松的發生。
2.2 常見骨吸收標志物
2.2.1吡啶啉(pyridinoline,PYD)和脫氧吡啶啉(deoxypyridinoline,DPD):PYD和DPD存在于I型膠原纖維中,是成熟的I型膠原纖維分子構成膠原纖維時分子間的連物,起穩定膠原鏈的作用。當破骨細胞活動時PYD和DPD作為I型膠原纖維降解產物釋放入血,不經中間代謝直接從尿中排出,且不受飲食影響,是反映骨吸收的一個特異指標[20]。已有不少研究[21]表明,尿DPD/Cr測定對骨流失及骨質疏松癥的診斷早于骨密度檢測,是反映骨吸收的特異而敏感的指標。
2.2.21型膠原蛋白C末端交聯肽(type 1 collagen protein C-terminal crosslinking peptide,CTX)和1型膠原蛋白N末端交聯肽(type 1 collagen protein N-terminal crosslinking peptide,NTX):CTX和NTX是破骨細胞在骨吸收過程中降解產生的特異性產物,能直觀的反映骨吸收情況。NTX和CTX在血清中和尿液中均可檢出,在血清中的水平受晝夜生理節律、飲食的影響較大,而24h尿中NTX、CTX可以克服生理節律的影響, 受飲食的影響也比較小[22]。Bouzid K等[23]認為,女性骨質疏松患者絕經后,測定CTX比ALP、BALP有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性。
2.2.3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TRACP):TRACP主要由破骨細胞釋放,參與骨基質中鈣磷礦化底物的降解。TRACP被蛋白酶分解成5a和5b兩個亞型,純化的人破骨細胞TRACP是TRACP5b。最近在對TRACP5b和骨微結構參數研究發現,骨組織損傷(特別是骨小梁)破壞會導致血清TRACP5b濃度升高,血漿中的TRACP水平可反映破骨細胞活性及骨吸收的狀態[24]。血清TRACP5b已大量應用于絕經后婦女抗骨吸收監測及作為乳腺癌患者骨轉移的診斷工具[25]。對骨代謝異常的患者監測發現,2年骨密度下降2.5% 相對的皮質區下降5.8%,與TRACP5b水平呈正相關,結果表明,TRACP5b可用于骨代謝異常的早期監測[26]。
2.3 T1DM與BTMs
T1DM的骨密度降低,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增加,可能與骨吸收增強,骨形成減少有關[27]。一項橫斷面研究認為,T1DM的ALP、BALP與非糖尿病組比較沒有差異,但OC水平下降[28-29]。一項包括22篇文章的薈萃分析顯示[30],與健康對照組相比,T1DM的25羥維生素D3、OC和CTX水平明顯降低。但甲狀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鈣、P1CP、BALP和DPD在統計學上沒有顯著差異。另有研究表明,T1DM患者的OC(28.4±16.4 VS 41.2±14.6ng/mL,P=0.005)和BALP(51.3±118 VS 61.7±10.6U/L,P=0.006)水平較健康對照組明顯降低[31]。
對于T1DM患者,尤其是青年起病的糖尿病患者,青年時期獲得的峰值骨量明顯低于正常同齡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腎病等慢性并發癥出現早,降低了骨微循環的營養物質供應及對維生素D的轉化能力,導致隨年齡增長的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增加;同時,T1DM由于促骨形成的重要合成類激素-胰島素及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的嚴重缺乏,使骨形成明顯減少;T1DM患者骨及骨髓中內源性的抗氧化物質如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Px)、過氧化物歧化酶應激的SVCT2表達下調,T1DM小鼠骨密度明顯下降[32]。此外,T1DM的自身免疫及炎癥狀態也可以引起骨量丟失以及礦化缺陷[33]。
2.4 T2DM與BTMs
T2DM患者的骨密度多數增高或無變化,可能與T2DM患者骨轉換水平降低有關[34]。印度的一項研究表明[35],與健康對照組相比,T2DM的OC水平顯著降低(4.06±1.97 VS 9.62±3.29 ng/mL,P<0.001)。一項橫斷面研究顯示[36],T2DM與非糖尿病患者相比,TRACP(1.39±0.99 VS 1.85±0.81 UI/L,P<0.05)、CTX(0.20±0.12 VS 0.33±0.15ng/mL,P<0.05)降低;BALP (14.83±6.5 VS 12.96±6.73μg/mL,P=0.11)、OC(1.48±1.25 VS 1.45±1.2 ng/mL,P=0.911)水平沒有差異。另有研究表明[37],T2DM的骨形成指標(P1NP,P<0.001)和骨吸收指標(CTX,P<0.001)顯著降低。也有研究發現T2DM的OPG水平是升高的[38-39]。
T2DM患者本身的高血糖可導致滲透性利尿,使鈣、磷、鎂等從尿中大量排出,使機體處于負鈣平衡;低血鈣及低血鎂促進甲狀旁腺功能亢進,使破骨細胞活性增強,鈣、磷動員增加,骨質脫鈣,骨密度下降,導致骨質疏松[40-41]。長期高血糖也可使體內產生過多的糖基化終末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AGEs),對骨骼形成有負面作用[42]。AGEs的堆積可以刺激破骨細胞骨吸收因子白介素-6 (IL-6)、腫瘤壞死因子-α (TNF-α)形成,這些因子可以促進破骨細胞的成熟,導致骨吸收增加[40-42]。OPG/RANKL系統可能干擾了T2DM的骨轉換[38]。也有研究[43-44]認為,T2DM對骨轉換的影響可能是通過改變Wnt通路使骨硬化蛋白的水平升高,增加OPG的表達,促進骨吸收所致。在T2DM晚期,胰島素分泌不足,影響成骨細胞的分化和形成,并影響骨基質的形成和礦化,從而引起骨密度和骨強度的下降。另外大多數T2DM合并肥胖,血脂聯素水平升高,脂聯素水平與骨密度呈負相關,與尿NTX的排出呈正相關[45]。
3 糖尿病腎病與BTMs
一項臨床研究[46],分別檢測T2DM正常白蛋白尿患者(51例)與糖尿病腎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患者(微量白蛋白尿組40例,臨床白蛋白尿組28例,腎功能不全組20例)的骨密度及BTMs,結果顯示25羥維生素D3在正常白蛋白尿組最高,在DN各組間隨著腎功能的惡化逐漸降低(P<0.05)。DN各組OC及P1NP均低于正常白蛋白尿組(P<0.05)。DN各組CTX均高于正常白蛋白尿組(P<0.05)。大量白蛋白尿組及腎功能不全組各部位骨密度值均低于正常白蛋白尿組(P<0.05)。結論是隨著T2DM患者腎功能逐漸下降,其骨量減少的程度逐漸加重,P1NP、OC、CTX、25羥維生素D3等骨代謝指標較骨密度更敏感地反映DN早期骨轉換的變化。
DN是糖尿病的主要微血管并發癥,DN腎小球濾過膜通透性增加,25羥維生素D3缺乏,體內鈣、磷代謝失衡等因素均不斷作用于骨代謝,隨著腎小球濾過功能的明顯下降,腎小管分泌與重吸收功能消失,鈣、磷代謝紊亂及其引起的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等進一步加重骨損害,引起一系列代謝性骨病的發生,從而影響骨轉換。
4 新型降糖藥與BTMs
4.1 腸促胰島素治療藥物與BTMs
腸促胰島素治療藥物主要指胰高血糖素樣肽受體激動劑(glucagon-like peptide,GLP)及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dipeptide peptidase - 4 inhibitors,DPP-4抑制劑)。腸促胰島素是腸源性激素,通過激活腸促胰島素受體信號通路發揮其生物學效應, GLP-1、GLP-2以及腸抑胃肽 (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GIP)在腸細胞攝入營養時釋放人血。骨細胞包括成骨細胞及破骨細胞上均有GIP和GLP腸促胰島素受體的表達。研究表明,GIP既可以作為抗骨吸收激素也可作為骨合成代謝激素[47],GLP主要是作為一種抗骨吸收激素[48],GLP-l受體對骨吸收的調節必不可少,缺少GLP-l受體的小鼠由于破骨細胞活性增加,從而使其骨皮質孔隙度增加。GIP和GLP-2對骨吸收有直接抑制作用,GLP-1則是間接的通過降鈣素依賴性途徑發揮其生物學效應。腸促胰島素在調節骨轉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enriksen等[49]在絕經后婦女的皮下注射利拉魯肽后,發現CTX水平下降、OC相應增加,表明利拉魯肽對骨形成具有刺激作用。故推斷腸促胰島素在骨代謝中發揮調節作用DPP-4可使腸促胰島素失活,DPP-4抑制劑則可延長GLP-1的作用時間,其對骨代謝的影響類似于GLP-1的作用。有薈萃分析表明,DPP-4抑制劑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風險[50]。
4.2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sodium glucose transporters 2,SGLT2)抑制劑與BTMs
腎臟通過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SGLT2)對葡萄糖進行重吸收,SGLT2存在于近端腎單位,可獨立于胰島素將葡萄糖轉運至細胞內[51],約90%的葡萄糖通過SGLT2轉運體重新進人血液。SGLT2抑制劑可通過調節血中鈣與磷酸鹽的水平,從而影響骨量以及增加骨折的風險。臨床資料顯示,應用SGLT-2抑制劑與安慰劑組相比較,血清鈣以及25羥維生素D3的水平未見明顯改變,而血清磷酸鹽、鎂和PTH水平較安慰劑組有所增加,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52]。Taylor等[53]提出SGLT2抑制劑可對骨代謝產生不利影響。認為SGLT2抑制劑通過阻斷近端小管上皮細胞上的鈉-葡萄糖共轉運體2降低鈉轉運,從而驅動磷酸鹽和鈉的共同轉運。血清中升高的磷可促進甲狀旁腺PTH分泌從而增強骨吸收。
5 他汀類藥物與BTMs
長期的高血糖可促使動脈硬化,斑塊形成,還有部分肥胖的T2DM患者常合并高脂血癥,這就依賴于他汀類藥物的治療來達到調脂穩定斑塊的作用。有研究報道[54],與使用他汀類藥物治療的健康對照組相比,T2DM患者使用他汀類藥物治療后P1NP、CTX是明顯下降的。而且使用他汀藥物治療3年以上的T2DM患者比使用該藥物3年以下的健康對照組的CTX水平更低。一項隨機的安慰劑對照交叉試驗表明[55],T2DM患者使用阿托伐他汀治療12周與對照組相比BALP、OC和CTX并無明顯差異。
6 骨轉換抑制劑與BTMs
部分糖尿病患者合并代謝性骨病時,常常會使用骨轉換抑制劑治療。一項隨機對照試驗表明,使用阿侖膦酸鈉治療的T2DM患者的尿NTX水平比使用維生素D治療的患者明顯降低[56];與使用安慰劑治療的T2DM患者相比,其CTX、NTX、BALP都是下降的[57]。另有研究表明,使用雷洛昔芬治療的T2DM患者的NTX水平下降,但BALP水平無明顯變化[58]。丹麥的一項隊列研究表明,T2DM患者使用骨吸收抑制劑有利于預防骨折的發生[59]。
7 小結
骨質疏松癥是糖尿病嚴重的并發癥之一,因其致殘率、致死率較高越來越備受關注。T1DM和T2DM患者均是骨質疏松癥和骨折的高危人群,雙能X線骨密度不能完全評估骨密度正常或增高的這部分糖尿病患者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近年來,某些BTMs如P1NP、CTX、OC、25羥維生素D3及IGF-1被認為可以早期發現糖尿病患者骨量減少、預測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但各研究之間存在很大的異質性,且影響BTMs與糖尿病關系的因素很多,可能與年齡、性別、體重、糖尿病類型、糖尿病病程、觀察時間、糖尿病并發癥及伴發病、跌倒、糖尿病治療等密切相關。所以對于高危人群我們需要聯合監測骨密度與BTMs,更全面、合理的評估骨質量,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DOP患者,預防骨折。目前,雖然BTMs的實驗室檢查方法、正常值范圍不統一,但其獨特的應用潛力及臨床價值不容忽視,開展BTMs的研究,特別是在糖尿病患者中,這對防治DOP及骨折至關重要。總之,DOP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健康問題,糖尿病患者骨折風險明顯增加,BTMs為我們提供了DOP早期診斷和療效評估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