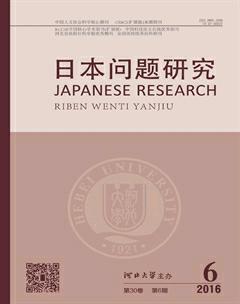日本“國家正常化”與美國的東亞地緣戰略
侯典芹
摘 要:戰后,由于美軍單獨占領日本,美國占領當局直接主導了日本的非法西斯化改革,日本的對外政策也被納入美國的東亞地緣戰略框架內。正因如此,戰后日本的“國家正常化”進程與美國的亞洲地緣戰略密切聯系在一起。冷戰時期,日本充當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哨兵,日本在“舊金山體制”下獲得“獨立”和國際空間。冷戰結束后,美國推行全球霸權戰略,日本乘機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擴展自主權。尤其進入21世紀,日本通過參與美國的“反恐”戰爭,實現了海外派兵。近年來美國實施戰略東移和“亞太再平衡”,日本借機加快修憲活動和軍事“解禁”,加速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步伐。
關鍵詞:日本;國家正常化;美國;地緣戰略
中圖分類號:D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16)06-0021-0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6.004
戰后不久,日本就開始了“國家正常化”的漫長進程。尤其是冷戰結束后,日本更加主動地迎合美國的亞洲戰略,乃至全球戰略,以便借機擴大自主權。進入21世紀,日本充分利用美國戰略東移的機會,加快軍事上的“解禁”行動,加速實現“國家正常化”。但由于戰后美日關系的特殊性,日本的 “國家正常化”進程只能限定在美國的地緣戰略框架內。作為美國亞洲戰略的地緣“前哨”,日本曾一度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重要“冷戰”棋子。在后冷戰時代,日本又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地緣戰略支點。近幾年,美國加快實施戰略東移,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更是給日本擴大自主權帶來機遇。日本則充分利用這些機會,逐漸推進“國家正常化”。
一
由于二戰結束時日本被美國軍隊單獨占領,戰后初期的非法西斯化改革也是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控制下進行的,所以日本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美國。而美國戰后執行的是全球霸權戰略,為此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一直以蘇聯作為其最大的對手,其對外戰略中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將蘇聯勢力“遏制”在二戰結束時所確定的界限之內。正是出于這種地緣戰略的目的,美國在西歐、中東、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建立起一系列針對蘇聯的軍事同盟體系,把社會主義國家包圍在其中。在東亞地區,日本成為美國“遏制”蘇聯勢力進入太平洋的重要前哨,美國在日本大量駐軍,并與其在韓國的駐軍形成犄角之勢。
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國憲法》,到次年5月開始生效。這部憲法不僅規定了日本的政體和國體,尤其是其中的第九條強調了日本“放棄戰爭 ”權力,成為這部憲法的最大特色,這部憲法也因此被稱為“和平憲法”。然而,美國的對日政策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特別是其亞洲戰略服務的。因此,就在這部“和平憲法”剛剛公布不久,無論是美國的華盛頓的起草者還是東京的執行者都后悔不已,并想方設法要加以修訂(即憲法的第9條,即“和平”條款),只是由于民眾的反對才未能修改[1]。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由于蘇聯控制著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具備向海洋方向擴張的地理條件和實力基礎。要遏制蘇聯向海洋方向擴張,最好的辦法是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建立起防御線。所以,在冷戰爆發的背景下,美國一方面加緊干預中國內政,甚至支持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另一方面,美國高層也在開始考慮對日政策的調整,即由原來的削弱日本轉為扶持日本。1947年3月,麥克阿瑟就提議與日本盡早媾和,美國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并表示促進早日實現媾和[2]。
隨著冷戰的爆發,美國的東亞地緣戰略也開始發生變化。“二戰”期間一方面,美國總統羅斯福出于對日作戰和戰后重建東北亞國際新秩序的需要,日益重視中國的地緣戰略價值,并積極推行使“中國大國化”的方針,廢除了近代以來美國對華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構建美、英、蘇、中四大國合作體系[3]。為此,美國不惜大力支持蔣介石,在促使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后,轉而積極支持蔣介的內戰政策。另一方面,美國對當時中國內部的政治形勢還是有所了解的,在中國內戰形勢逐漸明朗的情況下,美國不得不做兩手準備,即在繼續支持蔣介石政府的同時,改變對日政策,開始扶持日本。正如有學者所言,“雖然在1946年的憲法中美國堅決要求日本接受第九條的和平條款,但幾乎自1946年憲法剛開始生效的那一時刻起,美國就懊悔不已”[4]。
同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已經開始在實際上修改“和平憲法”,更加積極地扶持日本。按照麥克阿瑟的命令,日本政府創建了7.5萬人的警察預備隊,后來這支隊伍成為保安隊,最終又被改變成日本自衛隊。朝鮮戰爭期間,美國甚至試圖說服日本重新建立軍事力量,以幫助美國包圍蘇聯。但是,由于當時日本國內和平勢力非常強大,吉田茂政府頂住了美國的壓力。在吉田茂任內,以及其繼任者時期,日本主要維持輕型武器裝備戰略,依靠美國的安全保障,專心于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5]。隨著國際冷戰體制的形成,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一批戰前的政治家,甚至其中包括一些戰犯,得以重返日本的政治舞臺,如,鳩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他們提出了“重建國家”的口號,試圖重新恢復日本在美軍占領當局主持的改革中被剝奪的東西,包括重新建立武裝力量,重建強權國家。這些主張的的核心內容就是重新自主制定憲法。針對這股國家主義的逆流,日本國內保守派與革新派都加強了各自內部的團結,最終確立了重新統一的社會黨得以在國會維持了“護憲”所需的席位,即“五五年體制”[6]。同時,由于“冷戰”對峙態勢在亞洲不斷加劇,最終升級為“熱戰”,引發了朝鮮戰爭。而“朝鮮戰爭的爆發迫使美國最終確定了單獨媾和的對日和月薪方針”[7]。1951年9月,美、英、法等48個國家在舊金山簽署對日和約,隨后美日又單獨簽署了《安全保障條約》。這樣,日本在舊金山體制下不僅獲得了“獨立”,而且得以重返國際社會[8]。
到20世紀60年代,美日重新簽訂《美日安保條約》,推進美日“戰略伙伴關系”,使得一度出現危機的日美關系得到恢復。根據新的《美日安保條約》,日本自衛隊力量雖然受到嚴格的限制,但仍得到漸進式的擴充。在“局部戰爭下常規武器的進攻”的預想下,日本通過第2次防衛力量擴充計劃(1962年-1966年)和第3次防衛力量擴充計劃(1967年-1971年)。同時,日本自衛隊的武器裝備不斷向現代化邁進。但是也必須看到,在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力量仍非常強大的背景下,日本民眾曾多次掀起反對美國軍事基地,尤其是要求收回沖繩主權的群眾運動,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參與美國的越南戰爭的行動。1968年1月,佐藤政府還提出了“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隨著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的民族自信心逐漸提高,日益不滿“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國家身份角色,追求政治大國的傾向越來越突出。
總之,二戰結束后,由于日本國內形勢以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美國的軍事占領下的日本,開始成為美國霸權戰略聯盟中的從屬伙伴。再者,美國占領當局主導制定了日本的戰后和平憲法,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日本重蹈軍國主義道路。在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格局下,日本被置于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際體系的力量結構中,其內政外交都要從屬于這一大的戰略格局。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日本在美國的對蘇“遏制”戰略中的重要地緣角色是顯而易見的,就像英國在歐洲、在歐亞大陸西部外圍所扮演的角色。在漫長的冷戰時期,美國先后發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海灣戰爭,其駐日本的軍事基地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總的來看,日本的軍事角色(自衛隊角色)還是消極的、從屬的。
二
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國際格局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時,美國和中國的實力都發生變化,隨之的國家戰略也開始出現調整。這些變化成為日本國家戰略調整的重要的外部條件。但是,日本的國家戰略調整不可能完全脫離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尤其是美國的亞太地緣戰略。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執行全球霸權戰略。日本則利用美國進行“反恐”戰爭的機會,在軍事上逐漸突破國際法和國內法的束縛,向著“正常化”的方向邁進。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著名國際關系學家約瑟夫·奈曾經這樣評價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和地域規模確保中國在東亞地區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在多大程度上中國能成為挑戰美國全球霸權的力量則取決于其經濟增長和政治凝聚力,即使幸運之神眷顧,中國仍任重道遠”[9]。可見,當時美國并不擔心將來中國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相比之下,倒是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后的日本引起西方國家的擔憂。80年代初,日本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10%;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進一步上升到15%。當時美日之間不斷發生經濟摩擦,根據冷戰后美國的民意調查結果,美國有相當的民眾認為,“今后的威脅不是蘇聯而是日本”[10]。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很多日本人認為:“既然‘勝利了——蘇聯解體,曾經的軍事威脅不復存在——那就意味著要對冷戰關系重新審視,日美關系需要重新界定,就像在歐洲所發生的那樣”[11]。 但是,這種希望很快破滅了。再加上經濟矛盾的激化,加劇了美國民眾的“反日”情緒,同時也增加了日本人的“厭美”情緒。“美日關系日益充滿了摩擦、憎恨和相互指責”[12]。甚至美國一度將日本的經濟威脅視為蘇聯軍事威脅消失后要面臨的最大威脅,對于日本長期以來在安全上的“搭便車”也不是那么慷慨了[13]。
但是,到90年代中期,作為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的約瑟夫·奈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改變。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爆發,美國在東北亞地區遇到冷戰后首場嚴峻的安全挑戰。雖然經過四方會談的協調達成《核框架協議》,半島核危機得以暫時化解,但是此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對東北亞地緣政治安全形勢的觀點。恰在此時,“中國威脅論”一時間甚囂塵上,從而使美國的東亞地緣戰略經歷了短暫的搖擺之后又重新回到原有軌道上。也就是說,日本仍是美國亞洲地緣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80年代,日本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在經濟力量日益膨脹的驅使下,日本越來越不滿足于只作經濟大國的“畸形國家”,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做政治大國的意向。80年代是戰后日本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時期。中曾根政府作為這一轉折時期的的產物,他本人還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推動了日本的右傾化,助長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削弱了左派力量,并使日本社會上的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傾向有所發展,使日本朝著政治大國的方向前進了一步[14]。中曾根執政期間不僅以首相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詆毀踐踏“東京審判”,還要求日本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期間,日本的防衛費用突破了占GNP1%的限額,他還縱容日本篡改侵略歷史,唱軍國主義時代的“君之代”,掛太陽旗。在經濟急劇膨脹的背景下,日本政界逐漸形成了以擴張軍事力量為基點的政治大國外交目標。
進入90年代,日本利用美國發動海灣戰爭,“9.11”事件以及本世紀初的兩場“反恐”戰爭,借船出海,在“國際貢獻”的旗號下,先后向許多國家派出自衛隊,并同時完成了一系列法律的修改,開始了向“正常國家”邁進的歷程。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日本向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提供了13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但仍招致了美國高層的不滿。在海灣危機期間,美國不僅要求日本向多國部隊提供財政援助,向“前線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向駐日美軍提供新的支持。“海灣危機期間,美國十分希望日本為反伊聯盟提供人力支持,尤其希望日本能夠向海灣地區派駐掃雷艇和補給艦為多國部隊提供后勤支援”[15]。當時美日關系正在經歷冷戰結束,國際格局轉變的考驗,日本根據憲法規定沒有派兵參加多國部隊。
結果日本政府招致美國的批評,認為日本為戰爭做得太少,也太遲了。面對美國的批評,日本高層頗為震驚,也感到了“心理受到了創傷”。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確為日本修改憲法,向正常國家邁進提供了機遇。隨后,日本政府就一直謀求為修改憲法掃清障礙。1992年,日本國會通過《聯合國維和行動協力法》(即PKO法案)。接著,日本自衛隊參加海灣的掃雷行動。隨后,日本又通過一系列法案,使其自衛隊得以在柬埔寨、莫桑比克、戈蘭高地以及東帝汶等地的聯合國維和行動。
美日同盟關系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的結束一度使美日關系出現“漂流”。隨后由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美國漸漸意識到一個新的潛在競爭對手正在崛起[16]。“中國威脅論”很快在東亞地區散布開來,并成為美日同盟關系繼續維持的理由。所以從90年代中期開始,美日同盟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也有學者認為,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日美失去了共同對付威脅蘇聯的戰略需要,成為日美關系進入準平等時期的重要前提條件。而90年代前半期日美之間發生的嚴重經濟摩擦,正是日本試圖進一步實現美日關系平等化的表現。此后,美國出于全球戰略利益的考慮,不僅需要緩和美日間的經濟矛盾,加強雙方的經濟合作,而且還需要努力為美日同盟尋找一個可能取代蘇聯的新的共同威脅,以便作為維系美日同盟關系的新紐帶。而這個時期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以及隨后發生的臺海危機,使美日兩國意識到中國強硬態度背后的某些暗示。
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冷戰結束后,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也發生了某種變化。1994年朝鮮半島第1次核危機爆發,這次危機曾一度使美朝關系走向戰爭邊緣。對于這件事對美日關系的深刻影響,有學者認為,“如果日本政府在對待朝鮮半島危機時像海灣戰爭那樣不能進行安全保障合作,日美同盟此次大概真的會壽終正寢。果真如此,日本能否單獨對付朝鮮的核威脅呢?答案是不能!這一結論是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再次得到認識。朝鮮和臺灣海峽的危機,催生了1996年橋本和克林頓重新定義日美安保的聯合聲明”[17]。這次危機發生后,日美于1995年達成防衛新指針協議。隨后,在美國發展地區導彈防御技術方面,日本成為其中最積極的伙伴[18]。相應地,日本比以前更積極配合并參與了美國的一些海外軍事行動。2002年以后,日本先后參加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動,邁出了日本戰后海外派兵的第一步。2005年,日本同意了一項關于為期五年的美日合作協議,即兩國聯合生產導彈防御系統,并承擔10億美元的費用,來建設導彈防御系統的硬件設施。而就在這年的下半年,日本正式同意美國的一艘核航母在日本建立基地。2007年,日本把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防衛廳長官升為防務大臣。日本在軍事解禁方面邁出了具有實質性的一步。2008年,美國的核動力航母喬治·華盛頓號停靠日本橫須賀美軍基地。為了應對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新變化,美國仍然需要日本充當其亞太地緣戰略的棋子,日本則會繼續尋找機會加快國家“正常化”的步伐。
三
2009年初,當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時,美國深陷嚴重的金融危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更令美國戰略家們焦頭爛額。全球金融危機尤其使歐洲國家遭受重創,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主權債務危機。相比之下,亞洲經濟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世界經濟的中心迅速從歐洲轉向亞洲,亞太地區將成為未來世界的經濟和政治中心。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利益方面的考慮,不得不加快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無論是從未來亞太地緣政治格局的戰略利益考慮,還是從目前制衡中國實力增長的角度出發,美國都需要日本這個重要地緣戰略棋子。而在經濟實力下降的背景下,美國在亞洲會更多采用“平衡”戰略,充當亞洲的“離岸平衡手”。
關于日本在美國東亞地緣戰略中的角色,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明確指出,由于近代以來中日關系的曲折,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日本就是美國遠東政策的基地,從最初的美國占領軍的駐地,逐漸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政治和軍事存在的基地,日本也因此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全球盟友。所以,“美日關系如何演變是中國地緣政治前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19]。基辛格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指出,在美國的亞洲地緣戰略中,無論是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中,還是在東南亞地緣政治中,日本在美國對華“遏制”戰略中都會扮演日益活躍的角色。所以,美日關系是美國在亞洲的最重要關系[20]。因此,無論是冷戰時期“遏制”蘇聯勢力東進亞太,還是阻止中國進入西太平洋地區,日本都堪稱是美國的亞太戰略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地緣戰略意義十分突出。中日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民族積怨以及領土爭端等,嚴重影響了兩國關系的正常發展。尤其是釣魚島問題,不僅成為中日之間的最大障礙之一,而且成為美國介入中日爭端的楔子,美國介入東亞事務、制衡中國的重要抓手。
2009年,鳩山由紀夫政府重新確定了對美政策,有意疏遠美國,但日本仍然是美國最密切的盟友。菅直人上臺后,重申了日本的承諾,擴大美日防衛合作,允許美國海空軍繼續駐扎沖繩軍事基地。美國“重返”亞太,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這是一種帶有赤裸裸的麥金德式、以勢力均衡為核心的地緣戰略。日本則利用這個機會,借機大肆煽動“中國威脅”論,以便為日本加緊軍事“正常化”和修改“和平憲法”做準備。
在安倍第一任期內,日本就已經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正如安倍在紀念儀式上所說,冷戰結束后日本的安全保障環境發生了變化,日本有必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防衛力量的作用。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在日本擺脫戰后體制、建設新國家方面邁出重要的第一步”。 后來的事實表明,安培并沒有停止使日本“正常化”的腳步。相反,在第二任期內,安倍借美國在亞洲地區實施“再平衡”戰略,擴大日本自衛隊的行動范圍。加強日美軍事同盟關系。為了配合美國在南海對中國的挑釁行動,日本開始積極介入南海爭端。自2015年6月份,日本國內就開始討論自衛隊是否應該參與美國的南海巡航行動,日本拓殖大學特任教授、前防衛大臣森本敏說:“日本應該參加南中國海巡航,但是從地理和邏輯來說,菲律賓更該參加,因為菲律賓不僅是美國的軍事同盟國,而且是當事國。至于日本,應與當事各國一起,以合作的方式參與”。盡管日本社會中反對這種行動的聲音很大,但這卻從側面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某種傾向。
針對歐亞大陸上的中國崛起,其地緣政治色彩非常明顯。2015年4月安培訪問美國期間,美日發表了新修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首次明確規定:美軍支援日本包圍和奪回島礁的聯合作戰,以及美日兩國針對日本以外國家受到武力攻擊是共同參與海上作戰。美日軍事合作的范圍已不再僅限于“周邊事態”,而是進一步擴大到全球范圍。所以,安倍訪問美國之后,日本國會將會按照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通過《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聯合國和平合作法》、《船舶檢查法》等的修訂案,并新設立所謂《國際和平救援法》,為戰爭中的美國及多國部隊提供后方支援,行使所謂“集體自衛權”。為了清除日本軍事“正常化”道路上的最大根本障礙,安倍的下一個最大目標就是,在明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的勝利,然后在其任內實現修改《日本國憲法》[21]。
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新的安保法案,實現了戰后日本安保政策的最重大的一次調整。這種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其實質是賦予日本政府主動發動戰爭的權利,與“和平憲法”的基本精神相背離,是一種變相的“修憲”行為。它不僅會對日本國內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會給國際社會尤其是鄰近國家的安全帶來更多不可控的因素,使得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對此,將拭目以待。
四
自“冷戰”爆發之日起,日本就成為美國在亞洲實施“遏制”戰略的重要地緣“前哨”。日本的對外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在美國東亞地緣戰略的框架內,而且日本的“正常化”進程的每一步都與美國的東亞地緣戰略乃至全球地緣戰略聯系在一起。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對于日本而言,用這句話形容幾十年來的美日軍事同盟關系也許并不為過,美日軍事同盟關系是戰后國際秩序的產物,是美蘇“冷戰”的結果,美國不會輕易讓日本脫離自己的懷抱,日本的“國家正常化”只能處在美國地緣戰略的框架內。從美國全球地緣戰略來看,其基本目標仍是防止歐亞大陸出現一個嚴重的霸權挑戰者。隨著亞洲的迅速崛起,美國深切感受到這種挑戰。于是,美國一方面加快實施戰略東移,另一方面,鑒于自身實力的相對下降,不得不更多依靠其亞洲盟友的力量,以實現“亞太再平衡”。美日同盟已經從對付蘇聯轉向主要針對中國,日本在執行美國戰略上逐漸變被動為主動,并利用中美之間的利益分歧,以對付“中國威脅”為名,加快軍事“解禁”活動,以實現日本的“國家正常化”。
[參 考 文 獻]
[1]Glenn D,Hook,Gavan McCormack.Japan's contested constitution:documents and analysis[M].New York: Routledge,2001.
[2]五百旗頭真.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吳萬虹,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23.
[3]宋成有.東北亞史研究導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396.
[4]加文·麥考馬克.附庸國:美國懷抱中的日本[M].于占杰,許春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72.
[5]約瑟夫·S·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M].劉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32.
[6]李寒梅.日本民族主義形態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74.
[7]沈志華.對日和約與朝鮮停戰談判[J].史學集刊,2006(1):66-75.
[8]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3.
[9]約瑟夫·S·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M].劉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13.
[10]五百旗頭真.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吳萬虹,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173.
[11]加文·麥考馬克.附庸國:美國懷抱中的日本[M].于占杰,許春山,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73.
[12]Richard Holbrook.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Ending the Unequal Partership[J]. Foreign Affairs,1991(5):42-56.
[13]邁克爾·H·阿馬斯科特.朋友還是對手——美國駐日大使說日本[M].于鐵軍,孫博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78.
[14]黃大慧.日本大國化趨勢與中日關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71.
[15]王緝思,牛軍.締造霸權:冷戰時期的美國戰略與決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35.
[16]馮昭奎.復交40年:中日關系中的美國因素[J].日本學刊,2012(5):49-65.
[17]五百旗頭真.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2010[M].吳萬虹,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231.
[18]Robert S.Ross.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Security Order[J].Orbis,2010(54)4:525-545.
[19]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M].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0.
[20]亨利·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M].胡利平,凌建平,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99.
[21]劉江永.地緣政治思想對中美日關系的影響[J],日本學刊,2015(3):1-20.
[責任編輯 李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