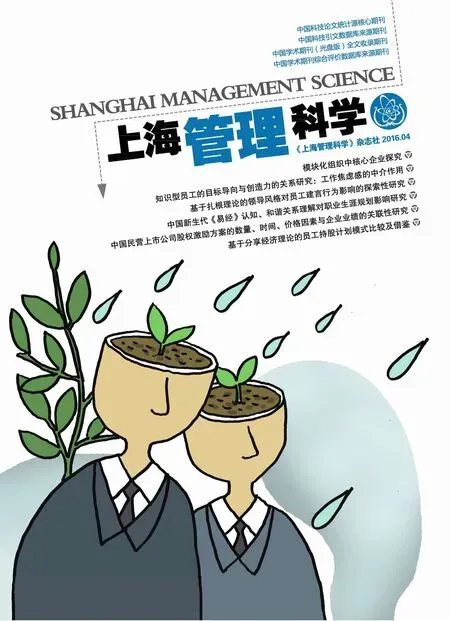知識型員工的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關系研究:工作焦慮感的中介作用
彭志遠 路 琳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知識型員工的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關系研究:工作焦慮感的中介作用
彭志遠 路 琳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知識型員工的創造力,影響其創造力的主要因素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本文探討了目標導向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作用,分析了工作焦慮感在目標導向與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基于對主管與員工問卷調查,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掌握趨近目標導向、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員工創造力具有正向關系;工作焦慮感在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員工創造力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知識型員工;目標導向;創造力;工作焦慮感
引言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目標導向與創造力之間關系的研究層出不窮,學習目標導向(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與創造力之間的正向關系廣泛得到證明,使得學習目標導向幾乎與富有創造力相提并論;表現目標導向(Performance goal orientation)與創造力的關系則并不明朗,部分研究發現兩者呈負向關系,另外一些研究則報告兩者不存在線性關系。之前學者對于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關系的研究往往基于學習目標導向和表現目標導向的二維度論,近幾年一些學者提出的目標導向三維度論和四維度論,對目標導向的劃分更為精確。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了Elliot和McGregor(2001)的目標導向四維度框架,將目標導向區分為掌握趨近目標導向(Mastery prove goal orientation)、掌握回避目標導向(Mastery 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表現趨近目標導向(Performance prove goal orientation)、表現回避目標導向(Performance 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其中,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表現為尋找機會提升能力,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為避免出現無法學到新技能的情況,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表現為尋找機會證明自身價值,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表現為避免在眾人面前暴露自身不足。
對于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關系,較多學者認為目標導向需要通過一些中介變量進而影響員工創造力。Gong和Huang(2009)認為學習目標導向通過創造性自我效能正向影響員工創造力。王端旭和趙軼(2011)則發現積極心境能在學習目標導向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現代企業中的知識型員工常常承受一定水平的工作壓力,進而產生工作焦慮感。將工作焦慮感引入目標導向和創造力的關系,進一步研究目標導向對知識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理,無論從管理理論還是實踐的角度來看都具有重要意義。
1 理論基礎與假設
1.1 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關系
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勇于在工作中嘗試各種他們認為能夠對工作帶來好處的方法,在可能的失敗與挫折后,并不氣餒,并總結出盡可能好的解決工作問題的方案。Dweck和Leggett(1988)研究發現,學習目標導向的員工,更渴望面對工作的多樣性、易變性和不確定性。Gong(2009)和宋文豪(2014)均從創造性自我效能的視角,發現學習目標導向能夠通過創造性自我效能影響員工創造力,這類目標導向較高的員工通常具有較高的創新型自我效能,信心滿滿,敢為人先,對于復雜的、挑戰性較高的工作并不畏懼,并愿意投入精力去進行創新,這樣一來自然表現出超出尋常的創造力。
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著眼于如何避免不能清楚理解新的工作知識、不能快速領悟新的工作技能。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真誠且熱衷于學習和發展自我,是具有主觀意愿的“主動創新”;而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由于僅僅是避免自身工作能力不能得到提高,就會消極地應對工作中的新知識和新技能,雖然也會有創新,但卻只能是具有消極情緒的“被動創新”。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較高的員工,通常具有完美主義傾向,自我標準較高,不愿輕易犯錯,他們有創新的想法,但害怕犯錯后收到負面評價,一定程度上,這些特點限制了大膽創新。
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主要考慮在工作中勝過其他員工,向他人證明自己的能力更強,在績效考核中取得高人一等的成績。為了使工作績效比他人更加優異,員工可能會傾向于從事更為熟練的工作,為了回避風險和不確定性而不敢進行創新。然而,對于本文研究的知識型員工,其從事的工作不同于簡單、重復性高的勞動,而是具有創造性的高層次腦力勞動。面對工作的易變性和不確定性,要想獲得更加優秀的工作績效,需要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努力提高自身技能水平,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才干和靈感,在工作中通過創新行為更佳的工作績效。Elliot等研究發現,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員工的自我效能感、成就追求等因素正相關,而這些因素常常對創新行為有正向作用。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對于創造力可能產生積極影響,但是本質上他們追求的還是良好的工作績效,對于知識型員工而言,創造力和工作績效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
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認為自身能力并不能靠努力而改變,他們關注的是如何避免獲得較差的績效,并且不愿意讓他人發現自身的不足。Button等人(1996)研究認為,表現回避目標導向明顯帶有消極意味。由于創新成果不僅僅需要新穎的想法和創意,更需要的是將想法付諸實踐。而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害怕接受挑戰和承擔責任,往往容易在一兩次失敗后就“打退堂鼓”,根源在于他們害怕、或是不希望得到別人負面的評價,所以一般情況下他們并不愿意改變現狀,而是選擇墨守成規,故步自封。而一旦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較強,員工希望盡可能地避免消極評價和負面結果,往往也會導致他們產生防御性行為,也即回避創新。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a 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具有正向關系。
H1b 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具有正向關系。
H1c 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具有正向關系。
H1d 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具有負向關系。
1.2 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的關系
Linnenbrink和Pintrich(2000)提出,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低程度的焦慮相關聯,掌握回避和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中等程度的焦慮相連,而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高程度的焦慮相連。Elliot和McGregor(2001)使用相關分析法研究,發現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考試焦慮正相關。Linnenbrink和Pintrich(2002)結合已有的成就目標導向理論和學業情緒研究,得出了兩者之間的一些基本結論:掌握趨近目標導向對積極情緒(如喜悅,希望,自豪等)有正向影響,對消極情緒(如焦慮,內疚,難堪,生氣等)有負向影響;掌握回避目標導向對積極情緒無影響,對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對積極情緒有正向影響,對消極情緒的影響不確定;表現回避目標導向對積極情緒無影響,對消極情緒有正向影響。Pekrun和Elliot(2009)用Elliot等人編制的成就目標導向問卷對美國、德國等地的大學生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表現回避目標導向可以正向預測焦慮,而焦慮則負向預測工作績效。劉惠軍和郭德俊(2003)發現,考前焦慮與掌握趨近目標導向顯著負相關,與掌握回避目標導向和成績回避目標導向顯著正相關。
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勇于在工作中嘗試新鮮事物,總是顯得信心滿滿,對于復雜的、挑戰性較高的工作并不畏懼,并愿意投入精力去進行創新,且隨著掌握趨近導向的增強,員工更加享受學習的過程,這樣可能降低焦慮。掌握回避目標導向雖然也以學習和掌握為目的,但其關注點是防止自身不能掌握應當掌握的知識,因此,這種傾向易產生焦慮感;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則關注表現和績效,在績效表現較差時容易產生焦慮。表現回避目標導向的員工,關注如何避免獲得較差的績效,故容易導致工作焦慮感。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a 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具有負向關系。
H2b 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具有正向關系。
H2c 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具有正向關系。
H2d 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具有正向關系。
1.3 工作焦慮感的中介作用
情緒能夠通過信息加工、認知拓展以及動機促進對員工創造力產生影響。雖然工作焦慮感屬于消極情緒,不利于思維發散,但焦慮感較強的員工往往注重細節,能夠在思考問題的深度上有所提升,也將帶來一定的創造力。Simonton(2000)提出的創造力 VSR 理論,認為創造性活動經過變異(Variation)、選擇(Selection)、保留(Retention)三個階段。一般而言,外部環境的變差可能使得員工感到焦慮、恐懼或者不安,其工作焦慮感一般也隨之上升。Zhou和George (2001)研究發現,工作不滿意感在一定條件下能夠激發員工的創造力,如果環境過于穩定舒適,不能引發員工對當前慣例的不滿,那么當前狀況會繼續維持。在此基礎上,當工作焦慮感較低時,外部環境趨于穩定,員工往往安于現狀進而產生惰性,創新行為所受到的外在刺激也會被一定程度削弱,從而也就相對抑制了員工創造力的激發。我們進一步討論,在合適的激勵下,自身焦慮感的提升恰恰會激發員工對于解決問題的探索,創新隨之而來。本文中,我們提出,某些目標導向恰恰創造了這樣的動機,使得人們能夠在一定的焦慮推動下進行創新。
情緒作為中介變量影響員工創造力已經被很多研究證實。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因為害怕自己不能掌握新的技能而產生工作焦慮感,很大程度上,這種焦慮感產生的積極作用勝過消極作用。使得員工努力學習、適應工作的快速變化,由此產生的內在動機很可能帶來工作、方法上的創新。同樣,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較強的員工,為了獲得較優的績效而產生了工作焦慮感,一旦績效出現下滑,雖然員工會表現出緊張和擔憂,但也同時表現了其對績效和出現的問題非常重視,且焦慮感的上升使其更加關注細節,很可能在創造力(尤其是有用性維度)上有所斬獲。
鑒于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掌握回避目標導向和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均能通過正向影響工作焦慮感進而正向影響員工創造力。而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表現回避目標導向雖然能夠對員工的工作焦慮感有一定影響,但其對于創造力的影響作用并不是通過工作焦慮感所致,故不在本研究討論范圍內,在此不做相應假設。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工作焦慮感在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正向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工作焦慮感在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正向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樣本
本研究通過調查問卷法獲取數據,采用員工自評與主管評價,其中主管評價員工的創造力,因此每一份研究數據都由員工本人問卷以及對應的直接主管問卷兩部分組成。本次研究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有效問卷395份,有效回收率達到87.78%,行業覆蓋了制造業、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等,其崗位分布主要集中在技術研發類、營銷類和人力資源管理類。
在被調查者中,性別比例方面,男性比例略低于女性,占47.6%,女性比例占52.4%;年齡方面,沒有19歲以下的員工,20至29歲的員工最多,比例為55.4%, 30至39歲的員工比例為35.2%,40至49歲的員工比例為8.4%,50歲以上的員工比例為1.0%;員工在當前公司的工作年限方面,1年以下的占18.2%,1至3年的占39.2%,4至6年的占25.6%,7至8年的占3.8%,9至10年的占4.6%,11年以上的占8.6%;員工在當前部門的工作年限方面,1年以下的占22.0%,1至3年的占43.0%,4至6年的占25.1%,7至8年的占3.3%,9至10年的占3.0%,11年以上的占3.5%;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學歷最多,占46.6%,大專學歷其次,占30.1%,大專以下和研究生或以上的比例分別為13.9%和9.4%。
2.2 測量
本研究的問卷采用配對數據的方式進行收集。其中,掌握趨近目標導向、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表現回避目標導向和工作焦慮感由員工自評,創造力由員工所在團隊的直接上級填寫。同時采用Likert7點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來測量上述變量各個條目,所有英文量表的條目都采用規范的標準翻譯和回譯程序以確保問卷的內容效度。
掌握趨近目標導向、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和表現回避目標導向的測量使用的是以Elliot和McGregor(2001)的2×2成就目標導向量表,共包含12個題目,每個目標導向3個題目(采用7點計分,從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7表示“非常同意”),其中如掌握趨近目標導向中的“對我來說,盡可能徹底地了解這份工作的內容非常重要”。
工作焦慮感的測量使用的是以Parker和DeCotiis(1983)的量表,共包含5個題目(采用7點計分,從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7表示“非常同意”),其中如“我完成工作以后會覺得緊張或煩躁”。
創造力的測量使用的是以Zhou和 George(2001)的量表,共包含13個題目(采用7點計分,從1表示“幾乎沒有”到7表示“非常頻繁”),其中如“員工提出新穎的和實用的意念,以改進表現”。
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選取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包括本公司和本部門)和受教育程度為控制變量。員工獲得的知識和技能與教育程度有關,教育程度能夠影響到員工創造力。而在以往創造力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常常把工作年限作為一個重要的控制變量進行研究。
3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3.1 驗證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使用Mplus6.0軟件對研究變量進行了驗證性因子分析(CFA),以檢驗掌握趨近目標導向、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表現回避目標導向、工作焦慮感以及創造力測量量表的區分效度。表3-1的結果表明上述六個變量作為單獨因子時模型擬合度最高,從而驗證了本文六個構念的區分效度良好。

表3-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3.2 相關分析
在進行假設檢驗之前,本研究對文中涉及到的控制變量與掌握趨近、掌握回避、表現趨近、表現回避、工作焦慮感、創造力這六個主要變量進行均值、標準差的描述性統計,同時對以上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3-2的數據顯示,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4(p<0.01),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8(p<0.01),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4(p<0.01),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7(p<0.01),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21(p<0.01),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46(p<0.01),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49(p<0.01),工作焦慮感與創造力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5(p<0.01)。本研究中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為本文的研究假設提供了初步的實證支持。
3.3 假設檢驗
由于本研究的問卷采用員工自評與主管評價,每一份研究數據都來自樣本員工與其對應的直接主管,我們借助SPSS19.0統計軟件用回歸分析的方法共檢驗了13個研究模型。
3.3.1 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關系檢驗
本文H1提出了目標導向對員工的創造力的影響。采用多元線性回歸進行檢驗,第一步加入員工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公司)、工作年限(部門)和受教育程度這5個控制變量得到模型1,第二步在模型1的基礎上分別將四大目標導向作為自變量加入得到模型2-5,如表3-3所示。掌握趨近目標導向、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顯著正相關(β=0.15,p<0.01;β=0.24,p<0.01;β=0.12,p<0.01),因此,H1a、H1b和H1c得到驗證。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關系不明顯(β=0.02,p>0.05),H1d未能得到驗證。
3.3.2 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的關系檢驗
本文H2提出了目標導向對員工的工作焦慮感的影響。采用多元線性回歸進行檢驗,第一步加入員工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公司)、工作年限(部門)和受教育程度這5個控制變量得到模型8,第二步在模型8的基礎上分別將四大目標導向作為自變量加入得到模型9-12。掌握趨近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顯著負向關系(β=-0.24,p<0.01),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表現回避目標導向與工作焦慮感具有顯著正向關系(β=0.19,p<0.01;β=0.42,p<0.01;β=0.46,p<0.01),因此,H2a、H2b、H2c和H2d均得到驗證。
3.3.3 工作焦慮感的中介作用檢驗
工作焦慮感對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中介作用進行假設檢驗需要滿足以下3個條件:首先,自變量(目標導向)與中介變量(工作焦慮感)的關系;其次,自變量與因變量(創造力)的關系;再次,將自變量與中介變量同時考慮時,自變量對于應變量的影響消失或者明顯減弱。其中條件2已經在H1中得到驗證,條件1中的自變量與中介變量的關系也已經通過H2驗證。

表3-2 描述性統計結果
H3提出了工作焦慮感對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中介作用,具體包括H3a提出的工作焦慮感對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中介作用與H3b提出的工作焦慮感對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中介作用。將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分別與工作焦慮感同時加入模型1后得到模型6、7。模型6、7的分析結果顯示,工作焦慮感在掌握回避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正向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表現趨近目標導向與創造力的正向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H3a、H3b得到驗證。

表3-3 實證模型回歸結果(包括本文全部12個模型)
4 結果討論與研究建議
4.1 研究結果
本文以知識型員工為研究對象,用問卷調查方法探討了員工目標導向與其創造力的關系,以及工作焦慮感在其中的中介關系。結果顯示:掌握回避目標導向和表現趨近目標導向均能通過正向影響工作焦慮感進而影響員工創造力。
以往研究結果表明,員工目標導向對創造力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一般而言,學習目標導向對創造力產生積極的影響作用,而績效目標導向對創造力產生何種影響作用,不同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卻并不一致,因此,本文對于二者關系重新驗證,并將兩類目標導向進一步細分,其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通過實證研究,解釋了員工創造力的內在動因因素,為員工目標導向對創造力的影響研究提供了實證數據支持,豐富了有關員工目標導向(尤其是四維度論)與創造力關系的理論;其次,本文在其他學者對員工目標導向與創造力關系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工作焦慮感這一中介變量,這為目標導向的影響機制提供了新解釋,也為后續研究拓寬了思路,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創新點。
4.2 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本研究中工作焦慮感指的是員工包含憂慮、恐懼和不安的情緒反應,屬于整體性定義。然而,大量文獻認為,焦慮可以進一步細分為狀態焦慮和特質焦慮。狀態焦慮是指因為特定情境引起的暫時的不安狀態,如憂慮、恐懼和緊張等;而特質焦慮是指一般性的、長期的性格特質,往往表現為一種固有的、持續的憂慮和不安。Boswell等人(2004)將工作壓力進行劃分,并認為挑戰型工作壓力往往利于自身創造力的激發,妨害型工作壓力則會一定程度限制創造力的發揮。本研究受此啟發,結合前面討論的焦慮的進一步細分(如特質焦慮和狀態焦慮,或抑制性焦慮和促進性焦慮),以助于更好解釋其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制。
第二,本文在目標導向的四種維度中,僅聚焦其中兩種導向,提出其通過工作焦慮感影響創造力的機制。針對另外兩種導向,即,掌握趨近型和表現回避型目標導向,受限于本研究的既定范圍,我們僅揭示它們與工作焦慮感有一定關系,但其對創造力的影響是通過其他機制產生。今后的研究可以此為方向,展開進一步探索。
4.3 管理啟示
本研究通過對員工的目標導向、工作焦慮感和創造力的關系進行研究,可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理解員工個體和環境差異對其創造力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可以為企業的人員招聘、后續培養、干部選拔等諸多流程提供智力支持,長期來看將對企業知識型員工人才隊伍建設提供幫助。另外,本文的研究可以為企業更科學地看待員工情緒管理(尤其是工作焦慮感),有助于企業營造最適合的組織氛圍,提高創造力。
[1] Elliot A J, McGregor H A. A 2× 2 achievement go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3): 501.
[2] Gong Y,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c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765-778.
[3] 王端旭, 趙軼. 學習目標取向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制研究:積極心境和領導成員交換的作用[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1, 32(9): 172-179.
[4] Dweck C S, Leggett E L.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8, 95(2): 256.
[5] Gong Y,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c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765-778.
[6] 宋文豪, 顧琴軒, 于洪彥. 學習目標導向對員工創造力和工作績效的影響[J]. 工業工程與管理, 2014, 19(2): 28-34.
[7] 梁國勝. 中小學生成就目標的結構及其發展特點的研究[J]. 碩士論文.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02.
[8] Elliot A J.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goals[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1999, 34(3): 169-189.
[9] Van Yperen N W. Task interest and actual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assigned and adopted purpose goal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6): 1006.
[10] 王端旭. 領導支持行為促進員工創造力的機理研究[J]. 南開管理評論, 2010 (4): 109-114.
[11] 柳麗華. 企業知識型員工績效管理研究[J]. 山東: 山東大學, 2006.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goal orientations on knowledge workers’ creativity: job-related feelings
of anxiety as a mediator
Peng Zhiyuan Lu Lin
Knowledge workers’ creativityis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successful organizations. Researchers hav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onfactors that predict knowledge workers’ creativity.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goal orientation onknowledge workers’ creativity,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job-related feeling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al orientation and creativity. Based a survey conducted among 395 dyads ofknowledge workers and their supervisors in diversified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employee’s masteryapproach goal orientation, mastery-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 orientation have signif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reativity; job-related feelings of anxie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mastery-avoidance goal orientation,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 orientation and creativity.
knowledge worker; goal orientation; creativity; job-related feelings of anxiety
C936
1005-9679(2016)04-0007-0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企業員工的探索性創新行為與開發性創新行為:內涵結構、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研究”(71272113),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與戰略重點研究”(15JZD017)。
彭志遠,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人力資源管理;路琳,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知識共享,創新,跨文化比較研究。